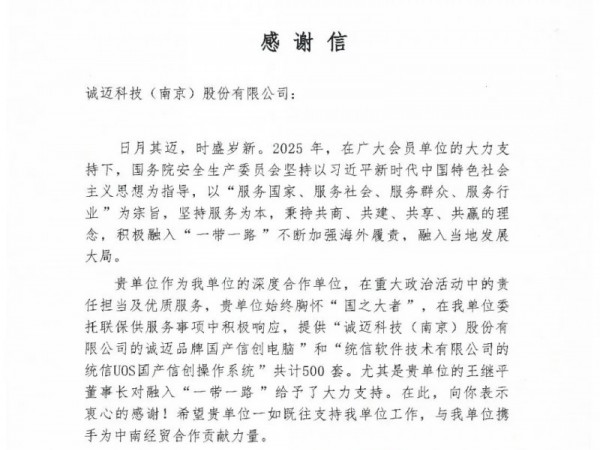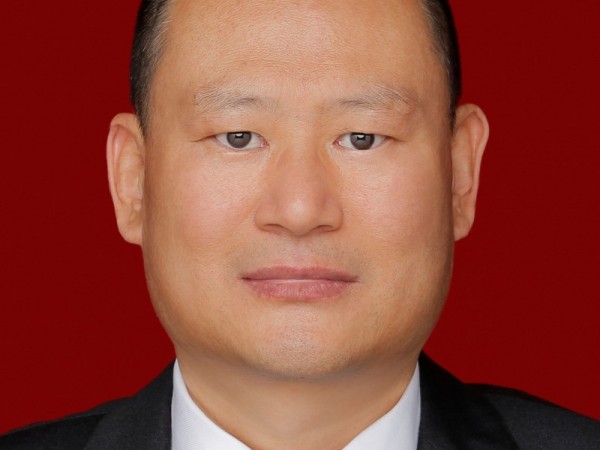1、“对内忽悠”3大典型症状
在这一篇里,我们将详细并分阶段地描述风险投资人与创业者相互之间“对内忽悠”的“典型症状”。但是在所有这些背后,我们要问一句,相互忽悠的世界“有多少信任可以重来?”
投资前期“忽悠”典型症状
核心词:Term Sheet
创业者:卖“分歧终端机”
手拿多份Term Sheet鼓动风投竞价
刻意伪饰企业表现
投资者:
“没诚意”,给了Term Sheet不打算投
“借用”创业者创意
个别坏分子还 可能要求返点
《非诚勿扰》中葛优活生生把一台“分歧终端机”忽悠给了范伟,可以说是艺术的夸张,但不少创业者把诸多如“垂直分 众”、“山寨分众”或者“中国youtube”这样的企业在很稚嫩的时候就忽悠给了投资人,恐怕是不争的事实,也是风投最近就自己以往的大干快上反思得最 多的地方。
风投表达初步想投资的意向,是从Term Sheet开始的。所谓TermSheet(投资条款清 单,termsheet ofequityinvestment)就是投资公司与创业企业就未来的投资交易所达成的原则性约定。
“话说从前的从前,那时天还是蓝的,水还是绿的,VC没谈过五轮是不给Term Sheet的,给了T ermSheet是准备要投资的。”——— 这虽是VC间流传的玩笑,但还是可以证明,以往的Term Sheet还是有类似于录取通知书的“含金量”的,而不像现阶段通胀贬值得厉害。
经历“就是想看、并不想投”的“非诚”类VC多了,很多创业者面对风险投资人的时候也留了一个心眼,甚至有企业“不见兔子不撒鹰”,不给 Term Sheet不给财务数据,因此Term Sheet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信物”,但是“信物”满天飞本身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另一方面,因为Term Sheet通常会设置排他性期限,在签订之后风投可以从容地做尽职调查,因此部分V C已把先给企业Term Sheet作为抢项 目的一种策略,但是Term Sheet也未必真是“兔子”———正如玩笑中所说,在TermSheet的背后实际投资诚意有多少,具体到各家风投,恐怕 就是一件悬殊很大的事情了。
因此就有企业在签订了TermSheet之后,被风投拖上几个月最终没拿到钱而不了了之(最惨的是可能 在这期间还碰上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导致企业“贬值”),难怪有创业者恨恨地说,不道德的风投,与耽误女人青春的男人同样可恶。
而学乖了之后的创业者也开始“多谈恋爱不结婚”,不着急签订Term Sheet,而是找风险投资人多要Term Sheet。在形势好的时候,经常有创业者手 里拿着五六份TermSheet让风投相互之间竞价,特别是如果这其中有知名V C的T ermSheet,那就相当具有“说服力”。一旦竞价,V C自 身也可能不冷静,你给10倍市盈率,我给15倍,最后20倍,还可能是高价买到的“赝品”,难怪曾有投资人在公开场合表示,“最不喜欢让V C竞价的企 业。”
但如果说Term Sheet的问题都还是“游戏规则”之内的话,有一些做法就“纯属道德问题”了。除了一些情理之中的装积 极的做法,创业者最常见的是对自己公司的情况造假,比如媒体曾曝光的在海外上市的某新能源企业,“看似繁忙的油罐车行来驶去,却始终未见任何油品装卸,更 有员工自曝,‘那些车都是租来的。’”
而风投方面最为不能容忍的可能就包括,极个别风投私下里找创业企业要求投资“返点”,因为风 投作为G P的收入是来自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和一定比例的激励收入,“但是我投资了这家公司,我个人会有什么好处?”一些把个人利益放在这个链条上的 V C,就可能会个人要点公司的股份,或者直接要求一定比例的投资现金作为返点。
还有一种情况,是风投“借用”(在创业者看来就是 “抄袭”)的作法——— 风投每天可能会收到相当多来自创业者的商业计划书,有部分风投可能会把有价值的创意移植到其他公司。风险投资人中还可能有一种创 业合伙人(EntrepreneurinResidence,EIR),他们有创业经验,同时参与评估项目,而创业者的想法,有可能就是触动他们下一次创 业的灵感。
2、“对外忽悠”的典型症状
一位成功企业家至今仍对当年差点被风投“搞死”的经历心有余悸。当时企业在经历了A轮融资之后,产品逐步成熟,也想进一步扩充资金。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认识了风投L先生。在交谈之后,L先生对这位企业家的公司十分赞赏,当场就要作势签支票。“要不这样,我们搞个隆重的融资发布仪式,当场签约。”然后风投对企业家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去花钱,把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弄上去,之后争取三年上市。
这位企业家兴冲冲地跑回去,从自己创业的小办公楼里退出来,花几十万租了个看上去比较像样的办公地点,交付了租金之后开始装修。
这期间该风投也到公司做了尽职调查,但是却始终没有实践最后签支票的一步——事后才知道,这家基金已经投资了该企业家的竞争对手,尽职调查是为了掌握更多关于企业的数据与内部情况。而这使得本来就缺钱的企业家在搬回原来地方的同时,又不得不支付租楼违约金,公司也险些就此一蹶不振——而这位风投至今仍活跃在业界。
面临忽悠与被忽悠的“灾后重建”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业界的笑话中总有夸张的成分,而且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笑话和不那么好笑的现实例证,但如果用“忽悠”来形容风投群体特征,显然对那些用心工作、尽心扶植企业成长的投资人不够公平。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业内普遍存在忽悠与被忽悠的现象,虽然可能“震级”不一样,但每次发生都可以看作是对诚信理念的摧毁,以此形成的负面效应甚至是恶性循环后患无穷———创投可以忽悠企业,企业反过来也可以以种种“中国式手段”来对付创投,最终只能是越来越恶劣的商业环境。因此,创投行业面临的“灾后重建”任务艰巨。
根据赵本山对范伟“早期、中晚期”症状的总结,创投和企业之间往往也会体现出不同 时 间段的典型症状,而“忽悠”种种怪现状也可以分为创投和企业家之间的对内忽悠,以及包括对媒体、对公众(包括对二级投资市场的股民)、对同行(其他风投)的对外忽悠。
而公平地说,如果按“主观”和“过失”来划分,“忽悠”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归为纯粹的“人品”和诚信问题,但也不排除有当事人“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企业形势、行业形势、包括资本市场错误的判断,而从客观上起到了对忽悠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一开始就抱着忽悠心态的,也有到后来被“逼上梁山”的……当年有一部老外写的《MrC hina》专门讲自己是如何被中国合作者忽悠的,而近两年来风投界的类似主题素材也足可以写成一本著作。
为什么创投界会有如此多的“七十二变”忽悠?归结起来无非是“机会多,法规少,人才缺”,在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无数商业机会,众多行业都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在资本市场造就的“创富神话”刺激下,人选择多难免有急功近利的做法;而另一方面,风险投资行业在中国还刚刚起步,随着创投队伍在短时期内的大量扩充,其中难免良莠不齐,有水平、有经验、熟悉中国本土市场的创投人士还远远不够,而这个行业也更多地还处于以游戏规则做事,而不是以准则和信条来做事的状态。
这一期我们先来看看“对外忽悠”的典型症状,下一期我们再着重看看风险投资人与创业者相互之间的“对内忽悠”。
“对外忽悠”的典型症状
对外忽悠的典型症状包括:“兑水”夸大融资数据吸引眼球、同行之间玩“击鼓传花”、相互抢单、忽悠二级市场投资者。
曾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某中国知名公司,上市前曾经在媒体上曝出三轮融资,其中包括2500万人民币启动基金,4000万美金A轮融资,“数千万美元”B轮融资,3000万美元C轮融资,但在上市前的招股说明书中,却显示创业者加上A轮融资的投资一共也投入了不过600多万美元,B轮融资也不过1200万美元,只有C轮融资与所公布的金额相差无几。
当然这其中可能有创投签约承诺与实际投资的差别,但是实际差距如此悬殊,不能不说是“大跃进”意识的结果。有这样成功者的案例在前,在很多人意识中“大即是美”,为了获得媒体注意力、社会公众以及合作伙伴的信任,企业你追我赶地刷新融资纪录,而在这背后给融资金额“兑水”似乎已经成了行业普遍的潜规则。
“这一年不仅被企业忽悠,而且也被同行自己人忽悠。”这是在一次创业论坛年会上一位投资人的慨叹。尽管很多投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投资功夫在前不在后”,但不少事例恰好相反,不少企业为了融资,堆砌概念,项目仓促上马,投资人只花两三个礼拜甚至更短的时间做尽职调查,之后发现问题,投资人再想办法“击鼓传花”吸引下一轮投资者,而被忽悠进来的风投如果不甘心吃这个哑巴亏,最终只能是把问题企业交给二级市场投资者——— 普通股民。
在投资高潮时期,对热门企业的投资不仅仅投资人之间相互抢单,而业界彼此间的生存状态也越来越紧张,同行之间相互隔岸观火、火中取栗、甚至趁火打劫的事例比比皆是,在风投间矛盾最为激烈的时候甚至也有为此对簿公堂。
3、真假天使投资人之辨
天使投资人被几度误读
大众对天使投资人最感性的印象,可能就是《非诚勿扰》里范伟那个有着漂亮女秘书、习惯用“母语”交谈的“天使投资人”——— 这也使得影片播出之后,有些业内人士在一段时期内多少不好意思再告诉对方,自己是天使投资人。而随着2009年离职Google中国的李开复创办“创新工场”成为普通关注的社会性事件,再度为公众普及了“天使投资”以及其扶持年轻人创业这一概念——虽然“创新工场”并不算是典型意义上的天使投资。
也是在2009年,曾被业内称为“中国民间天使投资第一人”的刘晓人陷落,也让人们看到了所谓“天使投资人”的另一面:不排除还有像刘晓人的红鼎投资一样,募集资金大部分是自周围人借来,对行业和企业缺乏了解,而真正用作股权投资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
即便没有资金链的问题,民间天使投资中“煤老板”、“80后富二代”的涌现,也引起了一些业内人士的担忧,他们甚至觉得这二者并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天使投资人”——而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正本清源的时刻。
台风来的时候,谁都在天上飞,正像网络上的流行语所说,“带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也可能是鸟人。”
中国的天使投资人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是否存在真假天使投资人之辨?
富人的游戏
“等咱有了退出,就不怕再投资,到时候想投网络投网络,想投芯片投芯片。一次投两家,一家投着玩,一家学经验!”——这是投资行业内对“俩包子,吃一个扔一个”的戏仿版。不过事实上,很多天使投资人都是来自于这种“退出-投资-培养下一拨企业家—下一拨企业家继续投资”的循环。天使投资者有三类主要来源:曾经的创业者;传统意义上的富翁;大型高科技公司或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者。
其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就是当年Sun公司联合创始人托尔斯海姆对Google两位年轻创始人的投资——“我听不懂你们的商业模式,但我还是先给你们一张支票,半年之后再告诉我你们在做什么。”而他开出的10万美元支票,成为了Google的首笔天使投资。实际证明,硅谷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良性循环体制的成功。
而在中国,在创建过程中曾引入风险投资制度、成功实现上市或退出的企业家,也为目前涌现出来的天使投资人的一种主流轨迹。———而因为是自己个人的钱,不受V C/PE投资周期的限制,也就使得天使投资人在投资时具有更多的艺术性和自由度,他不一定非要在什么时间急着花出多少钱,但也可能在短暂接触之后就为尚在襁褓中或脑海里的公司开出一张支票,而不必像VC投资那样要做较长时间的尽职调查。
但也正因为这种投资早期公司的“守护者”定位,天使投资的回报周期也会更长,毋庸置疑可说是“富人的游戏”。因此,用自己的、而不是借来的钱做天使投资成为最基本的入场原则,而像刘晓人那样用向周围人集资的方法,待到金融形势不好时,自然而然就走向资金链断裂,更是犯了天使投资的大忌。根据美国证交会(SEC)的规定,个人投资者的资产净值必须在100万美元以上或个人年收入20万美元、夫妇双方年收入30万美元以上,才有资格成为天使投资人。
炒房子最坏的结局可能是成为房东,但是做天使投资人,在大部分情况下其投资都可能是石沉大海。“如果到处都是天使投资人,那就不是天使,而是鸟人。”深港产学研产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厉伟告诫人们,“成功的几率几乎等于失败的倍数,所以千万不要把救命养老的钱拿来做天使投资。”
“给的不仅仅是奶粉钱”
而资金来源还不是主要问题。在曾投资过迅雷、康盛科技的周鸿祎看来,“必须要给整个社会澄清理念,否则就连创业者也分不清谁是真的天使投资人,谁是假的天使投资人。再出去说自己是天使投资人,还有人敢理你吗?”
在周鸿祎看来,真正的天使投资人应该有三点衡量标准:
“第一,投资者本人一定是创业者出身,自己做过企业,才能对企业的运作、特别是企业的成长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也有非常多的经验和教训”,这也是周鸿祎不愿承认那些拿着家里的钱做投资的“80后富二代”为“天使投资人”的原因。
“第二,天使投资人一定是针对某个行业去投资,并不是乱投,他一定是对某个行业和产业有比较深刻的理解———这就像保姆去带一个新出生的婴儿,有经验,才知道如何去呵护,不是就出个奶粉钱就完了。第三,天使投资人也要相当了解资本游戏的运作规则。”
因此,周鸿祎觉得,必须看到那些天使投资“传奇”背后的因素,“像SUN的托尔斯海姆,说是自己不懂Google的业务,他可能是看不懂细节,但他肯定相信公司未来的方向,否则也不会去投钱。”
而除了为公司保驾护航、为其战略发展出谋划策之外,出于感情的因素,天使投资人有时也愿意在待人处事方面给出自己的意见。比如一档很有影响的商业节目以“80后创业”为题邀请康盛的戴志康做嘉宾,周鸿祎的意见就是,“能不去就不去,如果没办法,一定得去就一定坐台下,不要坐台上。发言的时候一定要多讲自己的企业,多讲自己的产品,少讲个人。”周鸿祎的理由就在于,“一个企业家的心态如果不能摆正,还没有成功就以为自己成功了,天天在聚光灯下发表演讲、在舞台上秀自己,这样的人是做不好企业的。”
当然,也有天使投资人强调对创业企业不过度干预,或者天使投资人不一定非得是企业家出身,但其要对产业方向、格局有深刻的洞悉与认识,可以为尚在襁褓阶段的企业提供相应的资源与经验做支持,这是成功的天使投资人必须具备的素质。
也有业内人士提出,托尔斯海姆对Google的完全放手,实际上也是基于大环境的成熟:“在硅谷,你做什么人们都知道”。而在具有中国初级阶段特色的时期,不仅股权投资整体的诚信环境需要完善,创业企业支持系统的不完善也使得很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希望能让天使“扶上马再送一程”,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与经验。包括其后如何引入VC,在很多情况下天使投资人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天使”尚未形成气场
事实上,目前中国正需要成熟的天使投资人来推动创新与商业转型。数据显示,天使投资在美国所占投资总体比例为40%左右,而根据中经合董事长刘宇环的估计,在中国这个比例可能连4%都不到。———换句话说,在目前98%中小企业依靠借贷来生存的中国,也的确需要形成天使投资人的气场。
初创企业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时候,有时会开玩笑地说,“从街上拉个卖菜的,只要能给钱,就给股份。”———但往往越到这个时候,卖菜的越不敢轻易给企业掏钱。
“中国的大部分投资是财务性投资,看人家企业活得不错了,或者快上市了时投资,两三年之后IP O就把钱赚回来了。在项目前期、在企业刚刚创立时,就敢往里投钱的,没几个人,因为没有那个判断力。”在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看来,目前的中国更需要的是天使投资干这种“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而从另一角度来说,除了看清基本发展形势,很多天使投资人也更强调对团队与人的了解和信任,前期接触时间短、企业早期产品和服务还不成熟,在这个时段也注定了“人”的因素更为重要,这也是很多天使投资人在自己周围认识的圈子里选择投资对象的原因。A 8音乐集团董事刘晓松在十年前投资腾讯的时候,后者只有十名员工,连一台像样的服务器都没有,但是这笔因为“信任”而来的投资事后带来千倍回报。
虽然投资回报率高,但是同样高的失败率也使得很多天使投资人在拿钱的时候,并没有抱着非要“一击而中”的想法。不少天使投资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投资失败就当是给社会做贡献了。”
而事实上,正因为天使投资是在企业早期“共患难”的时刻,不同于VC投资有激烈的竞争和更明确的利益分配,天使投资的气场更为“和谐”———大部分天使投资人都愿意叫上更多身边的朋友做联合投资,在共享资源的同时也能降低自己投资的风险。
4、“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
“风投干的活也不难,投资时拿的是LP的钱,之后有协议就能靠企业家了。”———此前我们曾提到有创业者这样评介风险投资人的工作,但他们的工作果真是这样简单吗?他们又面对着怎样的近似于“成王败寇”的现实生存法则?如何衡量风险投资人的成功与失败?哪种成功令人江湖上“一战成名”?又有哪种失败必须要有人为此负责而导致一招失手、退隐江湖?
经典“传说”是怎样炼成的
如果说以1993年IDG开始在中国成立风险投资基金算是中国创投业务正式拉开序幕,而以2003年、2004年随着新经济的复苏,风险投资在国内再度活跃为“风投2.0”的时间起点(也有以国家正式出台法律法规鼓励创业企业投资、扩大外资创投的空间的2005年为时间点进行划分),最初十年出现在国内的第一代风险投资人,经历“大浪淘沙”留下来的精英已经寥寥无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随着2000年前后互联网的崩盘,很多投资人也与创业公司一样没有熬到“剩者为王”的一天。———这就是风险投资行业的现实性,不能赚到钱,VC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石。
衡量一个风险投资人的最重要的指标,就在于其基金能否赚钱。———但是除此之外,就像红杉合伙人迈克尔·莫瑞茨这样为业界所钦佩的人物、或是被大众视为“传说”的投资案例,总还有其他的因素。
除了对行业的独到眼光与深刻理解、敢于判断的决心、甚至包括反潮流的勇气———这期间还有时间因素在起作用:要经历时间的磨砺与积淀,除了一次又一次被证明决断的正确性之外,在低潮期有“中流击水”的勇气,也相当重要。借用莫瑞茨的话说,当人们都恐惧地趴到桌子下面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投资时机。
数据显示,腾讯、百度、阿里巴巴、分众等这些高回报率的投资案例都是在低谷时期投资的。当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行业被公认有发展前景、投资人彼此间竞争进入企业的时候,往往并不是经典案例横空出世的时机。
比如2003年2月软银亚洲对盛大的投资,因为这种中国特色娱乐方式刚刚在国内兴起,对于不少风险投资来说,网游还属于看不懂的“行业”,甚至有风投承认自己当年对网游企业采用的是避之则吉的态度,而更为严重的是,盛大正处于与韩国开发商A
ctoz就版权问题诉之公堂,如果不能妥善解决,甚至会威胁到盛大的运营权而导致游戏停运。
当时盛大所要求的投资金额至少是3000万美金,在做了充分尽职调查之后,软银团队帮助盛大调整了组织架构、管理架构,制定了管理层回报机制,财务预测,财务监控制度,而且在盛大与韩国开发商Actoz的和解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终软银的4000万美元投资获得了5.6亿美元的回报。
如果单纯从投资回报率的角度,在后来的投资案例中超过这一数字的大有人在,但为什么这一单成为经典,在于软银亚洲的投资让人们看到一个以往未被充分认识的行业,而且风投也用自己的资源帮助了创业公司,在这家公司最有风险的时候,敢于承担风险,这些因素、包括戏剧性的对比都是多年后读者仍对此案例津津乐道的主要原因。
一战成名的经典案例,似乎往往都带有这样一些“吾往矣”的反潮流特色,比如孙正义对阿里巴巴的投资,比如前不久在创业板上市的福建圣农,在2006年第一次融资的时候也正值禽流感流行,而达晨投资在那时大胆进入,在三年后为自己获得了近十倍的投资回报率。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几乎绝大部分的风投都会承认,投资有运气的成分在,“有时寄予厚望的未必能如愿,有时来临的巨大成功则令你想象不到。”
能与不能承受的“失败”
以风险投资的工作性质来看,遇到投资失败的案例是家常便饭。有这样一组数据,风险投资的案例中,有90%以上的企业以失败解决而告终,0.5%的企业能实现IPO,2.5%的企业会以比当初高的价格卖出,5%的企业只是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因此几乎没有风投可以担保说,自己没有失败的时候。———但是,这其中却有可以承受与“不能承受”之分。
对投资人来说,可“承受”的失败一般有两种。一是该投的没有投,该把握的出手慢了,这是一种机会成本的浪费,也是令投资人压力比较大的失败;而另一种属于大家都摸不清情况的时候交了学费;比如最早对专业的博客网站的投资,风投的尝试几乎全线覆灭,———但是在投资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知道门户网站后来居上有如此猛烈的“剿杀”势头。
又比如视频网站,投资人名单上几乎涵盖了中国大部分知名创投基金,但是最后胜出的也不过两三家。———虽然中国会有自己的youtube,但是不知道具体会是哪一家。这种对新行业,因为很难判断随后的形势,再加上投资的金额一般在百万美元级别,失败就基本属于可以承受的范畴。
而另一种失败则可能属于每个投资人的噩梦,即“数额特别巨大”(一般在几千万美元的数量级)、“性质特别恶劣”(一般来说不仅仅是市场形势、或者企业自身运营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欺瞒、伪造等诚信层面)、“影响特别严重”的--风险投资人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圈子,有些投资失败案例往往在圈内很难被隐瞒,但是后一类失败基本上是在已经被社会大众所知的范畴,比如我们此前曾提到的,企业创始人携款潜逃、或者上市CEO大规模挪用资金而导致公司退市,简而言之,就是属于失误在不该犯错的环节,这时的后果往往就导致有投资人要为此“被负责”,而通常的结果,是负责人离开这只投资基金。
5、中国式LP与GP的纠结关系
随着近年来人民币的风生水起,正在形成中的本土LP(有限合伙人Lim itedPartner,指基金的提供者)群体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人视线当中;而他们与GP(一般合伙人GeneralPartner,指基金的管理者)之间所进行的磨合,也颇具中国特色。
经常可以听到不少风险投资人在公开场合呼吁L P多放手。事实上,与西方经历长期发展时段、处于成熟期的LP运作模式相比,本土LP很难像国外同行一样做到“长期持有、不参与投资决策”,而他们对投资的介入,也就是行业内通常所说的“LP角色G P化”,不仅使一些G P头疼,在很多时候也给被投资企业增加了负担。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本体LP们似乎也有自己的道理,“钱是我出的,为什么我不能说了算?”“有的G P只是70后,比我的商业经验还少,为什么我不能给出自己的意见?”
在网络上,“LP”也是另外一个名词“老婆”的缩写,因此,也有创投界人士开玩笑地称,“目前中国的G P都是‘妻管严’”———而在目前国内,也可以看到不少出资人与管理者最终由不和走向劳燕分飞的事例。
可以说,中国的G P与LP,正在相处磨合中学习和谐之道,而这不仅是现阶段中国商业环境中的必由之路,也对无数创业企业的走向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LP“当家作主”
“你每年要收取一定比例的基金管理费,要是不能帮我赚钱怎么办?”“你把钱拿跑了怎么办?”“凭什么我的钱我不能做主?”这是一些风险投资人在募资时经常要遇到的来自民营企业家的问题。而这个时候,如果仅仅解释国际惯例就是LP出资之后不参与管理,通常很难令对方满意。
而这是否能一味地归罪于“土财主”们守财而不具备国际视野?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西方的LP之所以可以做“甩手掌柜”,不插手基金的日常投资决策,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整套法律体系的支撑与监管;此外,“信托”观念在西方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与此相对应的商业文化、诚信道德理念都经历了时间的积淀与考验。而在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以及诚信商业文化尚待完善,都不得不使很多LP在掏钱的时候“多留一个心眼”。
此外,中国创投行业刚刚起步,还没有培养出大批合格的风险投资人,很多本土L P也会觉得一些60后、70后的G P资历尚浅,其所称的“G P专业化”程度很难令人信服,对企业的了解可能还不如白手打拼的自己,而在近两年金融遇冷募资吃力的情况下,一些LP的强势话语地位也就顺理成章。
据了解,目前本土LP往往采用这样一些形式来参与经营与决策:或者是LP方人士在投资决策委员会中占一定比例,委员会实行投票制,开会变成“双边谈判”;或者LP自己设立一个专家咨询委员会来监督G P的投资,如果专家咨询委员会反对,投资项目就可以被否决。
GP被LP意志所左右
而这种LP意志,往往也影响到基金最终的投资方向和投资时间。在谈到为什么风险投资喜欢投Pre-IPO企业,而投资原创、高科技初创型企业不多的时候,就有业内知名G P表示,“投资企业时间的长短往往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是被LP的意志所左右,他们的资金很难容忍三五年以上的投资期。”
与西方被称为“O ldM oney(老钱)”的家族基金、教育基金不同,一般风险投资基金投资回报周期在七到十年左右,而目前中国国内的民间资本很多都希望赚快钱,所以倾向于做“短平快”项目,G P在选择项目的时候,也往往只选择本土LP看得懂的项目,而这种情况时间一长,则更容易形成跟风与行业浮躁的氛围。
针对这种情况,业内人士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LP大众化倾向有害”,大量私人的、做短线的资金在行业里,肯定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当设立相应的法规门槛,同时对其进行风险教育;但同时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政府还应该进一步放宽宏观政策,并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创投行业。
其实,中国式LP的不成熟也未必都归因于民间资本,也有风险投资人深有体会地说,如果LP是国内大型国有机构,更可能出现领导一换就变卦的情况。
期待“不差钱”LP入场
除了相关部门完善法律法规,LP与G P之间建立科学的管理与激励机制、并逐步以时间的积淀培育起相互信任的基石,说来说去,很多事情还是与“钱不多”有关———这是指真正有实力、“不差钱”的资本,因此,国内创投界也期待能有更多的长线基金入场。
在目前情况下,LP在中国主要可以分成三大类,一是社保基金,而未来保险、银行及企业资金均有可能成为重要LP集群;第二类是政府引导基金;还有一类就是富裕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民营企业家把实业界积累下来的财富向股权市场转移。
而国外的L P则包括养老基金(包括公共养老基金、公司养老基金、工会养老基金)、国家主权财富基金、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组合基金、捐赠基金、家族及富有个人等众多来源。因此,业内也在呼吁中国LP结构的多样化,有行业人士甚至给出这样一个数字,LP基金中的长线基金(比如社保、保险)比例达到50%以上,才可以视为是国内创投行业真正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