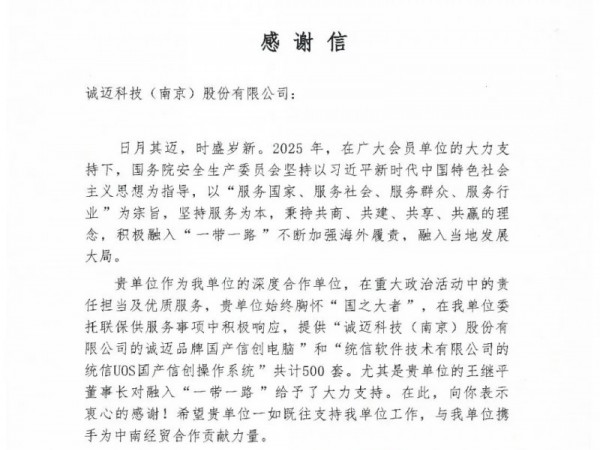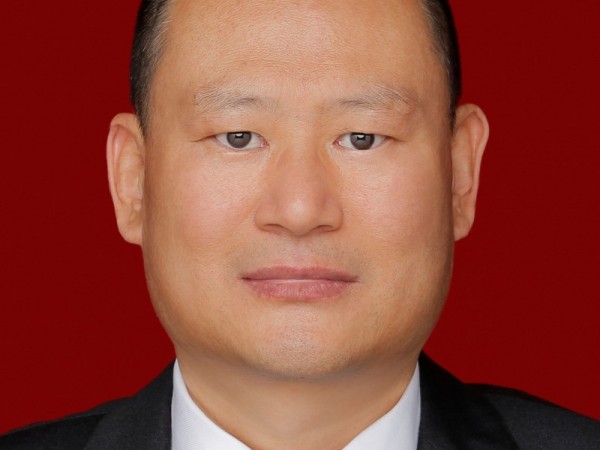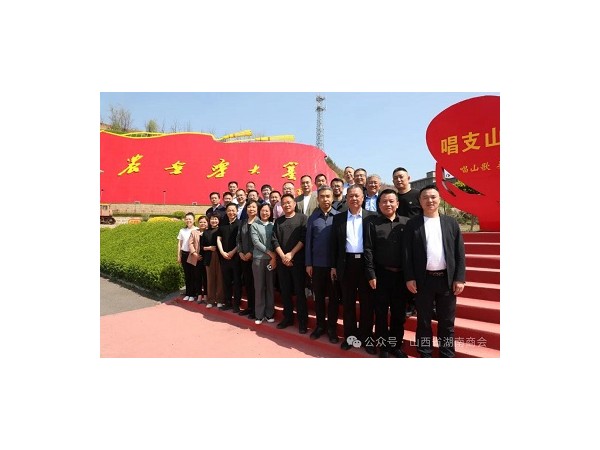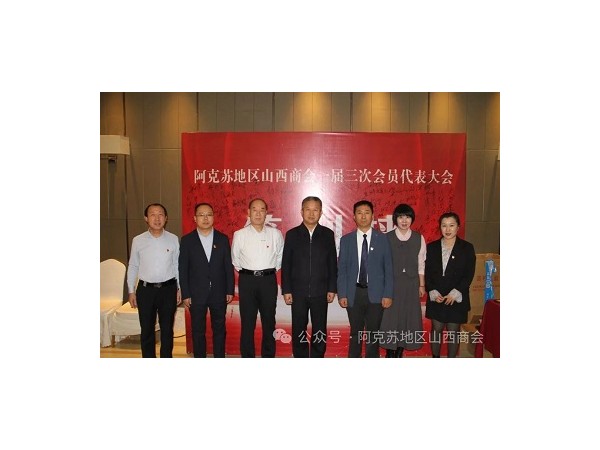收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行动。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收集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的东西,收藏意识一直有,一直在做。四十多年了,保守一点讲,应该从1966年算起—就是我九岁那年收藏的第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些传单,再往早算,是那张为了不让小朋友知道我父亲名字而把父亲的名字撕掉的幼儿园成绩单。
虽然一直在收集,但是范围很窄,量也不大。很不容易找到一件“文革”时的东西,很不容易找到一件“抗战”时的东西,因为没有市场,没有买卖。古玩市场兴起的时候,也只卖唐宋元明清的东西,近现代的、抗战时的很少。改革开放以后,进入90年代才开始好起来。从1990年到现在,才叫收藏。以前就是要,就是检。你认识一个人,就跟他要,不认识,就找不到东西,水远找不到,你可能总共认识一千个人,一千个人里边最多十个人会有东西,而他要给你,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一个国家,收藏没有市场的时候是很可怕的。

搬家是90年代开始的。我收东西是靠全民大搬家,那些东西噼里啪啦地全出来了,搬家太愉快了。中国每一个家庭可能在这二十年间都搬了一次家,有些还不止一次。搬家,总得搬掉一些东西嘛。大搬家时,我就拼命检“破烂”。比如,90年代初收购宣传画,每次赶场要买二三捆,手提肩扛,满头大汗。开始,许多收藏界人士认为我不入流,找却从头到尾笑嘻了,现在他们才明白,一般文物的价值十年增长十倍,“文革”文物是十年增长五十倍,三五元一张的幸福维持了七八年,价格转而扶摇直上。

90年代以前就三个渠道: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向亲友要,第三就是在垃圾堆里捡,1990年以后就有点市场的感觉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年,一下子就有市场,有拍卖了.我买了些很好的东西。
有了市场,可以逛地摊了。成都古玩地摊可能只输给北京。从1994年到现在,我淘了二十多年地摊。逛地摊很快乐,是会上瘾的。首先是结交五湖四海的高人。其次是捡漏,有次我只花了两元钱就买到了宋哲元将军的家谱,高兴得不得了。再次是地摊的无拘无束、自由交易、琳琅满目,让你幸福而不觉时光流逝。有市场是个很幸福的事情。
我的收藏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收藏梅兰竹菊,春花秋月,才子佳人,我收藏的大多是些火爆爆的东西。“文革”遗书我收藏了很多,一般人都不忍去看。另外,这二十余年我检了两万余本日记,时间将证明,这是更有价值的藏品。我是想保留一些历史的细节,我想,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社会肯定是有用的。
刚开始觉得把一件事情搞清楚很好玩,慢慢一件件事连起来,越来越觉得好玩,觉得幸福、快乐,就跟吃鸦片一样丢不下了。然后觉得还不够,还要查更多的资料,读更多的书,收集更多的文物,了解更多的事情,就这样进去了。我收藏文物有三个标准:一是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二是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三是标志性的,反映社会变迁的。

我常常想.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十三亿人中的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同样也需要每个人都承担。作为我来讲,经商有了一点资产有了一点钱,我想做一些事。以前是东一件西一件地收藏,单枪匹马地干,是一种爱好,这时我利用在全国建立起来的网络收集,变成了责任。我这样做,对自己是一种满足,我实现了理想、愿望;对社会也有一些帮助。所以一旦有值得收藏的战争文物,我会在第一时间前往。

建川博物馆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宋美龄家属们赠了宋美龄穿过的旗袍;四川黄埔同学会捐赠了军校课桌椅凳三件套;我向开国大将罗瑞卿的长子罗箭少将,要来了一床缴获日军的毛毯。毛毯在艰苦时期包裹过刚出生的罗箭,跟了罗箭七十多年,一直都在用,老人很不舍,但还是拿走了。我们建博物馆、收藏文物是为了记录和还原历史,但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还是为了让每个人的心灵都直面民族创伤,让战争的记忆成为民族的思想资源。

为了选择落户的地点,我去北京、上海、重庆等很多地方考察过。因为我是房地产商,他们认为我是骗他们的,五百亩拿到手,二十亩用来建博物馆,剩下的四百八十亩用来搞地产开发。所有人怎么也不相信建博物馆需要五百亩地。领导们觉得我是在圈地,以建博物馆的名义忽悠他们。后来,大邑县相信了我,五百亩地全部用于建博物馆。

建川博物馆落户安仁,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天意,老天爷安排的事情,一个人想努力是办不到的。大邑县安仁古镇,是“取仁者安仁之意”而名之,始建于唐朝。安仁镇的人文环境和博物馆一脉相承,一是安仁公馆群是民国建筑,与百年收藏吻合。二是刘湘是抗战名将,它又是一个抗战之镇,与抗战系列馆吻合。三是2003年时,只有安仁镇能拍到五百亩地,安仁镇是历史文化名镇,建筑高度不能超过十三米,这样永远没有烟囱、高楼来压迫博物馆。

我们相信安仁这个项目肯定会载入史册,哪怕有一天我们离开
安仁,人们也还会来安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