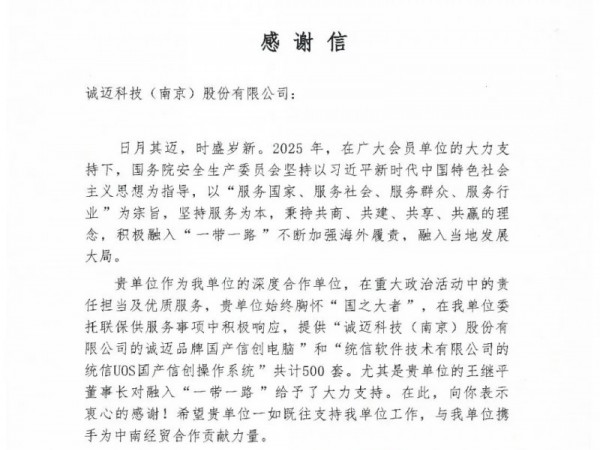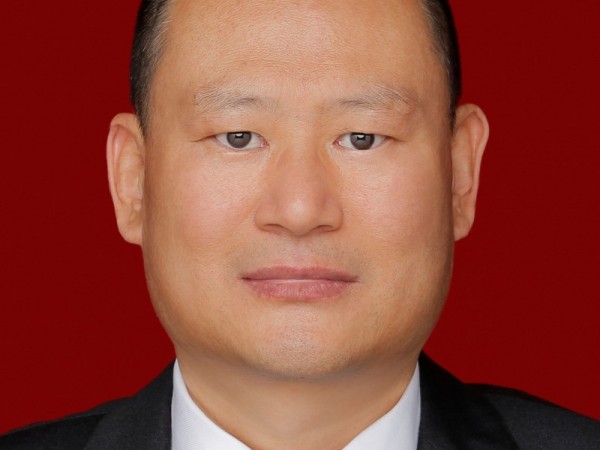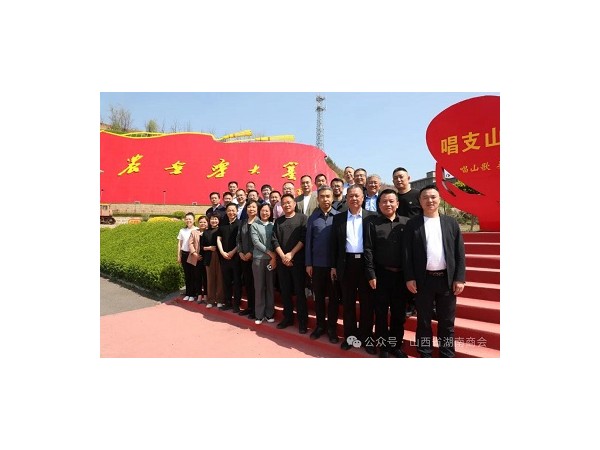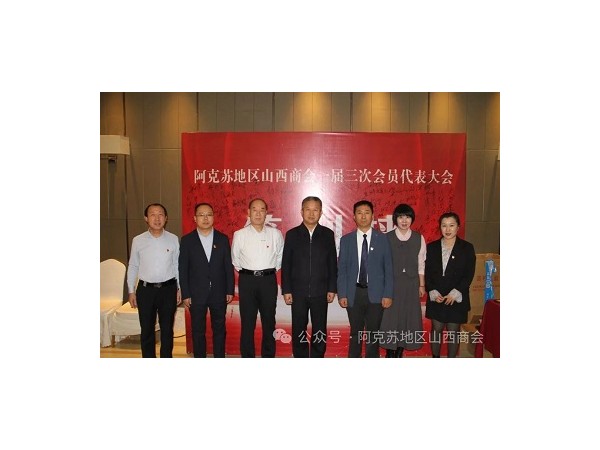2012年10月15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美国经济学家罗伊德·沙普利(Lloyd Shapley)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诺贝尔奖英文网站中,我们得知罗伊德·沙普利与中国渊源甚深,他曾在二战期间在中国西部成都服役。我们设法与罗伊德·沙普利的儿子取得联系,得到了珍贵的口述和图像资料。去年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建川博物馆开始为40位援华助战的外国义士塑造铜像。今年3月10安装完毕,而入选“援华义士广场”的罗伊德·沙普利先生就在3月12日溘然长逝,谨以此文回顾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在中国的抗战经历,并向所有援华助战的国际友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图一,罗伊德·沙普利在诺贝尔奖颁奖晚会现场。

图二,建川博物馆援华义士广场内罗伊德·沙普利塑像。
一、科学世家 天赋异禀
1923年6月2日,罗伊德·沙普利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个科学世家,在五个孩子中排行第四。他的父亲,哈罗·沙普利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曾担任哈佛大学天文观测中心主任。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沙普利年幼就展现出数学天赋。
他这样回忆他的幼年时代:我的两个哥哥都聪慧过人,成绩优异,我的姐姐,我猜也相当聪明。不过我们有时会玩一些数学的游戏,比如计算扑克牌上的数字,在这方面我总能胜过大我四岁和六岁的两个哥哥。所以我有点数学方面的名气。
他在菲利普·艾克赛特学院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读本科,在数学上的表现突出,超过其他科目。1943年,大学三年级的他应征入伍,服役将近三年。

图三,后排左起:罗伊德·沙普利的哥哥阿兰、威利斯,父亲哈罗,母亲玛莎,怀中是弟弟卡尔,姐姐米尔德里德。时年六岁的罗伊德站在前排。摄于1929年
二、应征入伍 秘密来华
沙普利入伍后,首先被送到北卡罗来纳州的新兵训练营,进入那里的气象学校,进行了为期十周的气象学习,绘制并分析气象地图。之后他与所在部队乘火车跨越美国版图,在圣地亚哥附近的一个基地停留一段时间后,乘运兵船驶向未知的战场。
途中,沙普利运用手表以及自制的简易导航工具,在部队墙上的地图中标记运兵船的位置。因为公开绘制船只的“秘密”位置,沙普利受到了训斥。于是他将地图取下,但继续测绘船的位置。几周之后,他准确的判断出他们首先停靠的地点是塔斯马尼亚的霍巴特。终于,他们在印度登陆,乘长时间的火车之后乘DC-3客机飞越喜马拉雅山,最终到达了中国西部。
因为部队要对他们的行踪保密,士兵的一切信件都要经过审查,所以沙普利甚至不能告诉家人他在哪里。为了让他们知道,他写了些关于“查理叔叔”的事情,这不会引起审查人员的注意,但足以使家人意识到这封信所传达的并不是字面上的信息,因为家里根本没有一位“查理叔叔”。罗伊德的哥哥威利斯发现了这信中的奥秘,信中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母连起来是“C-H-I-N-A”(中国)。
三、首立军功 铜星嘉奖
当时沙普利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团的一名一级二等兵,随部队驻扎于一个位于中国西部的秘密军事基地。在1992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这样回忆:“(那是)一个负责截听无线电的气象站。气象站需要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沙普利工作的气象站不但进行气象观测,也负责截听无线电报。
由于援华的美军轰炸机部队需要从印度运输燃油和导弹,每两周对日本进行一次轰炸。轰炸机中途不能在中国境内降落,这样会落在日军轰炸机射程之内。因此,轰炸机部队需要提前三天知道目标地区的天气情况。作战前线从西伯利亚南移,经过中国,到达了日本。气象中心截听的无线电波来自苏联和日本,有时甚至来自太平洋上的美国海军。沙普利所在的气象战需要分析大量的数据,而通常大多的数据质量都很差。于是他们将所能收集到的全部数据绘制成气象地图,并进行长期的气象预报,然后根据需要发送至各个机场。
沙普利最终成功破译出了苏联的气象密码,使部队得到了更加准确可靠的数据。他在访谈的文章中提到:“这个基地初期也参与一定的密码分析工作,并不是一定要破译。不过后来出现了紧急情况需要破译密码,因为我在部队的智力测试(IQ)中成绩很高,这项任务交给了我。后来我破译了一组苏联气象密码而获得了一枚铜星勋章,同时我升任下士,也就意味着我一个月开始拿56美元,而不再是52美元,所以我在很低的职位上,升得很快。但那毕竟是一项成就。”除了军功的荣耀,在艰苦的抗战岁月,每月加薪的4美元对沙普利也有极重要的意义。

图四,罗伊德·沙普利因破译苏联的气象密码而获得铜星勋章(Bronze StarMedal)。
四、休戚与共 抗日援华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与对日本的作战。1942年5月,日军切断滇缅公路这条战时中国最后一条陆上交通线后,中美两国在印度东北部和中国云南间开辟了一条转运战略物资的空中通道,成为了抗战最艰难时期的空中“生命线”。这条空中通道因飞行轨迹高低起伏状似驼峰,故叫驼峰航线。沙普利回忆说:“我们去中国得飞过缅甸和喜马拉雅山,那时候叫“飞跃驼峰”(flying the hump),“空运”(airlift)这个词还没发明。”

图五,抗战最艰难时期的空中“生命线”—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有“死亡航线”之称,航线跨越喜马拉雅山脉频繁遭遇强紊流,强风,结冰,设备老化等难题,因此在航线开辟后的三年间共损失594架飞机与1659名空勤人员。首批B-29轰炸机在1944年4月24日飞越驼峰,抵达中国四川成都专为B-29而建的机场。
沙普利对这段历史有相当详尽的回忆:“部队在试用新型的B-29轰炸机对付日本,比过去的轰炸机大一倍,或者至少有欧洲战机的两倍大。它们没有经过正规的测试就被生产出来送到中国了。先到印度,再飞跃喜马拉雅山。所以部队在修建一个巨大的机场,就在我们基地旁边,有数十万名中国工人在那里工作。让我想到了修建金字塔的情景,人们排着长队,手提肩扛。没有水泥一类的东西,尤其是没有机械——这就是内陆的中国。但是有充足的人工,以及众志成城的决心。那是用鹅卵石铺了两英里,才能负担当时最重的飞机。因为我们抗日,所有人都喜欢我们。

图六,1943年民众拉水泥碾子修筑新津机场,后面起飞的是美军的B-29轰炸机。
所以那是一个大的建筑工程,最后建成了美军20航空军。当时的指挥官是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后来他成了美国空军总参谋长。他们最终集结了100台轰炸机,有四个机场,包括我们那一个。所以我们基地有20架这种庞然大物,负责轰炸日本东部,后来是朝鲜和满洲,时间大概是与诺曼底登陆同时。
我们的上校指挥官,定期会向柯蒂斯·李梅汇报天气情况。记得有一次,海军发现有飓风正在以正常的速度行进,关键在于它是否会转弯,会在什么时间怎么转。结果海军失去了飓风的消息,只给我们发了一个坐标。飓风很可能已经转弯了,可我们无法预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得告诉他们“走或者不走”。我们的指挥官咬紧牙关,说“飞吧,我想”。结果是部队飞到长崎的过程中,几乎都在飓风中心眼中。幸好没有人员伤亡,投下的炮弹被卷进飓风里,也可能卷到了海岸上,飓风造成的破坏比我们能做的大多了。当时有很多这样的轶事发生。”
五、心系中国 荣誉一生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沙普利随即退伍,几个月后重返哈佛校园开始新学期课程。沙普利是哈佛1944届毕业生中第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不过因为2年多的援华抗战经历,他并没在1944年毕业,他毕业于1947年6月。
回忆自己这几年的兵戎岁月,沙普利说:“这是一段有趣的经历,远比我期待的好得多。我以为自己就是被抓壮丁,实际上我还是发挥了一点自己的专长。”作为经济学家的沙普利曾在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工作多年,那也是他在哈佛毕业之后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沙普利说:“我在兰德公司应聘时,有人因为知道我曾经业余做过密码分析而帮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所以那是我事业的开始。”
沙普利的抗战经历让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从那时起,在中国的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我一直关注远东,尤其是十年前中国重新开放(改革开放)之后,我又去了几次。”他的儿子彼得·沙普利也在邮件中告诉我们,在中国的经历对他父亲的人生有着“重大的影响”,他一直喜欢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沙普利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多年,一直有来自中国的学生。

图七,2012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合照。前排中间为沙普利,右一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
2012年,诺贝尔奖再次将沙普利与中国拉近。他与美国经济学家埃尔文·罗斯分享经济学奖的同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今天将此文献给这位曾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的援华“老战士”,愿他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并希望他的抗日事迹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所铭记。

图八,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向客人讲述沙普利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