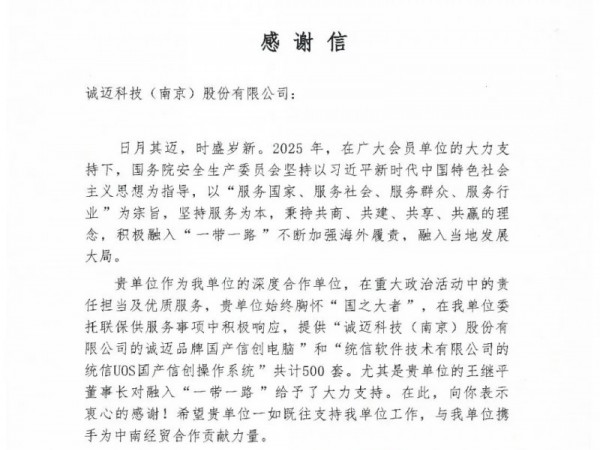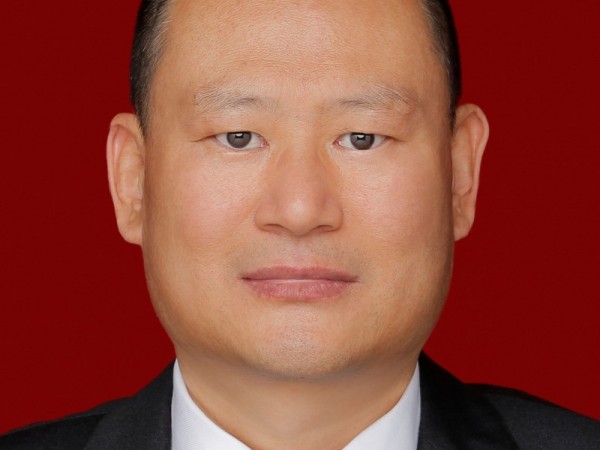当人们在谈论全球化的时候究竟在谈论什么?
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到当下互联网科技的方兴未艾,全球化是纵贯世界史的一个重要主题。随着距离的缩短,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摩擦也被随之放大。在多种力量的交融和博弈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开始褪色,被隐藏的不公开始被看见,黑暗中的弱者已从幕后走到台前。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重心也从政治利益和军备竞赛转变为建立世界范围的“福利国家”。
当下,全球化的潮流,已不再是殖民、剥削和制造悬殊的共谋,而是反抗、协作和实现双赢的同盟。与此同时,互联网作为无界的虚拟公共空间,真正实现了突破时空界限的全球连接,因此,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也成为一个绕不开的热门议题。本期全媒派独家专访国际政治学家贝朗特·巴迪、清华大学崔保国教授,为你揭秘全球治理新洞察及互联网空间治理新趋势。
被放逐的与被颠覆的:当代全球治理新变

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巴黎政治大学教授 贝朗特·巴迪(Bertrand BADIE),曾作为东京大学、莫斯科大学、柏林大学、日内瓦大学等35家世界知名大学的客座教授,出版专著11本。
“我们正在为过去不近人情的国际格局付出代价。”巴迪教授一针见血地说道。
20世纪下半叶,殖民主义虽然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超级大国们依然对相对落后的南半球国家不屑一顾。在后殖民时代的头30年,“弱国无外交”确是真理: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甚至被完全驱逐出国际政治的游戏场。不管是政府间的国际合作还是为全人类谋福祉的全球性事务组织,人们看不见南半球国家的身影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幸而,流血的伤口终于变成了盔甲,流放者集结起新的力量。
颠覆者的春天来临了
1945年,联合国成立,彼时有51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但几乎所有初始成员国都来自北半球或是他们的“飞地”;到了冷战时期,两级对峙,谁也没工夫搭理世界南部的落后国家;再后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霸主消失了,国际格局变得混乱不堪。
此后,不管是横行了几个世纪的欧洲中心主义还是曾经剑拔弩张的两极格局都彻底成为了明日黄花。大国缺位,国际秩序再次面临重新洗牌的时局,而网络信息的流通,又使既得利者与被剥削者的巨大鸿沟大白于天下。

新中国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
过去我们对南半球国家的轻视正在反噬。即便在东西方两大阵营握手言和的时刻,也没有人想起邀请南半球那些弱小国家来参与。这种做法无疑激起了一种被羞辱和被排挤的痛苦感受,终于局外人的身份惹恼了他们,这些曾经的流放者已经进化为叛逆者。
巴迪教授认为,悖论在于,大部分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比如健康、安全、经济发展等等,都发生在南半球,但解决方案的决策权却被北半球的发达国家所垄断。这种割裂的运作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轻则南北半球的国家们互相埋怨,重则双方矛盾激化,两败俱伤。
“必须让国际问题的当事人发声,不然所谓的全球治理就是痴人说梦。”当下国际争端的主要发生地在南半球而不是过去的旧中心,发展中国家正在掌握主动权,而发达国家却逐渐陷入被动。如果看不清这一点,还妄图使用武力压制,恐怕会铩羽而归。
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各国必须学会解决新问题和新冲突。国际舞台的聚光灯打在欧洲大陆上几百年,现在却向中东、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部分)转移。
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谈论政权和军备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更关注国际社会中的发展问题。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的7项国际安全问题:食物、健康、环境、经济、数据、文化以及政治。在这个进程中NGO、媒体、科技、宗教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世界局势将会呈现新的面貌。
全球治理是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
“这种说法是赤裸裸的诽谤!”巴迪教授的掷地有声地反驳道。
西方国家对强调权谋和武力的“政府间外交”有根深蒂固的偏爱,因此有人认为互利共赢的全球治理无法实现。曾经,人们将国际政治舞台视为主权国家(Inter-state Strategy) 的天下,而非政府因素(Inter-social Strategy)只是民主化进程中微不足道的配角。这种执念滥觞于凡尔赛体系,随着发展中国家新主角地位的确立,以及对自主权的争夺和捍卫,它已经成为过时的误解。“旧世界的逻辑崇尚弱肉强食和攻城略地,新世界的原动力却来自改造落后国家和地区。”在这一过程中,相关各方的团结协作至关重要。

科菲·安南
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科菲·安南曾经说,如果我们想要成功维持和平局面,第一步就是必须接受新的世界秩序,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共谋发展。此言得之。
从微观上看,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向心力(Social Integration),社会机制就无法良性运转;从宏观上看,这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
如果国际社会的凝聚力不足,动态平衡就会打破,世界局势就会面临分崩离析的风险。“我不否认政治和军事冲突依然存在,但它们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巴迪教授强调,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在食物、健康、环境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悬殊才是暴动与反抗的根源。做个简单的比较,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开启现代化进程之后,目前的人均GDP已经超越了6000美元,但非洲的人均GDP还不到1000美元。仓廪实而知礼节,物质的极端贫困根本无法发挥人文主义对社会的有利影响。
互联网的发展更是火上浇油。
50年前,贫困者对富裕者一无所知;落后者对强大者全无所闻。那时,贫穷并不会引发国际层面的暴动。随着全球传播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穷人每天都看着有钱人上演炫富的戏码;被剥削者也了解既得利益者的安逸生活。现在,资源匮乏就是国际社会动荡不安的源头。尤其,人们一旦意识到鸿沟,就会构建对立——这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身份焦虑 (Identity Tension)的讨论。例如,白人相对强势,而穆斯林、有色人种就容易受到歧视和虐待。这也解释了为何中东与非洲成为了当下全球版图中的火药桶。人们因为宗教、肤色、人种、家乡而受到不公的待遇,而这些身份标签已成为国际冲突新的导火索。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些成果。50年前,非洲有八百万饱受饥荒折磨的难民,现在,这个数字没有改变,可是非洲的总人口数是之前的两倍。
巴迪教授认为,发达国家还有巨大的改进空间,与其把军队送到亚洲和非洲的土地上,不如学着用正确的方式应对冲突。
误解与分歧:互联网空间治理探幽
崔保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清华-日经传媒研究所所长。
在多层次中寻求对话
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变革使得互联网日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上升,已成为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大国越来越重视对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但由于技术为主导、虚实结合等特点,互联网治理又具备一定的复杂性,加之全球互联网治理缺少一个政府,只依赖于各国的协商,没有强制力,因而在具体的模式制定上,很难达成全球范围的意见一致。
崔保国教授认为,互联网治理有层次之分,各国在互联网治理上的分歧是由于相关方并未在同一个层次上对话。互联网治理大致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硬件层次,例如谁可以经营互联网这类问题;第二,逻辑层次,主要指的是使用者签约的互联网协议;第三,应用层次,即经营互联网的企业是如何签约的;第四,内容层次,许多互联网产品并非是全球通用的。
在技术层面上宽松,以推动为主,在内容层面上严格,以管理为主。我国与其他国家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有所分别,后者可能本就将技术与内容的管理等同理解,也可能与我国做相反的管理。
同时也需指出,目前很多人会把互联网治理与网络空间治理混为一谈,但二者有一定区别:互联网治理更多的只涉及互联网这一个空间,而网络空间治理的层次则更为广泛,崔教授举例:“支付宝的发展就不只有关互联网,还包括很多金融领域的问题。”
有关互联网治理的问题总是充满矛盾,云端博弈不停息。因此,当我们谈及互联网治理时,需要实现对治理的层次做出分别,不分层次就难以在同一个频道上对话,也就更妄谈解决分歧了。
在多主体中达成合作
在新的互联网空间秩序的重建过程之中,参与其中的不只是传统的主体——国家政府,包括科技公司、非营利组织等在内的非政府主体也逐渐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也许有人质疑互联网治理会将其割裂而违背互联网诞生的初衷,但这种看法的立场或许过于理想。互联网由技术社群开发,其诞生伊始确实强调开放、分享、去中心化,带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1996年,《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中宣称在网络世界是追求自由的人的一片新家园,这里没有国家主权,不欢迎政府的介入和控制。但到了九十年代末,互联网商业化的潮流无可阻挡,技术人员们也再难完全控制互联网的走向。二十一世纪后,互联网不仅是商业化,也开始了高度的政治化。
这些都是互联网发展的规律,商业化、政治化固然和最初的理想有冲突,但这无需回避,更无需妖魔化,技术专家主张和实施的互联网治理“去国家化”的美好图景难以实现。当互联网治理走入公共政策领域,正视并努力探索治理之路才最为重要。
当前关于互联网治理模式的讨论和想象有很多,其中多边模式和多利益攸关方模式比较突出。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强调以国家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强调治理主体的多样性,利益攸关方是指在某一特定组织中有直接或间接利益或利害关系的个人、团体或组织,这些可能是企业、公民社会、政府、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这些相关方将被平等对待,特别是政府并没有优先权可以主导问题的解决和政策的制定。
两种模式有所区别,但二者的关系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反而可以寻求一种立体发展。正如崔保国教授所说的:“互联网的治理,不可能都是国家治理,但也不可能不要国家治理。”国家在互联网治理的政策等基础设施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但在技术层次,则更多的需要交由技术社群来管理,分配的权重要依具体国情而定。
承认多元主体的存在合理性,并鼓励多元主体进行对话和协商,互联网治理不会走向分裂,而是能够达成最终的意见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