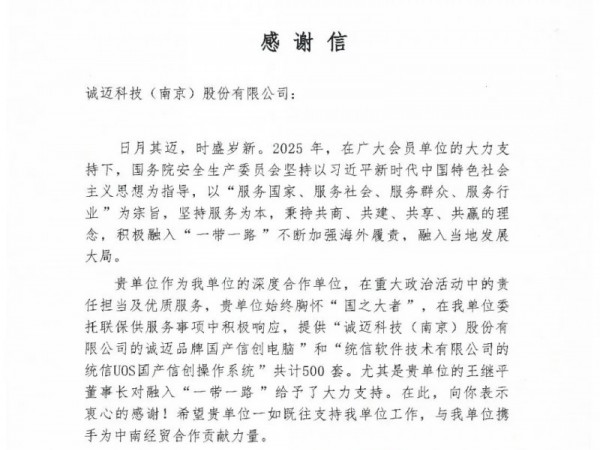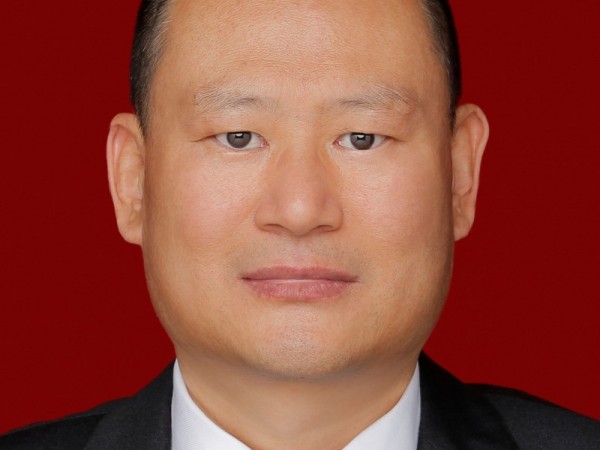接着须讨论,房地产税的可行性怎么样?
我认为可以通过回应最主要的五点诘难来说明:
第一,很多人讲国外这个税,可是在土地私有的情况下征收的,而中国所有的城镇土地都是国有的,还在上面再加一道税,这不是法理上面的硬障碍吗?包括一些很高端的人士也都说过这个意思,网上更是广泛流行此种诘难。
但我们作实证考察,国外可不是如所谓一律土地私有的情况,比如英国是工业革命发源地、典型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它不是所有的地皮都私有,既有私有土地,也有公有土地。公有土地里面还有不同层级政府所有、公共团体所有的区别。建筑物(包括住房)和下边土地的关系方面,大的区分是两类,第一类叫作Freehold,即我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没有任何条件可讲,下面的地皮就是我的,这就是终级产权上地与房是一体化的。另外一种是叫作Leasehold,我持有这个房产,但地皮是要签一个契约的,使它成为一个合法的占有权、使用权的形式。这个leasehold可以把最终所有权跟使用权极度地拉开,最长它是999年,但在法律框架上产权是清晰的,是毫无疑问的,即最终所有权在哪里非常清晰。总之,在英国,土地跟建筑物、跟住房的关系就是这两种类型,但是被称作Council tax的房地产税是全覆盖的,并不区分哪种可以征,哪种不能征。再比如香港(当然也是源于原来英国治下的既成事实),那里没有私有土地,土地全都是公有的,但是香港征了多少年的差饷,从来没断过,所称的差饷就是住房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至于香港的物业税,是营业性的房产要交的另外一种税)。香港差饷来由也很有意思:你要住在这里,就得有警察来保证安全,而治安警察当差要开饷那么钱从哪儿来呢?大家住在这里,那就参与进来分摊负担吧。所以,从国际的、海外的实践来说,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人们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说法,即:只有土地产权私有了,房地产税的合法性才能够成立。
再者从理论分析来讲,也可以印证:中国改革在80年代前期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国营企业要“利改税”,要与其他企业一样交所得税,走了两步达成了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建设过程中就有这么一个学理启示:不要以为国有企业产权终极所有者是国家,那么国家对它征所得税,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这不对,这些主体是有相对独立物质利益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必须加入市场竞争,而竞争又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公平竞争环境,所以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来调节终极产权在政府手里、但是有自己相对独立物质利益的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利益关系,合理的设计是把它们放在企业所得税一个平台上(所有的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现在是一个平台)。当然后面跟着的还有一个产权收益上交制度,这就合乎了现代企业制度各个角度的审视。
这一分析认识实际上可以比照地引伸为:现在最终国有土地上的这些住房的持有者是具有相对独立物质利益的、各自分散的主体,在最终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的情况下,通过立法可以用征税方式调节他们的物质利益关系,无非也就是这个逻辑和道理。中国大陆上与国有土地连为一体的居民住宅,在其土地使用权(通常为70年)到期时怎么办?我国《物权法》已对这一“用益物权”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自动续期”的立法原则规定,有关部门应相应制定细则,以回应公众关切和诉求,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
第二,土地批租形成的地价负担已经包涵在房价里面,现在再来开征一个税收,这不是重复征收吗?很多人听了也是愤愤不平。但是,实话实说,不要说地价是租,而这是税,就是税本身,作为现代的复合税制表现为多种税、多环节、多次征,也必然产生重复的问题,真问题是各种不同的税负重复得合理与否的问题,不可能只有一个税,其他统统去掉。而“租”和“税”,更不是两者必取其一的关系,所有的经济体都是在处理它们之间的合理协调关系问题,所以如果理性地说,这个问题也不可能构成硬障碍。
第三,如果按照开征房地产税来做的话,新的地皮和以后其上新生成的住房的供给,价格水平会与原来的有一定差异:原来没这个税收因素的时候,动不动出“地王”,以后不敢说有了这个税就不出“地王”,但最大可能是不像原来那个市场氛围和密集频率,因为各个方面预期都变了,市场更沉稳了,这就是它调节的作用。那么这个价位落差怎么处理呢?必要的情况下,“老地老办法,新地新办法”,中国早就有这些渐进改革中的办法与经验,社会保障方面老人、中人、新人不就是区别对待吗?最后老人、中人因自然规律退出历史舞台了,又回到一个轨道上了,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形成硬障碍。
第四,有人强调这个税在操作方面过不去。比如一位较活跃的教授,在一个论坛上强调的就是:税基评估太复杂,中国要搞这个税而解决税基评估的问题,那是150年以后的事了!但实际上我国10多年前有关部门就安排有物业税模拟“空转”的试点,也就是要解决税基评估的问题,开始6个城市,后来扩为10个城市。我去调查过,是把所有的不动产基本数据拿到,录入计算机系统,计算机里面早已经设计有软件,分三类(工业的不动产、商业的不动产和住宅),然后自动生成评估结果。专业人士要做的事就是这个软件怎么合理化的问题。在这里面模拟“空转”不就是要解决税率评估和对接操作的事嘛?中国早就在这方面考虑到铺垫和技术支撑,没有任何过不去的硬障碍。实操时还会借鉴国际经验来处理好评估结果与纳税人见面取得认可,以及如有纠纷如何仲裁解决等问题。
操作视角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事情太得罪人,你征这种税,逼着人家来跟你拼命,这动不动会形成大面积的抗税,政府怎么收场?”我们观察重庆,这就可以说到试点的作用——本土的试点其意义的体现。上海、重庆敢为天下先而进入试点,破冰试水,在柔性切入以后,便可看看动静。重庆方案更激进一点儿,敢动存量,涉及的是最高端的独立别墅。辖区内这几千套住宅要交税了,但给出了一个“第一单位”的扣除,把180平米扣掉以后,才考虑该征多少税。如果恰好是一个小户型的独立别墅,正好180平米,照样不用交税。重庆做了以后,没有听说产生什么暴力冲突或者对抗性矛盾,没有出现抗税事件,只是少数人迟迟不露面,找不着人在哪儿,其他的交税人一般都是没有多少摩擦就交上来了。可想而知,这些成功人士犯不着为一年交一万多、两万多元的税跟政府去拼命。这些都是本土的试水实验给我们的启发。
这方面我虽不认为在操作上就是过不去的事,当然也应强调审慎对待。为什么这两个地方要柔性切入?就是这个事不好碰,但是两地毕竟有战略思维,“敢为天下先”,在本土先行先试。本土的试水经验进入立法过程,它的意义不言而喻,非常宝贵,第一单位的扣除正是从这里也可得来的一个本土案例经验。我一开始就直觉地认识到中国不能照搬美国普遍征收的办法,上海重庆的做法使我更感受到在中国似乎就应是按照这个技术路线,首先建立框架,再相对从容地动态优化。重庆这个180平米的边界也在调整,最新调整是收紧了一点,无非就是让社会慢慢适应这个过程,但是一定要做第一单位的扣除。操作方面可能还会有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挑战,但无论怎样,总体来说,我认为决没有过不去的硬障碍。配套杠杆如处理得较好,这个税改决不应激生动荡、形成所谓“压垮稳定局面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五,如开征这个税,小产权房的问题如何解决?小产权房确实是一个中国特色,有这么多的小产权房,征税时怎么办?我们调研后形成的想法就是:小产权房问题不能久拖不决,必须解决。在深圳调研后已写了调研报告,深圳的实践使我们在这方面已经看出一个前景,就是分类处理,一次把通盘方案摆平,双层谈判(政府不在一线上去谈判,先跟那个小区形成一个框架,小区再向住户做工作,就好像现在拆迁,很多时候都是靠小区层面再做工作),谈妥了以后具体兑现可以分期来。小产权房分类处理是早晚要做的事,早做比晚做更主动、更积极。如果这个房地产税改革能够推动,那我认为正是借势应该倒逼着把小产权房的问题解决,这是好事,必做之事,不是坏事,也不成其为所谓硬障碍的理由。
总体来说,房地产税制改革的推进要领至少应可提到这么几条:
一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应该积极考虑加快立法。“税收法定”是一定要做的,但一直到现在,没有看到立法加快,2017年两会信息是:“纳入人大的一类立法,今年不考虑,交下一届人大考虑”,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下一届人大,下一届人大五年之内我们希望能够解决。进入一审后多长时间能走完立法全程,确实还不好预计,但关键是先应启动,不宜再作拖延。一俟成立法以后,可以根据情况分区域、分步推进。假定说2018年就可以推——这完全是假定,那显然不能全国700多个城镇一起动,一线城市,还有一些热得难受的城市,是不是可以作为第一批,先依法实施这个地方税,其他城市区域以后可以从容地分批走,“去库存”压力大的三四线城市慢慢考虑,不必着急。
二是适应国情与发展阶段,在法定规则中一定要坚持作住房“第一单位”的扣除,否则社会无法接受。“第一单位”社科院曾有方案提出人均40平米。人均多少平米,我们依靠不动产登记制度可以把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但可能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事。网上有个反馈意见,它是以假设情景的方式表达的反对:按照社科院方案,人均40平米,有一个家庭父母带一个孩子三口人住120平米,不用交税。但是,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孩子车祸中身亡,在父母悲痛欲绝之际,“当、当、当”有人敲门,政府官员赶到说“你家情况变化,要交房地产税了”。这是以此假设情景表达了对社科院这个方案的不认同,那么给我的启发就是:社会生活中真的发生这种事,政府一定会很尴尬,依法执行吗?那么你就得上门去收,但去依法收税的时候,虽从法条来说严丝合缝,但从情理来说呢?老百姓不认同,执行者自己也会非常难受。
那么这个事怎么办呢?没有万全之策,那么通过立法程序大家可以讨论:还有什么可选的方案?放宽一点,可选的方案就是干脆不计较人均多少平米,按家庭第一套住房来收缴,第一套多大面积都没有关系,反正这就是一个更宽松的框架。但是这个方案也会有问题,如果按第一套房扣,正如有人说的那样“一定会催生中国的离婚潮”,我觉得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前面凡是在政策上有弹性空间的时候,公众为了赶上政策“末班车”,屡次出现排队离婚的“离婚潮”。如果按照现在提出的思路来解决问题的话,可能就还得放松,放到单亲家庭扣第一套房、双亲家庭扣两套房,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当然,另外一种意见就是:“那是不是差异就太大了?”但我们总得寻找“最大公约数”,潘石屹过去的建议就是从第三套房开始征收,许多人听起来都觉得合情合理。无非是先建框架,寻求“最大公约数”。所以从“第一单位”扣除说的例子值得再强调一下,我们的立法应是一种全民参与,让大家理性地表达诉求和建议,没有绝对的谁正确,谁错误,无非就是找到我们一开始框架里走得通、按照“最大公约数”社会上能接受的税制改革方案。
第三,相关的其他税费改革应一并考虑,处理好协调配套关系,这显然是一个大系统。“房地产税”、“不动产税”这个概念广义地说包括和房地产、不动产相关的所有税收,再更广义的说,跟不动产相关的其他收费负担、地租等等,也应该一并考虑,优化为一个系统工程。到了具体落实中央所说的“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我认为主要聚焦的是狭义的保有环节的不动产税,这个概念的不同口径在不同的语境里面要说清楚。但是从宏观指导来说,相关的税费,所有相关负担的改革,一定要放在一起考虑,开发、交易环节的负担总的说应尽量减轻(炒房除外)。这方面的信息与技术支撑条件都有,最重要的是现在中央所说的2018年不动产登记制度要到位,实际上在2017年所有城镇区域工作应该做完。当然,能否如期做完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件事情早一点晚一点,肯定是要做完的。
第四,应对立法推进的困难有所准备。立法过程的速度是不可能强求的,应该是决策层下决心,启动一审,再争取走完立法的全过程。立法中应该充分讲道理,摆依据,积极运用系列听证会等方式尽可能阳光化地促成各个方面的共识。与其在没有立法安排的情况下并没有多少效果地在舆论场这样争来争去,不如按照中央的精神加快立法。
到了立法过程中间,各方发声便都需要慎重考虑,尽量理性地表达各自的诉求。整个社会应耐心地走一审二审三审、很可能要走到四审,一定会有社会上创造天文数字新纪录的各种意见建议,要收集、然后梳理出到底实质性有多少多少条,如何吸收其合理成分。
这是一个全民训练“走向共和”的过程,在公共资源、公共社会管理方面,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必须要经历的客观的社会培训过程,也成为使我们的现代文明得到提升的过程。我国房地产税立法过程哪怕需要10年,它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一瞬,但是这个“税收法定”的制度建设既然是肯定要做的,应该争取积极地尽快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