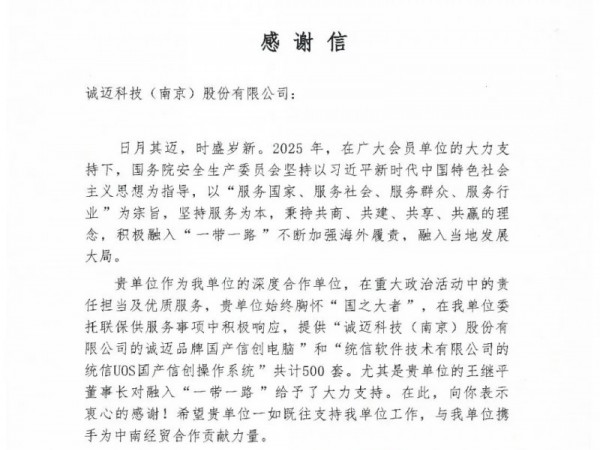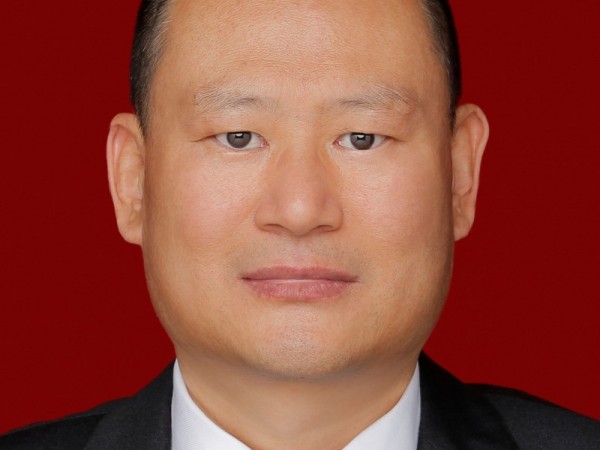这段时间,四大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的消息刷屏。北上广深,作为中国上班族追逐个人梦想的黄金之地,难道正在褪色?
确有其事。
以一线城市中的两大“巨无霸”北京、上海为例,按照已公布的数据,两地常住人口数量较上一年同期分别减少了4.3万和13.54万。
据数据显示,北京和上海两地常住人口数量较上一年同期分别减少了4.3万和13.54万/国民经略
时间回溯到2000年,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约为1300万和1600万。2022年,两地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2184万和2475万。20多年间,两座城市增长了八九百万人,这个增加量和欧洲最发达国家之一的瑞士的人口规模(870万人口)相当。
在人类的城市化历史上,很难找到像中国这样的波澜壮阔的故事。
那么,现在的逻辑改变了吗?的确,有一些变化。
最大“技术”变量
和一线城市“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另一类城市人口依然保持着相对强劲的正增长。
我们看数据:
2022年,长沙全市常住总人口1042.06万人,和上一年相比,人口增量达到18.13万人。
另一个是杭州。2022年,杭州常住人口1237.6万,同比增加17.2万人。
还有合肥。2022年,合肥常住人口为963.4万人,同比增加16.9万人。
2022年,杭州常住人口同比增长17.2万人/视觉中国
按照不完全统计,人口增加超过10万的城市还有西安和南昌,增量分别达到12万和10万的水平。
有趣的是,以上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当地省会。省会,为何偏偏能保持“逆势增长”?
实际上,省会的增长已经持续了至少10年以上,虽然迅猛程度比不上一线城市,但持续性较强,而且具有抗周期波动的特征。以长沙为例,2010年末,其常住总人口只有704.07万,10年之后便超越了1000万大关。
说的形象一些,这等于用10多年时间,将一个地级市的人口全部都搬到了省会长沙,虹吸效应不可谓不大。
2023年5月11日,长沙,五一广场人山人海/视觉中国
另一个让人不得不说的省会是成都。2022年末,成都市常住人口为2126.8万人,同比增加7.6万人,增幅的数字不算惊艳。可是,我们要知道成都已经成为了全国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的“第四城”。其他三个都是直辖市,行政级别远远高于成都,分别是北京、上海和重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省会是最近10多年,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大的受益者群体。随着众多千万省会的崛起,可以乐观地估计,未来中国可能将有2亿左右的城市人口都生活在省会。
省会为何这么“猛”?
有很多分析角度。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新阶段,省级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在一定范围内有所增大,必然强化省会对全省要素的吸附能力。这个问题不多谈。
另外一个因素更直接,也时常被忽略,高铁的线路扩张,成为了省会崛起最大的“技术因素”。
高铁线路的扩张,也是省会崛起的因素之一/视觉中国
一个数据十分有意思。
截至2022年,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第一的是经济发展的“老大哥”广东省,安徽、山东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此外,湖南、江苏、辽宁、江西、河南、湖北等6省份的高铁营业里程名列其后,均超过了2000公里。
高铁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省域的空间经济模式和人口流动模式,在中西部的经济大省,围绕省会的1.5或者2小时通勤经济圈开始成型。
高铁的便利也形成了新的通勤经济圈/《日光之下》剧照
显而易见,如果地市级的富人群体可以1小时到省城,他们大概率会把最核心的资产配置放在省城,而不是放在行政能级和资源吸附能力都愈发不突出的地级市。当然,资产配置向省会的大倾斜,主要发生在楼市的调控之前。
在高铁里程中,湖南排名第四,为2291公里,比东部著名的经济大省江苏还多一点。这无疑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长沙对湖南各大地级市的人口吸附,是一种轨道交通技术大跃迁之后的必然。
城市的圈层问题
省会的热度,自然不必说,另一个群体——计划单列市,同样是中国城市人口大迁移中的幸运儿。
计划单列市这个称呼,对00后和90后来说,有点陌生。但它们的设立,却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忽略的事件。计划单列最主要的好处是,这些城市在经济管理和财政领域有一定的省级政府权限,比省会有更大的自主权。
目前,全国仅有5个计划单列市,分别为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和深圳。位于东北的北方明珠大连和一线城市深圳,我们暂不讨论,剩下的三个单列市一直都有着明显的人口增加趋势。
厦门等城市的人口增长可圈可点/《炽道》剧照
2022年,宁波人口增加7.4万,厦门是2.8万。北方的青岛表现也不错,2022年青岛人口增长了8.54万。考虑到近几年的外部形势和人口流动趋势变化,三座城市的人口增长可谓可圈可点。
省会更多是行政能级上的优势(当然,很多省会也是本省第一产业大市),而单列市则无不是产业重镇。
比如,比杭州低调得多的宁波,就非常厉害。宁波港是全球十大港口之一,该市的石化、汽车及零部件、纺织等产业非常发达,在全球范围内也占有一席之地。2023年第一季度,宁波的GDP排名超过了直辖市天津,其以3801.8亿元超越天津3715.38亿元,排名升至全国第11位。
因此,一线城市人口的“负增长”背后,其实很可能是省会和计划单列市的大规模崛起,对一线城市的人口吸附能力形成了一定的替代。此外,再加上一些超级地级市的崛起,也强化了这种替代效应。
2020年4月7日,浙江宁波,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内一片繁忙景象/视觉中国
比如,在2010年之后,“最强地级市”苏州在十年时间,人口就增加了228万,增量和增速都是江苏第一,成为了人口超过1200万的产业大市加人口大市。产业和人口齐头并进的故事,也发生在无锡、东莞和佛山等超级地级市,它们无不是长三角城市群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极为核心的能量点。
如果我们放大视野,可以这样的下一个判断:未来,中国的产业人口(产业工人、普通白领、作为管理者的金领和拥有股权的企业主)将主要分布在三个层次的城市之中。
首先,金字塔顶的是一线城市,这里是核心大企业总部和资金中心、研发中心。这些地方是中国白领、金领以及企业主的主要集中地。拉长时间跨度,未来的四大一线城市可能拥有1亿的人口。
一线城市是白领等的主要集中地/《请叫我总监》剧照
其次是省会和单列市,它们位于腰部,但数量巨大,也拥有一些中型企业总部或者大公司的二级分公司总部,同时也是区域性的融资中心,拥有规模可观的白领群体(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当地公务员和地方国企员工)。由于这样的城市数量巨大,那么,它们可能吸附2亿左右的人口。
第三类城市则是产业强县,这里主要集中了产业工人和企业主人口,白领和金领很少,无法发展出像样的服务业。
形成这三个层次的产业城市,便可能会产生出一种圈层迁徙效应。首先,是产业的迁徙,这不用多谈。
另外一个即是产业人口的临时性迁徙,比如次级圈层的生活质量较高,房价较低,那么人口就可能阶段性迁徙到次级圈层。在机会合适的时候,产业人口还会返回上级圈层。实际上,深圳白领在文教医疗资源较好的长沙、武汉置业,或者临近的东莞买房的事情,早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深圳到长沙,最快不到4小时高铁。
产业人口的临时性迁徙也并不罕见/《突如其来的假期》剧照
城市的人口变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现象。我们对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不用过度解读,要看到趋势背后的真实原因。同时,也应该继续想方设法,通过发展和创新,让一线城市继续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和对优质人才的吸引力。
毕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一线城市依然是中国创新的核心地带。任何地方,暂时都无法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