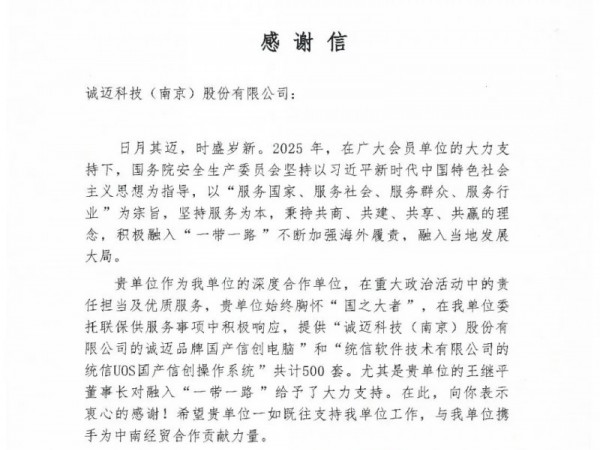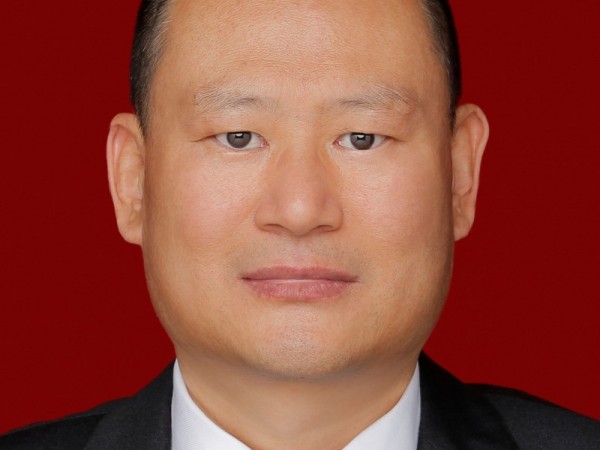5.16 陈永贵与谢振华
陈永贵和谢振华原来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互相都很尊敬,没有矛盾。谢振华主持山西工作后,由于地方工作经验不足,在处理两派问题上不公道,陈永贵有些看法但能忍让,真正对谢振华产生不满是从“七•二三”布告发布一年后开始的。
在“七•二三”布告发布一年之后,谢振华于1970年9月批准枪毙了支持刘格平的造反派总指挥部司令杨成效,紧接着,全省各地借办学习班的名义,红联站对红总站的群众实行了报复手段,武斗时流血最多的晋东南地区枪毙了红总站的一些头头,还有相当一批红总站派的人死于复仇性的“修理”或“退火”之中。当时的“修理”和“退火”手段,集五千年文明史酷刑之大成,在生殖器上用刑方面还有新发明新创造。
陈永贵对这些情况非常不满,说:“我以为武斗停止就不会再发生流血事件了,没想到一些人死于放下武器之后。”
最使陈永贵恼火的是杀和顺县委书记路成和。
1971年1月份,陈永贵到白羊峪检查生产,看见了和顺县枪毙路成和的布告。陈永贵一见贴在这里的布告,就气愤地说:“杀县委书记,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布告只贴在白羊峪,不往昔阳县城贴,这明摆着是不让我知道吗?”他又说:“路成和的错误是搞派性,并没有直接武斗杀人,根本不该杀。这真是欺人太甚!我现在不能只为团结,不顾山西人民的死活。”
第二天,陈永贵和他的秘书李福栋坐一辆吉普车直接到山西省委去找谢振华。谢振华外出不在,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曹中南接待了陈永贵。
陈永贵见了曹中南开口就说:“你们枪毙路成和为什么不开核心小组会议讨论?为什么杀了也不告诉我一声?”
曹中南瞠目结舌,半天答不上来,停了一阵才说:“我们怕你工作忙,开会没有通知你。”
陈永贵说:“怕影响我的工作?那为什么在电话上不说一声?”
这一句话问得曹中南哑口无言。
陈永贵越想越气,当着曹中南拍了桌子,说:“刘、张搞派性,你们现在也在搞派性,路成和是什么问题?该杀不该杀?”
曹中南见陈永贵又把山西的问题捅出来,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
“七•二三”布告后,中央把杀人权下放到省。就在陈永贵找曹中南的头两天,中央又把杀人权收了回去。曹中南以为是陈永贵先向中央告了状,然后才来到太原的。于是就有点心虚,便以检查的口吻说:“老陈,我们这些人总是高高在上,不能及时了解下面的情况。你在下面接触实际多,经常能听到群众的呼声。今后杀人问题一定要慎重。”
其实这完全是误会,也是巧合。陈永贵事先并没有向中央反映山西的杀人情况。现在他看到曹中南作了自我批评,火气消下去不少。回到宾馆,陈永贵问秘书李福栋说:“你看我今天谈话态度是不是有点不冷静?”
李福栋说:“给他们提个意见有什么不可以?不过今天从曹中南的谈话里看,可能还有个背景。曹中南虽出身于大学生,文质彬彬,一向说话喜怒不形于色,但是今天这个自我批评如没有来头,他恐怕不会这样讲。你还是在太原多呆一天,摸摸情况,看看中央文件。”
这一句话,提醒了陈永贵,他第二天便提出要看中央最近的文件和电报。在看文件时,陈永贵果然看到了中央把杀人权收回的电报,他欣喜若狂地说:“呀!这真是洪福愣运。这次来撞对了。这一下好了,由不得他们胡来了。”
陈永贵虽然在这个问题上跟谢振华有了意见,但从大局上跟谢还保持着友好。
从“七•二三”布告到陈永贵进入政治局,这长达四年之久的时间内,陈永贵始终坚持顾全大局,与谢振华合作共事。他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大寨、昔阳,山西工作让谢振华放手去干,只要不直接逼到他头上,陈永贵是不与谢振华直接抗争的。尽管这样,这四年中还是发生过几次比较大的争论。
“九•一三”事件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批林整风运动。1972年初,中央提出了纠“左”的口号。谢振华在联系山西实际批“左”过程中,把学大寨的经验之一——由小队核算过渡到大队核算也作为“左”的内容来批。
核算单位的过渡是陈永贵掌权之后根据大寨的经验和昔阳的实际搞起来的。陈永贵认为,要搞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变昔阳的山河,靠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形式已经不适应了。于是他提议要在全县实行大队核算,并在县委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
实现大队核算第一年,全县获得了大丰收,农田基本建设也全面展开,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到1970年,全县产量翻了一番,全县的五条大川也基本得到了治理。这些成就的取得,和昔阳全县搞大队核算是分不开的。
陈永贵这个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举动得到了中央的认可。1970年中央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时,到会代表对昔阳取得的成绩无不表示赞扬。
山西各县看到昔阳取得这么大的成绩,非常羡慕,一些县没有深入研究昔阳、大寨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只从形式上看问题,不顾自己的客观条件,单纯地从改变核算单位上作文章,其结果是事与愿违,不少地方在搞了大队核算后,不但不增产,反而减了产。其中寿阳县就是最好的一例。这个县有20万人口,80万亩土地,是山西省有名的产粮县,1958年的粮食产量曾达到一亿二千万斤。可是1971年春天全县来了一个核算单位大过渡,由生产队过渡到生产大队。到秋后又来了个“批林整风”,一反“左”,又下令全部分开。
群众埋怨说:“春天合,秋天分,一年四季胡折腾。”再加上寿阳从县、到社、到大队的干部分成两大派,结果1972年的粮食产量一下降到九千多万斤。
在批极“左”的时候,谢振华把全省搞大队核算看成是学大寨造成的恶果,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大寨,指向了陈永贵,说这是受了林彪路线的影响,是极“左”。这还不算,他还把搞农田基本建设也说成是“一平二调”刮“共产风”。 陈永贵听了虽然沉默不语,但心里很着急。他不断地想,又返回头去看几年来自己是不是“左”了,是不是又刮1958年的“共产风”了。
经过反思,他从昔阳的实践中得出结论:昔阳过渡是对的,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也没错。想到这里,他按捺不住内心的不满,愤慨地说:“他妈的!什么是‘左’?不说你搞派性,人心不齐,一半干,一半不干,减了产把帐反而挂在大寨身上。有朝一日咱们还得说说哩!”话音一落,陈永贵又猛醒过来,怕这话传到谢振华耳朵里影响团结,便马上对左右的人说:“这话只是说说而已,你们可不要当真。可不要往外传啊!”
山西批极“左”之风越来越猛,越刮越烈,昔阳内部也发生了不同的看法,个别干部思想动摇。陈永贵怕这样下去会使昔阳建设大寨县、改变穷山恶水面貌的战略目标付之东流,因此对内部的分歧义愤填膺。他没等省里的三干会结束,就回到了昔阳,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并指出:“过去我们批判张润槐,现在我们要批斗‘李润槐’。”他的话中虽然没有指明,但昔阳的干部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时隔不久,毛主席说:“不是极‘左’,而是极‘右’,右得不能再右了。”于是,全国由批极“左”转向了“批林反右”。 陈永贵赢得了主动权,非常高兴,立即发动全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不仅重新上马,而且由原来的四千人扩大到了六千人。
这一年,我从河北57干校回昔阳休假,陈永贵派人在阳泉车站把我接到昔阳县委办公室,他陪我吃了晚饭,从晚8点到12点,他一直和我谈这段由批极“左”到批极“右”以及他和谢振华的斗争过程。
陈永贵兴致勃勃地说:“省里有人看不起我,县里也有人不听话,说我这个大老粗尽是瞎胡闹。结果怎么样?我提出‘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不是听到上面的什么风声,也不是文件上找到了什么理论根据,而是在昔阳的实践工作中体会到不是‘左’。我又觉得有人打到门上来了,不得不反击,可是偏偏弄对了,你说为什么?”
我说:“这类事古今常有。”我随口吟了李白《梁甫吟》里的两句诗,“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陈永贵听了“哈哈”大笑。
陈永贵提出“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不久,周恩来总理知道了这件事,总理赞扬说:“陈永贵不是一般的劳动模范,而是有路线觉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