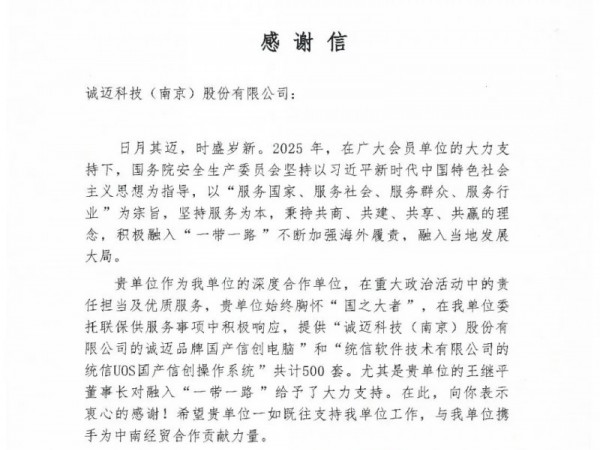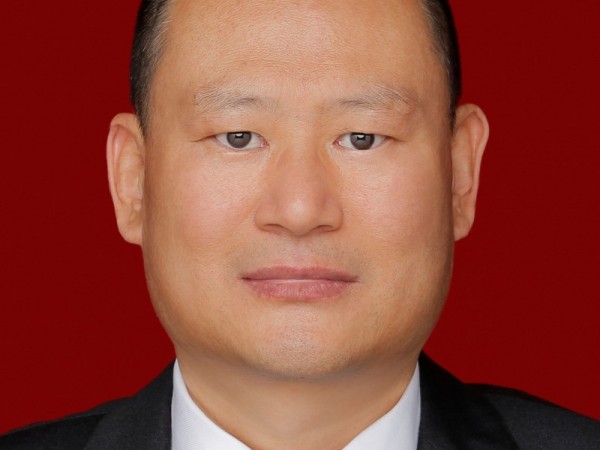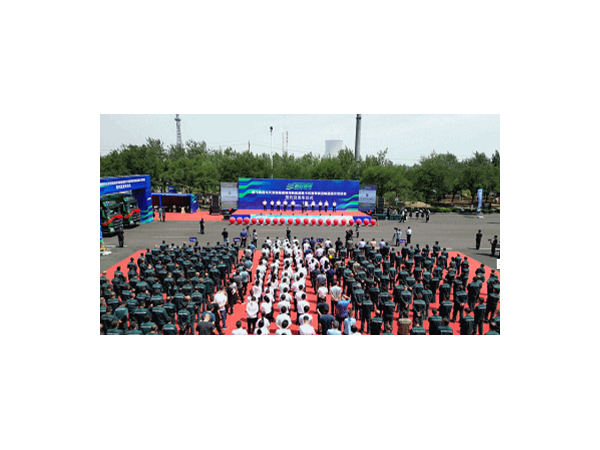《小王子》的作者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想让一个人造船,不要让他寻找木头,而要让他向往大海。”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过:“人是悬挂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弗洛伊德有这样的观点:文明导致了诸多的对于人性本能愿望的压抑,这些被压抑的能量需要寻求表达,而工作则提供了一个升华式的满足途径。
还有一个具体的事情:据法国媒体报道,因上班“过度无聊”,法国一男子把自己雇主企业告上法庭,并获赔5万欧元(约合40万人民币)。该男子称这样的工作使他的生活失去了意义,而法院作出判决的理由是,“工作无聊”损害了他的心理健康,是一种道德骚扰。
从以上观点及事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的存在与行为动机,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似乎都与“意义感”密切相关。
在中国的商业世界,也有人观察并总结,在中国有不少老板,他们在商业上是天才,领导和管理方面却是白痴——他们是优秀的商人,把握商机的能力炉火纯青,但在组织管理方面却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比如,人力资源总监提出辞职的时候,老板感到十分意外并且无法理解:咱企业发展得这么好,我给你们打造了绝佳的平台,你们真是莫名其妙!很多企业的领导和老板是超级业务员出身,很自然地重经营、轻管理。
在他们眼中,把客户搞定,把粮食资源打下来,把钱和银子赚到手,这样的硬实力才是企业的根本。他们把管理、组织、企业文化,尤其是员工工作意义感构建等事情看得太过简单。
出了问题,也是一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单一短期思路,倾向于在薪资方案、股权激励等单一维度上下功夫,不愿意也不习惯在软性的管理方面发现和解决问题。而在组织的软性管理中,“工作意义”是领导者需要关心的核心问题。
追求工作意义的浪潮
2021年,德勤公司携手《福布斯观察》发布了一份题为《人才2020:从员工角度调查人才悖论》的跟踪研究报告——他们对全球主要行业的560名员工进行了深入调查,通过剖析员工对待雇主公司组织和工作的态度,来认识并解决“人才悖论”的困境。
“人才悖论”来自于员工需求的转变: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期待能够在工作中凸显自我,于是越来越多的知识白领型员工由追求薪酬待遇转向追求工作意义,所做工作是否具有意义,成为了最受员工关注的工作特征之一。
报告指出,有31%的受访员工对其当前工作不满意,认为他们无法充分运用自身的技术和能力,计划跳槽的受访员工将职业发展不足(37%)和工作缺乏挑战(27%)视为影响其决策的两大因素。
换言之,离职率居高不下的一大原因是员工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缺乏意义。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要么让员工做有意义的工作,要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
但是,有意义的工作并非唾手可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其著作《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中尖锐地指出:21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司组织中充斥着大量的无意义工作岗位和内容。官僚主义制度凭借工具理性的逻辑,在每一个有管理需求的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高校、企业……
同时,无数缺乏意义的工作被创造出来用于维系官僚组织的运转,身处其中的员工则被“非人化”——如同社会机器的零件,服务于组织效率最大化的目标。而员工自身则难以获得自主性和预期的个人发展,充斥着受制其中的无力和无意义感。
对于“意义感”的忽视也体现在学术研究层面,基于理性人假设和科学主义视角,大量的管理学理论通常将有偿工作视为员工获取薪酬和参与生产的一种方式,缺乏对工作的社会性和象征性的文化维度的关注。而事实上,这些文化维度恰恰是帮助员工从工作中获取意义的最佳途径。
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作对员工群体而言已经不仅仅是获取物质回报的方式,更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越来越多的员工不满足于只作为组织运行的“螺丝钉”存在,开始思考工作之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并主动通过对工作内容的主观认识与实践来追求有意义的工作体验。
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预言的那样,在当下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劳动者(knowledge worker)日益成为企业竞争和发展的关键资源,如何充分发挥其自主性和创新性,激励其产生内在的工作动力,也随之成为了企业领导者的管理重点和难点。
相呼应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春花教授在不久前的中国商界木兰年会上所说:“在未来的组织发展中,企业领导者和管理者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怎么让工作和人变得有意义?”
什么样的工作对员工而言是有意义的?领导者的行为是否能为员工的工作赋予意义?什么样的领导行为能使员工的工作变得有意义?这是管理者们在企业未来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何为有意义的工作
美国管理心理学家施恩(E. H. Schein)提出的心理契约理论认为,个体会基于自身的承诺和感知,对组织中的权利义务产生一定的心理预期。当其心理预期与工作中的现实感知趋于一致时,个体便会拥有较高的工作满意度、工作参与以及组织承诺。
有意义的工作同样如此,当员工对工作特征的心理预期和现实感知一致时,这份工作对于员工来说就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工作能够为员工提供深层次的内在动机,满足其自我实现需求,而无意义的工作则会使员工对工作感到厌恶和抗拒,进而淡漠和疏远所在组织。
因此,对企业家和管理学者而言,明确有意义的工作所具备的特征无疑是一项重要任务。对此,埃斯特尔·莫林(Estelle . Morin)等研究者提出的“工作意义六维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工作的意义感构成。该模型将有意义的工作的特征总结为六个要素:道德合范、自我发展和学习的机会、自主性、认可、良好的人际关系、社会贡献。
道德合范(moral correctness)是有意义的工作的一项重要属性,在重视公平正义以及个人尊严的企业中工作,能够帮助员工产生意义感。这往往通过企业的话语体系来实现。
当企业文化和主流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规范相匹配时,更容易得到员工的接受与认可;而当工作行为与员工自身价值观间存在割裂时,会导致员工的认知失调,陷入要么离开要么违背本心的困境中。比如,日本工业革命与明治维新期间的思想家涩泽荣一就主张“义利合一”“儒士商才”的理念。
他认为传统上人们总是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商人的形象被丑化。他希望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因此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于道德有亏。
对知识劳动者而言,自我发展和学习成长的机会也是不可或缺的工作特质。只有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才能和实现个人愿望与抱负时,员工才会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激励。
而传统管理学理论中更看重的薪酬和福利待遇等因素则属于保健因素和基本条件——优越的薪酬只能消除员工对工作的厌恶,但并不会对员工产生激励,也无法使员工产生工作意义感。
自主性同样是很多员工对自身工作的要求。当员工只能被动接受上级命令,并受到规章制度的严格约束时,工作就成为了一种非自我决定行为,员工会认为自己只是迫于外部压力和标准要求而进行工作。
而外在约束消失后,员工的工作动机也会随之消失,产生“磨洋工”等消极怠工行为,更无法产生积极性投入进而发挥个人潜力。只有掌握了工作自主权,员工才会将工作内化为自己的主观选择,进而积极解决工作问题、承担责任、改善工作结果,从中获取成就和归属感。
“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欣赏与认可也是员工的工作意义需求。只有员工认为得到了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待遇和尊重时——比如薪酬水平、晋升前景、荣誉称号等——才会以高工作参与和高组织承诺作为对领导者和企业的认可的回报,这将成为维系员工与企业关系的紧密纽带,远比劳动合同和雇佣关系等制度性约束更能吸引员工。
工作场所中的人际关系和非正式组织环境也是塑造工作意义的重要环节。当工作氛围宽松融洽时,员工更容易对工作产生归属感,并将其视为自己的能动选择。而当工作氛围过于严苛刻板时,员工则会划清组织和自我的界限,正如那句经典的职场笑话:“同事罢了,真不熟”。人们想要一个友善人本的工作环境,不友好的组织氛围和“酷吏”式领导会令人不安、心生退意。
比如在大型组织机构里善于权谋的组织官僚,他们对下属要求绝对服从,对上面领导唯唯诺诺,做任何事都左右权衡,带着厚重面具,非常有城府和心机,用尽驾驭他人的权术之事。
那么,也无怪乎工作中没有推心置腹的战友和事业伙伴,而且一旦退休卸任,即成路人,无人搭理、倍感凄冷。很多人在工作中不仅仅只是想谋得一碗饭那么简单,还希望能够得到非正式的组织关怀和同事情义。有情有义有担当的领导,自然也会有更高的领导力。
最后,社会贡献也日益成为员工对工作意义的重要诉求。当企业的使命愿景和社会主流话语体系中的某些宏大叙事相关联时,员工更容易产生荣誉感和归属感,认可自身工作的意义。
比如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就遵循“义利合一”和“儒士商才”的企业家精神,他在解释自己构建的“自来水经营哲学”的时候说:“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不是利益,而只是将寄托在我们肩上的大众的希望通过数字表现出来,完成我们对社会的义务。
我们如果能像自来水管那样不停地生产,价格就会降低,产品就会变得便宜,人们会方便,生活会更美好,社会会更富裕,这是松下电器公司所有员工生存的意义,也是公司的社会使命。”
上述特征基于员工的心理承诺和预期而产生,在充分理解这些特征后,我们就相当于掌握了有意义的工作的“设计图纸”,接下来应当关注的,就是作为“工程师”的管理者如何指导这项重要工程的建设。
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领导力既是塑造工作意义的重要动力,又是自身的本职工作,只有当领导者认为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时,他们才能为员工的工作赋予意义。因此,了解在管理者眼中何为“有意义的领导”,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一窥这个问题的答案。
有意义的领导力:构建工作意义
鉴于领导力在这一问题中的双重身份,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什么是有意义的领导进行诠释。
首先,领导者作为工作场景中的个体,也有对自身工作的心理预期和现实感知,当二者保持一致时,领导活动对领导者而言就是有意义的。同时,作为一名管理者,让员工的工作有意义是领导者的重要诉求,因而当领导者能够通过自身能力实现这一目标时,领导行为才是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领导力有何特征
与员工不同,领导者“个人+组织人”的双重身份给予了其深化自我认知的机会。领导者既作为组织的成员承担自身的工作职责,又作为管理者承担对下属的领导职能,往往同时面对着“我是谁”“我在做什么”和“别人如何看待我”等关乎自我身份认同的多重问题。
因此,领导者对意义的感知既来自于自身工作的合意,又来自于员工的正向反馈,领导者通过满足员工的意义需求为自己构建工作意义。
首先,为满足员工对道德合范的要求,领导者应当制定并执行明确的道德规范(moral exemplarity),主动承担起道德责任,管理工作场景中的不道德行为,既践行自己的价值观,又为员工的高道德水平提供保护。
同时,依据社会交换理论,员工也会因此与领导者建立起情感和认知的双重信任,并给予领导者较高的绩效评价,积极通过遵守和维护工作道德来提高团队绩效。
其次,来自领导者的支持能够对员工的身心健康和组织承诺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在充满不确定性和高压的工作环境中。美世咨询的一项职场健康调查表明,在新冠疫情中,从雇主那里得到良好支持的员工将自己疫情期间的工作经历视为负面的比例更低。
同时,在得到良好支持的员工中,53%的人表示自己不会离职,85%的人因此感到在工作中更有活力。为员工提供工作和生活两方面的支持既能满足其对欣赏和认可的需要,又与人本主义的管理价值观相匹配,这与领导者对意义感的需求一致。
再者,为满足员工对工作场所人际关系和非正式组织的需求,构建社区精神(community spirit)也是领导者在意义构建中必须承担的职责。1994年,美国组织行为学权威、圣迭戈大学管理学教授斯蒂芬·罗宾斯(Stephen Robbins)将“团队”概念引入管理学领域,掀起了“团队合作”理念的风潮。此后,团队合作被企业界和管理学界广泛认为是提高工作效率和充分调动员工的资源和才智的重要方式,团队制也因此在现代企业中得到广泛应用。
华为的狼性团队、韩都衣舍的阿米巴小组、海尔的平台创客团队等,都依靠自身独特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团队精神成为了各自企业发展的强劲动力。作为领导者,无论是否处于员工的团队之中,都应当承担团队精神建设的责任,致力于将员工团队打造成有共同目标和信念、有归属感的社区,发挥出“1+1>2”的工作效果。
此外,领导者还应当积极塑造共同的工作承诺,以身作则,发挥模范作用。《论语》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领导者都只是表演性质地喊喊口号、走走形式,又如何能让员工尽心尽力工作?而如果领导者率先履行工作承诺,践行团队目标,严格用团队精神和价值观要求自己,就能让员工感受到真诚与投入而非强迫与形式主义,愿意相信和支持领导者的行动,最终塑造出所有组织成员共同的工作承诺。换句话说,要让员工感受到“被鼓舞”和“被激励”,而不是“被控制驾驭”和“被操纵管理”。
在动荡环境中,企业往往面临着高度不确定的经营前景。比如当前疫情背景下,员工大多对自身的工作稳定性和职业发展前景持有危机感,终日从事“前途未卜”的工作自然无法获得意义感。
这时领导者应当树立和传播积极信念,尽可能包容员工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强调对团队成员的信任和对企业前景的乐观态度,鼓励员工相信彼此和攻坚克难。
餐饮企业喜家德在疫情期间向全体员工进行书面承诺,直言“就是卖房卖车也要保证员工的权益,只要大家愿意不离不弃,公司领导砸锅卖铁也会挺住,大家团结一心一定能战胜疫情!”。
这为员工营造了安全和稳定的心理环境,让员工能够抛下顾虑专心工作,并在“同仇敌忾”的积极氛围中体会到工作的意义。
最后,有意义的领导行为应当能够使领导者对自我保持清晰的认知,并依据员工评价不断对自己的管理理念和做法进行批判性思考。就像陈春花教授所说:“能否成为一名好的领导者,在自我认知上有三样东西绕不开:自我、事实、经验。”领导者要摆正自己与企业员工的关系,认清自我身份,转变对员工需求的认识,以“让员工的工作变得有意义”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
道德规范、对员工的支持、团队精神、共同的工作承诺、对人和事的积极态度、自我意识,上述六个特征共同凸显了“有意义的领导”的一项本质属性:利他性,即领导者着重关注员工成长的内在现实需求,而不是以自身利益为重。
这在此前的积极导向的领导力研究中已经有所体现,比如对真实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和道德型领导的探索:既有文献认为,领导者的自我意识是真实型领导的核心,领导者应当对自己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以及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保持清晰的认知;而构建社区精神则是变革型领导的核心,领导者通过这一方式塑造员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以此作为推动组织变革的基础;道德型领导则与道德规范所描述的特征相似,强调对员工的道德认同和道德关注。
但这种利他主义的观念常常与组织制度体系和价值观之间存在冲突,使领导者在工作中陷入追求意义还是遵从主流的两难困境。揭发美国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丑闻的前安然副总裁莎朗·沃特金斯(Sherron Watkin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她看到的管理者们都只顾追求自己的高薪厚禄,将道德感和员工诉求都抛于脑后,财务造假、恶意竞争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而她无法接受公司的这种“赢者获得一切”的去道德化(de-moralizing)价值观,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这也是她选择以被辞退为代价揭发安然财务造假丑闻的直接原因。
领导者眼中的意义来自何处
至此,我们已经对有意义的领导的特征有所了解。进一步而言,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领导者为什么会认为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显然他们并非仅仅出于自身工作职责才选择为员工塑造工作意义,而是出于“意义动力(dynamics of meaning)”的驱使,即领导者依据对过往工作经历和员工对工作意义的诉求的认知来塑造领导行为的意义的过程。
桑德琳·弗雷默(Sandrine Frémeaux)等学者从事的一项针对领导者的大型访谈研究从四个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
第一个原因来自于领导者曾经的工作经历。现在的领导者在刚进入企业时也曾是工作中的“螺丝钉”,经历过探寻工作意义的过程,他们会依据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制定自己的领导风格和方式。如果领导者认为自己曾经的领导的管理措施没有意义,就会在自己的管理工作中引以为戒;相反,如果领导者认为自己从曾经的某位领导处受益良多,则会向其学习并模仿其管理方式,正所谓“萧规曹随”。
其次,家庭教育也对领导者有重要影响。许多领导者表示,在成长过程中父母的教育帮助他们塑造了最初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并成为其日后在工作和生活中始终坚守和传递的准则,也成为其自我身份构建的重要来源。星巴克的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提到过他创业的心路历程。
他的父亲是美国工厂的一位蓝领工人,善良勤奋、任劳任怨,但是在流水线和螺丝钉一般的工作中,他没有获得应有的个人价值和尊严。目睹了这一切的舒尔茨立志通过自己的创业带来“以人为本”的商业价值。价值观远胜商业模式,在星巴克的人事制度和组织管理中,人的因素被视为重点因素。
再者,领导者常常将有意义的领导力和自身的价值观和信仰志趣联系起来。比如,曹德旺把人生当成一场修行:“人生借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步骤,最后达到般若,完成人生轮回。”任正非的意义感总结是:“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洛克菲勒说:“我财源滚滚,如有天助,因为上帝知道,我会把它们用到该用的地方。”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老天派我来传授仁义道德之学问,你能把我如何?
可见,不论是怎样的宗教背景,具有一定的超越性的信仰、担当精神和利他价值观的领导人,往往会有一种天命的意义感,从中获得一种永不懈怠的创业者工作激情。
最后,过去的成功经验也左右着领导者的管理选择。已经被员工接受和认可的管理方式能够加强领导者的信心,使其认为自己掌握了有意义的领导能力,并能够在未来的员工管理中继续复刻。但也有领导者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过分相信过去的成功经验会降低对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导致难以及时发觉员工心理和需求的变化,使既有的管理方式成为员工的束缚。
领导者和员工的意义互动
稻盛和夫认为,领导者和员工间存在无法割裂的相互影响,正如领导者为员工塑造工作意义和对自身工作意义的追求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理解员工对工作意义诉求的基础上,领导者通过关注每一名员工的特点和愿望,积极发展双向信任和支持关系,利用自身领导力构建并传达员工期望的工作意义。而员工对领导者行为和自身工作的认可,又给予了领导者成就感和满足感,“风来疏竹,雁过留声”,让其感觉自己“让世界有所改变”,这构建了领导者的自我认知。
综上所述,领导者能够通过为员工构建工作意义来履行自身职责,又能够通过员工的高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参与等正向反馈为自己的行为赋予意义,最终实现意义的“双赢”和领导者身份的构建。
总结
目前,很多企业老板和组织管理者是超级业务员出身或者具有出色专家背景,很自然地重经营绩效,轻管理、尤其是意义构建,不愿意也不习惯把文化管理当做一个系统性、长期性和根本性的问题。而公司归根到底是人的组织。在制度和理性之外,要想调动人、激励人、凝聚人,唯有适应组织的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工作意义动机。有效构建意义和建设积极文化是公司管理的更高境界,也是效率和利润的新来源。工业化时代的工具理性和官僚主义制度在知识经济和创新型组织工作蓬勃发展的时代显得有些过时。管理范式的关注点由知识创新转向员工幸福和意义的背景之下,“有意义的领导力”这一概念开始被越来越多地接受与重视。
在当下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和组织发展中,领导人与管理者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怎么让工作和人变得有意义?
有意义的领导力的构建需要管理者充分理解道德合范、自我发展和学习的机会、自主性、认可、良好的人际关系及社会贡献这六项员工最基本的意义诉求,并将自己的意义感与对这些诉求的回应相结合,在与员工的互动中实现意义建构。有意义的领导既能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还能提高其工作满意度、工作参与度和组织承诺,与此同时,收获了工作意义的员工也会给予领导者正向反馈,促进领导者的成长与发展。
最后,领导者在现实场景中很难对员工的意义诉求的动态变化保持敏感,还常常面对着与主流价值理念的冲突以及组织规章制度的约束。这需要领导者秉持利他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价值观,拓宽自身视野,不拘泥于固定的理论和视角,真正理解员工内心对工作的愿望与诉求。
领导力水平的高低,不仅体现在领导者本人的专业技术水平,更在于其胸怀底蕴和视野,在于其对于组织员工精神世界的认识和工作意义构建能力,更加重要的是拼这些软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