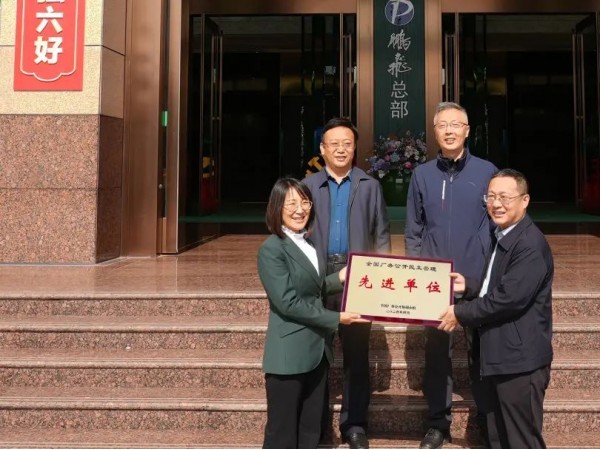澳大利亚黑德兰港——身材瘦长、一头黑发的冲浪玩家李·梅多克罗夫特(Lee Meadowcroft)曾作为模特在伦敦、米兰和新加坡的伸展台上走秀,而后他为了实现梦想回到祖国澳大利亚,做起草药生意。
他的店倒闭了—他说他不该选在那条街开店—他亏掉了几乎全部的积蓄。而时尚界在那时已经找到了更新鲜的面孔。于是,梅多克罗夫特和数万澳大利亚人一样,选择去煤矿工作,曾经一年能挣25万美元。现在他在学做水管工。
那是2004年底。他上了一个为期两周的吊车操作培训班,把手头最后的4000美元交了学费。他发现企业对工人极度渴求,以至于会派专车去接这些未来的焊工、电工和吊车操作员,把他们送到最近的机场,然后飞往矿场所在地,其中就包括这里,偏远的澳大利亚西北部沿海地区。
当时的中国正在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向前发展,希望得到澳大利亚的每一块矿石。像梅多克罗夫特这样的矿工要超负荷工作:连续工作13天,每天12小时,休息一天,然后再连续工作13天,每天12小时。矿业推动了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猛增,最高时达到一年将近1000亿美元——相当于全国男女老少每个人4300美元。
全球资源丰富的地方都借中国致富了,梅多克罗夫特和黑德兰港的其他设备操作员也不例外。
2011年他的年收入达到25万美元。他曾见到矿工们闲暇时在地上画个圈,把蟑螂放进去,赌哪只先爬出来,有时候赌注可达100美元以上。有一个焊工买了一辆法拉利308跑车,很快就厌倦了,于是办了一场1000美元一张票的抽奖把车处理掉。
“大家都很疯狂,”梅多克罗夫特说。
崩溃的到来同样是迅速而猛烈的。中国的经济放缓导致太多的矿场在向太多已经停产的中国炼钢厂供应矿石。新矿建设项目停工了。赫兰德港的经济陷入低谷。梅多克罗夫特丢了工作,而后下一份工作也丢了。他和其他几万人一样,回到了家中。
梅多克罗夫特的经历,是有关中国崛起局限性的又一则盛衰寓言。从俄罗斯到巴西,从尼日利亚到委内瑞拉,随着中国崛起而繁荣的资源大国,也因中国需求放缓而遭到经济打击。
不过在澳大利亚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它没有被全球崩溃打倒。这里的矿场成本比别的地方低,多数矿依然在作业。而澳大利亚的这种出人意料的持续繁荣,还因为有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资金正从中国流向这里。
在清洁的空气、优质的教育系统吸引下,再加上对中国未来的担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把钱花在澳大利亚。数以万计的中国家庭把子女送到昂贵的澳大利亚大学读书,澳大利亚向中国的食品出口也在猛增。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房地产投资自2010年以来增加了至少10倍;在墨尔本和悉尼市中心的新住宅单位有近一半被中国投资者买下。
这让一些人开始反思中国资金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有关联的企业向澳大利亚的政党做出了可观的捐献,一家据称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公司,去年拿到了一个港口的99年期租约,而港口就在一个经常驻扎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基地附近。
但是对梅多克罗夫特这样的人以及西澳大利亚州其他因矿业衰落而失去生计的人来说,中国的钱是一种赐福。现在他住在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在一个瞄准中国买家的新住宅开发项目中做水管工学徒。他一年只能挣2.1万美元,不过出师之后,他的收入可能翻两三倍。
当中国游客进入他工作的建筑工地时,他知道,他们可能是最终的买家。“如果你见到一群中国人,”他说,“那你就是见到了金主。”
繁荣的颜色
在黑德兰港(Port Hedland),钱的颜色是粉红色的。
码头上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鲑鱼色的尘土,从起重机顶部的黄色栏杆到快速转动的传送带的边缘——传送带把岩石快速送入巨型货轮的肚子里。50年前采矿业兴起时,这里的街头也蒙着这样的尘土。
“它把你所有的衣服都变成粉色,”市议会议员朱莉·阿里夫(Julie Arif)说。当年,工人们开始在附近的皮尔巴拉沙漠和山丘上挖矿时,她还是个小女孩。“我们过去称它为皮尔巴拉粉色。”
当时,当地领袖也并不介意。据阿里夫讲,在20世纪70年代初,该市市长曾说,“尘土把收银机堵塞了,我们才会担心。”阿里夫也主管该市的一座小型历史博物馆。
那些粉色尘土来自铁矿石。西澳大利亚州出口海外的铁矿石数量比澳大利亚其他任何一个州都要多。
铁矿石改变了黑德兰港。原住民称这个港口为Marapikurrinya,有过去很多年时间里,它的经济全靠羊毛出口以及从落潮时的牡蛎中采集的少量珍珠。在矿业兴起之前,它出名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末附近的农场工人举行了持续三年的大罢工,那成为澳大利亚原住民争取权益的关键时刻。
这些铁矿距离澳大利亚南部沿海的钢铁工业区路途遥远。不过,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允许大规模铁矿石出口,向日本和欧洲的买家开放这个地区。
尽管外国的资金慢慢来到了黑德兰港,但它依然很简陋。1975年,热带气旋“琼”(Cyclone Joan)将一半黑德兰港夷为平地,州政府用一英尺长的细钢杆在废墟上支起一个预制构件式建筑,替代遭到摧毁的医院。这个医院又使用了近40年才遭废弃,如今海边的这幢建筑还空置着。
娱乐方面有skimpies——也就是年轻女子的脱衣舞表演,她们几乎从不遵守夜晚降临后不得全裸的州法规定,随着夜色渐深,更是不可能遵守。
从黑德兰港往沙漠里驱车数小时,才能到达开采铁矿石的地方。工人们用炸药在露天矿山上炸开巨石,然后用大型推土机把它们铲起来。矿石粉碎后,用比房子还大的机器进行分类,然后用火车或巨型卡车(也就是所谓的公路火车,它能挂三到四个拖车)运到黑德兰港。
前不久,在黑德兰港的犹他点(Utah Point)泊位,一条传送带在印度洋深红色的晚霞中,把铁矿石倒入一艘中国货轮的七个大货舱中。货轮用小型面包车大小的机械吸盘固定。红色碎石流以每秒两吨的速度倾泻而下,发出沉闷的轰隆声。每个货舱都很大,面积相当于一栋宽敞的美国家庭住房,还能留出些空间。
起重机突然转向一边,停止倾泻铁矿石,轰隆着挪到靠近货轮中间位置另一个货舱的上方,继续倾泻。
铁矿石有时也意味着危险。有一次,梅多克罗夫特看见一根绷紧的一英寸粗的钢索突然断裂,把一名男子扫进一堆钢管中。还有一次,他看见一个50磅重的钢索滑轮砸到一个工人身上,削掉了他的部分脸和肩膀,并将他击倒在地。
“滑轮把他从地上弹起来,就像篮球那样,”梅多克罗夫特说,“现场流了很多血。”
不过,那时候这里的生活总的来说很平静,生活成本也不高。该市有8支业余棒球队,很多工人下班后就会去打棒球。房价也能承受。40岁的莎伦·拉米雷斯(Sharon Ramirez)还记得,她的父母在80年代末曾有机会以2万美元买下他们当时租住的平房,但最后决定不买。
“我们没有欣然接受那个价格,”她说,“因为在当时,那还是挺大一笔钱的。”
中国冲击波
黑德兰港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矿业繁荣对他们造成冲击时刻的故事。
对拉米雷斯来说,那个冲击时刻是当她家租住的房子以100万美元卖给一个外地投资者的时候。对戴夫·麦高恩(Dave McGowan)来说,是那8支棒球队中有4支因为工人的轮班从8小时变成12小时而解散时。对丹尼尔·康纳斯(Daniel Connors)来说,是当地汽车修理厂因为缺少工人而告诉他必须提前4个月预订才能给他的汽车换机油时。
当时中国在变化——它也改变了黑德兰港。
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再加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后贸易壁垒的减少,给中国经济点了一把火。连一些不出名的城市都冒出很多的摩天大楼。该国修了7.7万英里的高速公路,几乎全是1997年之后所建,这比美国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还长三分之二——中国的高速公路网就是以美国为样本的。
所有这些建设意味着,中国去年生产和消耗的钢铁几乎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
为了给钢铁厂提供原料,中国需要澳大利亚的铁矿石。铁矿石的价格增长了十倍。必和必拓公司(BHP Billiton)、力拓矿业集团(Rio Tinto)和福蒂斯丘金属集团(Fortescue metals Group)等大公司竞相修建矿场,尽可能快地增加港口泊位。
繁荣的大幕就此开启了。
小小的黑德兰港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每年处理货物的吨位比洛杉矶、香港或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还要大。熟练的焊工和电工一年的工资可达35万美元,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这里的人口已经翻番,达到约30万的顶峰。如果不是土著人宣称享有郊区的土地引发的争端阻碍了施工,导致房屋短缺,这里的人还会多很多。
高额的报酬有许多来自加班,或是由于上了一种被戏称为“离婚排班表”或“自杀排班表”的班次。矿业公司将工人运至偏远的营地,让他们连着工作27天,中间只休息一天,之后再送回。
焊工身着“高能见”服装——能反射光线、能见度比较高的黄色采矿作业服——数月里一直在沿海沙漠高达110华氏度(约合43摄氏度)的高温中汗流浃背进行户外作业,度过一个个漫长的夏天。
所有这些超时工资将物价推至极高的程度。黑德兰港的面包店、肉摊、报摊、特许经营的鱼店和潜水店都关门了,因为无力承担不断飙升的租金,也请不到本地人放弃矿业公司而为之工作。
当地一家小餐馆的老板雷·桑普森(Ray Sampson)以每周1600美元的租金租下一栋小屋,供他从市外聘来的厨师和女服务员住宿。
因为餐馆每天爆满,他又以每周1800的租金租了第二栋小屋,好容纳新增的员工。他们大多是途径这里、短暂停留几周的背包客,也是唯一愿意接受厨师和服务员这类工作的人。
房地产的卖价和租金大涨。澳大利亚别的地方、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富裕家庭听说了这里的四位数周租金,感到有利可图,于是大批涌入,进行投资。
珀斯一家便利店的老板洛林·墨菲(Lorren Murphy)在四年前飞到黑德兰港,花了近200万美元买下一栋两层楼房。他很快便签了一份为期两年的租约,租户愿意每周支付4100美元,也就是说每月近1.8万美元。
他羡慕那些有更多资金进行投资的人,因为这看起来似乎是一桩稳赚不赔的生意。“我有个朋友在这儿投了600万美元,”墨菲回忆道。
城里最终拆掉了原有的医院进行重建,新增了一座游泳馆、一个配备空调的篮球馆、一座新政府大楼、一座溜冰场,还有其他设施。在黑德兰港外,位于珀斯的州政府投资建设了多座医院、新电力线和供水系统,还花10亿美元修建一座澳式橄榄球场。
然而,在4000英里以外,麻烦正在酝酿。中国负债累累的开发商开始放慢盖新楼的速度。钢铁消耗量在2014年减少了3%,2015年又减少了5%,尽管那里正在修建更多钢铁厂,以为会有永无止境的增长。制造商对开设更多工厂表现得更加谨慎。
倒塌
“谁也没见过泡沫爆得这么壮观。”
在黑德兰港以南约200英里处,名为铁谷的铁矿场就座落在红色的沙漠里,这里有因为干旱而没充分长开的桉树,还有褐红色的悬崖。
之前担任矿场总经理的金·谢泼德(Kim Sheppard)沿着一座三层的黄色设备的阶梯往上走。他在上个月转到了别的岗位。这个设备落了一层粉色的矿尘,在压碎铁矿石和将之分拣成小块时发出铿锵之声。
这里的作业高度自动化,每班只需四名工人和一名监工,还有几名技工、爆破专家和经理在旁边一座有空调的楼内呆着。在生产的高峰期,曾经有几百名工人在这里劳作。
矿场周围的沙漠过去点缀着一些大型的工人营地,从而建成了更多矿场。现如今,沙漠上却一片空白。
“总是有兴有衰,”谢泼德说。“但这一次不同。”
黑德兰港很快感受到了这种痛楚。铁矿石价格大跌。因为担心工人发怒,破坏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设备,矿业公司裁掉了数以万计的雇员。
“那天他们说是喊卡车司机进来吃午饭,结果却说,‘拿上你们的背包,’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曾在铁谷附近一座矿场开挖土机的香农·贝克(Shannon Baker)说。“他们把我们集中在员工室,然后说,‘机场有飞机会带你们走。’”
黑德兰港一家大型房地产经纪公司的所有者吉姆·亨内伯里(Jim Henneberry)说,房租和房价已经下降了四分之三。镇上五分之一的房子处于空置状态。
比尔·齐奥姆巴克(Bill Dziombak)以每栋100万美元的造价在这里修建了联排别墅,却眼瞅着房租和房价崩了盘。“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仅仅12个月里,事情就这样突然发生了,”他说。“就好像从悬崖边掉了下去。”
卡米洛·布兰科(Camilo Blanco)经营的汽车修理厂的顾客不再需要预约。“曾有顾客走进来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因为我不得不离开这里,’”兼任黑德兰港代理市长的布兰科说。
矿工们临走前卖掉了太多旧机动船、肌肉车和沙漠越野车,当地市场充斥着这些东西。不久前,有人要把一辆带有诸多选配装置、原价1.4万美元的Rhino沙滩车以半价卖给布兰科,而他还是要讨价还价:“我说,‘我愿意出价五千’,而现在它就停在我家院子里。”
当地领导人在繁荣时期有大把的钱可花,如今却面临着削减房地产税的压力——相关税率的设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以极高的房地产价值为依据。单是运营黑德兰港的新篮球馆,每年就要花掉200万美元,相当于当地年度预算的3%。
“这就像冲浪,”西澳大利亚州州长科林·巴尼特(Colin Barnett)在珀斯接受采访时说。“浪来了,你得把握住机会,奋力乘浪而行,利用好它带给你的一切。浪走了,你就得奋力划水,我们当下就是在奋力划水。”
中国投资2.0
即便采矿业出现了最严重的滑坡,澳大利亚还是发现了经济增长的潜在源泉,这次依然来自中国那里,也就是艾克·王(Ike Wang)这类人。
现年24岁的艾克·王去年毕业于珀斯的莫道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该校有成百上千名像他这样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正寻找市场营销方面的全职工作,尽管西澳大利亚州经济增长放缓,但他有一个优势:他在中国天津的家人于今年年初花37万美元为他买下了一套带有两间卧室的公寓。
这套公寓位于13楼,墙壁刷成了白色,地上铺着白地毯,屋内几乎没有任何家具。但它拥有可以俯瞰这座城市良好视野,施工工艺看上去也很过硬。(巧合的是,这栋公寓楼的部分给排水管道是由梅多克罗夫特安装的。)
在艾克·王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这套公寓让他有了免费的住处。“这是一套新公寓,我很喜欢,”他说。“哪儿都是崭新而又干净的。”
房地产开发商称,他们发现很多中国家庭急于在澳大利亚买房。在珀斯开发了大量公寓楼的保罗·布莱克本(Paul Blackburne)说,“我认为投资回报是次要关注点——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把钱放在某个稳定安全的地方,是把钱转出(中国)"。
与美国的情况类似,低利率也增进了买家对房屋和公寓的需求。澳大利亚政府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15年6月30日的财年里,得到其许可的来自中国的房地产投资为182亿美元,为前一财年的两倍,比上一财年来自美国的投资总额多出两倍还多——美国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海外投资者。一些开发商表示,更多来自中国的资金在没有得到澳大利亚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悄悄流进了房地产市场。
黑德兰港乃至整个西澳大利亚州都面临着预算问题。该州已经着手出售为期50年的犹他点泊位租约,买家有可能来自中国,尽管矿产资源(Mineral Resources)等规模较小的公司纷纷表示反对。该公司拥有成本低廉的铁谷铁矿场,却不能使用其他码头,因为它们都受控于必和必拓等规模庞大的竞争对手。(梅多克罗夫特恰巧也参与修建了犹他点泊位。)
但总体而言,黑德兰港或者西澳大利亚州的失业率基本没有上升。一些人,比如梅多克罗夫特,在珀斯找到了工作。许多人搬到了东边的悉尼和墨尔本,投身于那里的建筑行业。
让一些澳大利亚人感到担心的是:这个国家眼下所处的经济轨道是否和10年前的美国类似?澳大利亚央行在4月份警告称,如果来自中国的需求下降,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可能遭受挫折,该国有着大量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的银行系统可能受到损害。
但截至目前,中国人的资金仍在流入。在铁矿石热潮中拿赚到的钱大肆挥霍的很多矿工,如今正竭力适应建筑业的工作。但也有很多矿工当初存了钱,已经用积蓄买了房或创办了小企业。
“他们是小微创业者,”西澳大学的博士生汤姆·巴勒特(Tom Barratt)说。他在写一篇关于皮尔巴拉(Pilbara)山丘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论文。
梅多克罗夫特就是存了钱的人之一。他买了一栋房子,很快就付清了大部分抵押贷款。另外,在过了许多年往返于居住地和遥远的矿山、港口之间的日子以后,他和相恋已久的女友结了婚,目前一边养育两个孩子,一边学着成为一名水管工。
尽管银行储蓄账户里的钱现在少了许多,但谈起那个繁荣的时代,他说自己无怨无悔。“我结结实实地辛苦劳作了12年,”他说,“去实现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无法达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