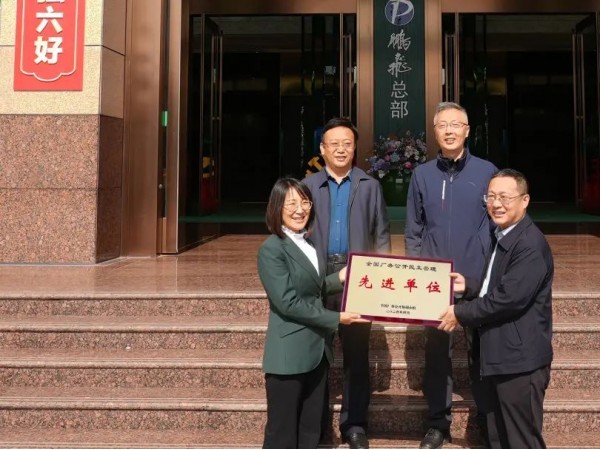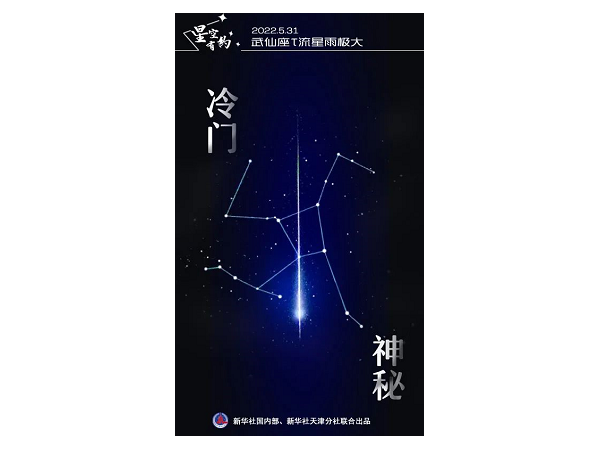2018年2月6日凌晨,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去世,享年101岁。这一天对中外学术界来说都是一个沉痛的日子。许多年来,饶宗颐先生已经成为一个学术符号,一个文化标志,一面代表秉承传统道德为往圣继绝学的旗帜。饶宗颐先生生于内地,生活工作在香港,一生执志于传统国学的研究、教学和弘扬,用最传统的学术在最现代化的香港播下种子,并用一生来加以浇灌和呵护,终于在香港培育出一片传统学术的绿色天地。饶宗颐先生是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学术交流使者,为香港的学术发展和繁荣作出无可替代的贡献。饶宗颐先生爱国爱港,对祖国有着深沉的眷恋,对祖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大地上出土的各种文物文献,有着痴迷的喜爱和执着的追求。饶宗颐先生具有强大的向心力,使得无数晚辈学者围绕着他,得到他的指点和熏陶,并用其来滋养自己所从事的学术事业。
学界晚辈习惯称饶宗颐先生为“饶公”。我自从20世纪80年代走上古文字研究的道路,就一直把饶公奉为大师,但无缘相见,只能通过读其书,从而想见其为人。直到90年代初,才终于有了亲聆謦咳的机会。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为庆祝建校30周年,举办了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我作为受邀代表,陪同先师姚孝遂先生一同赴港与会,并在期间拜见了饶公。饶公因对吉林大学古文字学科的奠基人于省吾先生格外尊崇而爱屋及乌,对吉大来的人都格外热情。我当时刚三十岁出头,比较青涩,饶公看着我,开玩笑地说:“你来自壮阔的东北,却有着江南男子的秀气哈。”说得我很不好意思。在那次会上,我的文章和发言引起了饶公的兴趣,他私下跟沈建华女士提到我,流露出某种期许。其时正好饶公想对他早年的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一书做修订,就想到了我,让沈建华女士联系我赴港协助他做修订工作。为此饶公专门联系利荣森先生的北山堂,筹集到一笔专项基金,委托香港中国文化促进中心负责安排我在港的工作和生活。对我说来,这自然是一个靠近大师、亲炙教诲的好机会,于是爽快地答应,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1995年年中到达香港,开启了在港八个月的工作和生活历程。
我到香港刚安顿好,饶公就让沈建华女士引导我到他位于跑马地山村道凤辉阁的家里,与我促膝倾谈,然后又请我吃饭。饭间谈学问、聊轶事,饶公言辞和柔,态度温煦,对我黾勉有加,让我如沐春风。
在港期间,常常与饶公见面晤谈。有时是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他的办公室内,如果赶上沈建华女士和郑会欣兄也在场,话题就会更多;有时是在新亚书院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室里。因为当时我在新亚书院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室工作,因此偶尔饶公也会乘坐校车到山顶新亚书院内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室来看我,顺便查看工作进展情况。那时的饶公已经年近八十,从跑马地的家里乘坐地铁再接驳校车上山到学校,非常辛苦,但我每次在学校看到他,他都是西服革履,皮鞋锃亮,腰板挺直,仪态壮严。见到我也总是不停地嘘寒问暖,同时充满兴趣地了解和听取各种学界信息。饶公每次到校,只要赶上饭点,都会让沈建华女士给我打电话约我下山一起吃饭。那些年内地到港访学访问的学者很多,为了请客方便,饶公的稿费和评审费就存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下边范克廉教师餐厅的账上,吃过饭,由沈建华女士或郑会欣兄代为签单即可。有一段时间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的王素兄也来港访问,还与我面对面在一个研究室待过,记得我俩常被一起约到山下陪饶公吃饭。有时临时被约,因时间匆忙,王素兄来不及换鞋,穿个拖鞋就去赴饭局,还被注重仪表的沈建华女士笑话。
我到港不久,饶公提议香港中国文化促进中心安排我做一次讲座。讲座那天,还是由沈建华女士陪我到位于中环码头双子星座大厦上的中心会场。待我们到时,饶公已经到了,仍旧是西服革履,头发一丝不苟。饶公充满激情地主持了我的讲座,谈笑风生,幽默风趣。我那次讲座的内容是有关甲骨文的。当时还没有后来才出现的投影仪,只有胶片投影。记得饶公对我写的甲骨文字形胶片很感兴趣,还专门让我复制一份带给他。当天讲座比较成功,听众爆满,中心助理主任跟沈建华女士说,打破了中心有史以来的纪录。观众对我讲的甲骨文字形的蕴意极感兴趣,时间已到,还希望再讲,无奈因会场接下来另有安排,只好作罢。讲座完跟听众的交流也很热烈,饶公始终参与其中,并不时插话,还做了精彩的总结。
在港期间,我和饶公还有过一次学术合作,就是撰写了一篇《甲骨断想》的文章。先是我跟饶公就甲骨文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讨论,然后由我草拟成文,饶公审定。该文后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二卷。
因在港期间协助饶公校订《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我还借机集中拜读了饶公其他有关甲骨学的论著,对饶公在甲骨学上的贡献和理念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于是撰写了一篇名为《谈饶宗颐教授在甲骨学研究上的贡献》的文章。该文发表在《华学》第二辑,刊出后在学术界产生了不错的影响,并被广泛征引。通过分析阐释饶公在甲骨学研究上的贡献,我在文中指出,因饶公号“选堂”,又因饶公在甲骨学研究上取得的成就足以与甲骨学研究的四位大师,即“甲骨四堂”的罗雪堂(罗振玉)、王观堂(王国维)、董彦堂(董作宾)、郭鼎堂(郭沫若)相提并论,因此完全可以将饶公列为甲骨学研究史上的第五堂:饶选堂。这一学术指称和甲骨学史上地位判定的提议,得到了学界很多人的认可。
1996年3月,我完成了在港工作,临行前去拜会饶公并告别,又蒙饶公请饭,席间相谈甚欢,依依不舍。
2002年我再次赴港半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同沈建华女士合作,为汉达文库的金文资料作释文校订。其间又得以多次拜见饶公,蒙其教诲和指点。有些教诲和指点对我来说,颇有箴膏肓、起废疾之效。
在此之后,我与饶公仍偶有书信往来,也曾寄书给他。但因饶公年纪越来越高,各种应酬却依然不减,我就不好意思再主动去打搅他老人家了。之后又有三次见到饶公,一次是2006年“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举行,我赴港与会,借照相之机,拉住饶公的手问候了一句。一次是2011年11月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简帛、经典、古史研究国际论坛”,饶公在台上,我在台下。那次饶公露面的时间不长,且周围始终围满了人,连近身的机会都没有。一次是2012年“海上因缘——饶宗颐教授上海书画展”在上海举行,在上海西郊宾馆举行的欢迎晚宴上,我趁间隙跑到主桌旁抢上前问候了一声,此时饶公已经是95岁高龄,连讲话都已吃力,只见他微微颔首,算是回应了我。2015年在香港大学举办的“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也邀请了我,可惜我因故不能脱身,没能去成,失去了最后一次拜见饶公的机会。
饶公被学界誉为“业精六学,才备九能”,举凡甲骨学、简帛学、史学、敦煌学、吐鲁番学、文学、考古学、目录学、史地学、比较文字学、方志学、儒释道、中西交通、古乐史、古画史等领域,都有深入的钻研和著述,不能不说是真正的“通人”。饶公的学术以文学起家,他一生挚爱《文选》,故号“选堂”,他曾跟我说过“所有文献都是文学”一类的话,让我至今难忘。除了研究学术,他同时还写诗、写字、画画、弹琴,集学术与艺术于一身,以文养艺,以艺助文,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如此融会贯通的结果,造就了他在学术和创作上汪洋恣肆、波澜宏阔的气象。饶公熟读传统经典,不受四部约束,重要典籍反复熟读,尤其是四书五经,他跟我说他每年都会重新翻阅。饶公看书有折页的习惯,我在港期间,就看到他的很多藏书中都有不少折页,以致使书变厚许多,这无疑透露了饶公的勤奋。因为读书杂、涉猎广,自然会注意到别人注意不到的内容和问题。如20世纪80年代初,饶公和曾宪通先生合著了三本书,即《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和《楚帛书》,其中涉及乐律、古乐理与天文的关系、宇宙生成论、像纬、五行与纳音等冷僻的内容,有些非常专门,这是学术视野狭窄、知识面不广的学者不易把握的,只有像饶公这样的“通人”才能探赜索隐,得其奥秘。
饶公一生视学术为生命,寝馈其中,乐以忘忧。他对学术始终抱着一颗好奇的童心,时刻不忘掌握新材料,了解新信息。至今每想起他一收到新书就急于打开翻看时的样子,就让我对自己的懈怠愧悔不已。饶公对待新事物从来都是持欢迎态度,记得2002年时我在香港,当时《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刚出不久,书寄到饶公办公室后,我第一时间翻看了几页,并记下了一些想法,随即写了一篇小札记发到了网上。饶公看到书后也非常兴奋,连夜翻读并很快也写出了文章。当得知我已写了文章且发到了网上,很感兴趣,专门到我的办公室来让我把他的文章也发到网上。记得饶公就站在计算机桌旁看着我操作,当我录好文章发到网上并指给饶公看时,饶公差一点就手舞足蹈了,脸上露出了一个孩子刚得到一个梦想多日的玩具似的开心表情。
饶公在学术上是“通人”,在做人做事上也非常通达。他一生自然也经历过很多坎坷,一定也遇到过诸多不如意之事,但仅以我与饶公的接触而言,便感觉他似乎总是充满着激情与快乐,不消沉,不抱怨,不随意评骘他人;待人以善,示人以诚。尤其对待年轻后辈,更是悉心护佑,提携有加,示后学以矩矱,度晚辈以金针;有时像个老顽童,跟年轻人开一些轻松的玩笑,显得亲切可爱,更赢得后学晚辈的推崇和拥戴。
饶公对儒释道都有精深的研究,对道家养生术亦有独得之秘。记得有一次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他的办公室内,他在那张部分已经磨光的黑皮沙发上,居然不用手协助,就直接以双盘的姿势表演了入定打坐给我看,让我不禁瞠目结舌。要知道当时饶公已经年近八十,竟然还有如此厉害的腿脚功夫,真让我这样的年轻人自惭不如。饶公对养生术的钻研,加上他开阔的心胸和参透的气度,让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他能够寿登期颐的原因。
饶公的学问以宏通见长,能由小处识其大者,故常有凿破鸿蒙之论。读饶公的论著,需从大处着眼,由宽处体察。若龂龂于细节,不识其“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之妙,便会因小失大,陷于苛狭之境。总览饶公的学术成就,其披览之富,识见之精,思辨之密,成果之盛,当世学者,确乎无出其右者。
我一直认为要公正地评价一个学者,需从三个方面综合考量:一是学术能力,二是事业贡献,三是社会影响。三者虽互有交叉,但仍可独立。对一个学者来说,这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能够两项偏强的学者,就应该算是著名学者了,若能三项都偏强,那一定是近于大师级的人物。无论学界如何评价,我将饶公列为三项都偏强的学者之列,大概不会有人表示反对吧?
饶公虽然走了,但是他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学术和艺术财富,种下了替往圣继绝学的种子。他的学术恩泽,将永远沾溉后人,无穷无已;他的学术火种,将薪尽火留,代代传递。我作为一个曾受他提携奖饰,得其指点教诲的后学小子,将始终怀念他,怀念那个慈祥可爱的饶公。
(作者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刘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