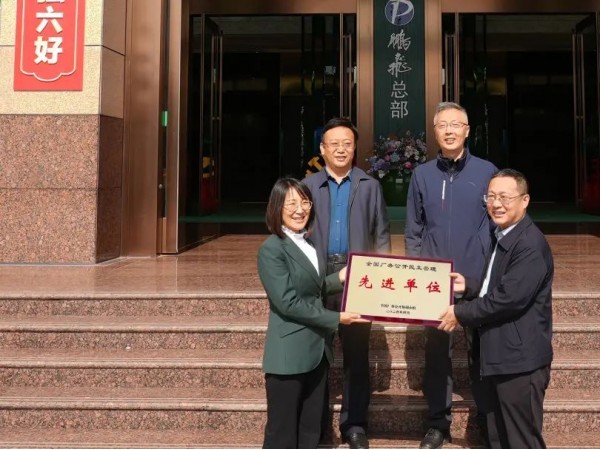封控这个事就像红萝卜蹲粉萝卜蹲一样,这个蹲完那个蹲,迟早轮到你。
以前是整个城市蹲,后来精准了,有的是按区蹲,有的是按楼蹲,此起彼伏,一浪一浪的,可好看了,可有时候蹲着蹲着就又全蹲了,整个城市又静默了。
太原就是这么个城市。
前几天还只是听说哪个小区或者某个楼高风险了,也就当个新闻听,不以为然。
接着小店区就传来消息有了确诊,也不知真真假假,大家讨论了一阵,第二天平阳街道就静默了。我住的酒店离得近,马上就有了危机感,飞一般的就搬到了河西住。
果不其然,第二天整个河东就静默了。
我住在河西的高楼上,摇着羽扇,看着静悄悄的河东,心里得意的笑,得意的笑。
笑着笑着就睡着了。
连我的智商都睡着了。
结果第二天正在房间努力工作呢,忽然有不详的感觉。
转头一看窗外,几辆车正停在十字路口,几个工人正在地上钻窟窿。
不好,莫非这边也要封,我赶紧跳下楼打听消息。
果然,河西也封了。
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吗,怎么一夜之间就同化了。
我很想跑。
因为我咨询了宾馆的前台,在疫情期间她们并不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一切都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办事。
我说没钱点餐,她们就笑,笑的花枝乱颤,一点不相信我的话。
她们以为这是一个大款的幽默。
我说你们就不怕饿死人吗。
她们说不会的,你可以点餐。
我无语,这不又回到原点了吗,算了,你们就等着收尸吧。
我决定出去自谋生路。
买张票回家去。
我死也要死到家里。
这是一个山西人骨子里对故乡的执着。
我出酒店打探消息的时候畅通无阻。
但街上到处都是铁皮封路。
能通过铁皮的车都不是一般的车。
我赶紧给约好的出租司机打电话。
我问你的车是不是一般的车,能不能顺利的从桥东跑到桥西来。
他说他也不知道,让我看看周围有没有能上下滨河西路的路口。
我东张西望了一阵,总有种地下工作者逃关卡的感觉。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回去问问宾馆的人吧,或许他们知道。
我返回宾馆的时候遭遇了盘查。
一个小伙子保安义正言辞的拦住了我。
我说我是店里的客人。
他说客人也不行。
我说我刚出去。
他说刚出去也不行。
我说我行李还在房间呢。
他说那也不行。
我说我出去的时候咋没人拦着。
他说刚刚下的通知。
我说顾客是上帝啊,我就是上帝。
他说上帝也不行。
我说卧槽,我就要进去,耶稣也拦不住我。
于是小伙子掏出对讲机找援兵。
他的队长还不错。
问客人有房卡吗,有核酸检测证明吗,有健康码吗?有就让进去吧。
我骄傲的亮出了所有。
回到房间我有点犹豫。
我是不是该走呢。
透过窗外,路口的铁皮又来了一层,弄成了个瓮城的形状。
我忽然想到,我要回去的那个城市我好像也不认识什么大白和哨兵。
我回去会不会有更悲惨的命运等着我。
我是不是又一次自投罗网,又一次被瓮中捉鳖。
我究竟会被在车站滞留还是会被集中隔离。
还是顺利的再次居家健康监测3天,又一次在孤独寂寞中不停的吃泡面吃到我想逃。
外面雾蒙蒙的。
什么也看不清,一道道的铁皮就像一道道的城墙隐隐约约。。
悲凉油然而生。
什么世道啊,好好的天不见天日,好好的路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