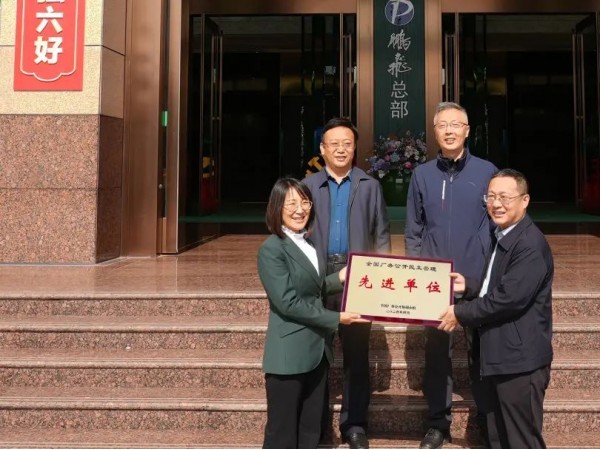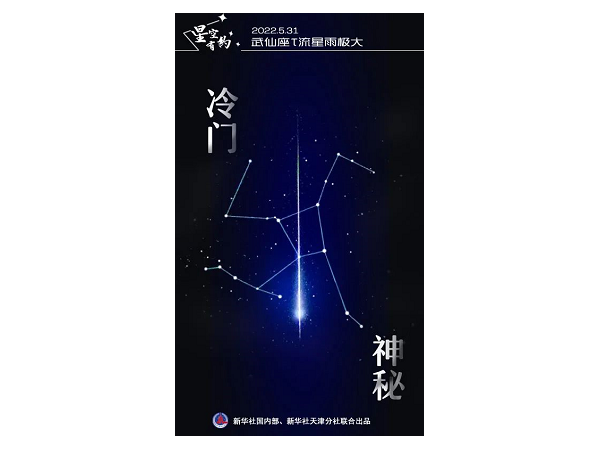今年9月初,私募基金会世资产前总经理侯贵程的几条聊天记录在各个微信群里流转,控诉公司实控人张议夫没有兑现曾经的对赌承诺。
侯贵程的说法是,自己以合伙人身份加入会世资产,主要的工作是销售,并约定了公司规模新增20亿就能获得3%的股份,新增40亿获得5%。
今年7月份,会世的规模已经扩张到了53亿元,侯贵程认为触发了解锁股份条件时,公司不仅没有兑现承诺,反而在兑付股权截止日当天和他解除了劳动合同。
在规模各异的私募基金里,矛盾的呈现有几百种方式,但成因几乎都是围绕钱来展开。这背后又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管理规模,但把量做上去之后,销售和投资,如何分配?
销售往往会觉得自己的募资能力推动了公司规模的扩张,做大了奖金池;但投资团队会认为产品业绩才是核心因素。
市场往上走的时候,发展是第一要务,矛盾只会积累不会暴露。但市场动荡阶段,冲突就是主角,收尾大多潦草,正如会世的结局里,双方在声明里表示和解,侯贵程离开公司。
私募基金的内部斗争和互联网公司宫斗一样,动辄涉及金额巨大,但前者在舆论层面的影响力小了很多,大量的讨论停留在了一个又一个行业内的微信群里,销售同行们愤慨又无奈,普遍的情绪是心有戚戚又道是寻常。
“会世的事情,你也看到了吧?闹成这样,说什么合伙人,到最后还是只把你当打工人。”
说这话的是另一家私募的销售晓文(化名),像会世这样的事情,离他还很遥远,毕竟今年能把量卖出去的私募销售已是凤毛麟角。产品还在创新低,晓文依然得硬着头皮到各地出差路演,“这年头虽然出差比以前更辛苦,我也不想回办公室,要是被老板看到,他又要问我,前面有管华雨,后面有周应波,市场明明是有钱的,为什么募不到我们这里来?”
晓文说完这话,打开了一个第三方数据公司的APP,拉出他们公司产品的回撤页面让我看,“他问我之前,怎么不先看看自己今年亏了多少?”
在一个私募基金里,“基金经理-销售-客户(包括直销和代销渠道)”构成了一个抽象的链条。在这个三角关系里,中间的角色常常被忽略,客户只关心要买哪个基金经理,并不关心是谁把基金卖给了你;基金经理多数也只想做投研,不愿把时间花在服务不如自己懂投资的客户上。
金融投资是基于信息和认知的交易,销售则是迂回在投资经理和出资人之间的中间角色,向这个链条的两端频繁地传递着大量的信号或是噪音,他们或许并不擅长投资,却极大程度地影响着买卖决策。
另一方面,资管行业是学历和智商的高地,却往往是管理制度和组织治理的平原。对于销售来说,他们的收入取决于很多因素:盖着公章的合同,几乎没人从头到尾读完过的员工手册,公司的业绩表现,以及拥有一切最终解释权的老板。
牛市到来的时候,增长可以掩盖一切问题。但当潮水退去,不是所有人都熬得到牛市回来。
01
今年没有奖金
入行三年多,许琪(化名)一直在一家主观股票私募维护一些代销渠道,2022年是许琪经历的第一个“周期底部”。
就像每一个深谙行业话术的人一样,许琪特地补充了一句,“底部不是一个点位,是一段区间。”漫长是痛苦的关键。她像一只无法预知春天何时会来的候鸟一样,悬而未决的等待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气温的变化,从一开始就不掌握在她自己手上。
去年的同期,许琪每天至少要回复上百个人发来的微信,路演排期比新荣记的包间还难定,代销渠道的人约不到办公时间,就约吃饭时间,约不到吃饭时间,就约晨跑时间,他们讲得最多的话都是,“XX的钱你们还能接多少”、“别废话了,直接把产品合同发我”、“上线材料今晚回复,明天一早过会上架,市场这么热不赶赶进度,难道要等跌下去?”
辛苦归辛苦,但看着公司规模从不到10亿涨到70多亿,许琪还是有动力的。她经常会在手机上用计算器更新自己的年终提成。过年之前,年终奖打到了她的工资卡上,虽然比她自己算得少了一些,但终究还是一个满意的数字。
今年,许琪依然很忙碌,只是需要回复的微信变得不太一样——“你们到底买了什么,能跌成这样”、“你们老板还在上班吗,不做客户沟通会吗”、“我们很认同你们的理念,但下季度的上架产品排期都满了,先保持联系啊”……许琪停顿了一下,“做我们这一行,‘保持联系’就是和‘下次请你吃饭’一样的存在,成年人看破不说破,但自己心里要有点儿数。”
2019年~2021年的三年里,股票市场极其繁荣,潮水也推动着大量私募基金的规模水涨船高。许琪所在的私募基金,擅长讲选股的故事,高集中度的长期持有也是能在那一波浪潮里崛起的常见流派。像这样的主观股票私募在市场上并不少,大多维持着十几个人的精简团队,除去一半以上的投研,几个包揽了行政、人事、财务、运营和品宣的中后台之后,也就剩下三四个人的销售团队。
这些销售需要开拓和维护的渠道一般按照区域(比如:华南、华北、华中、华东)或者机构(比如:A负责XX券商、B负责XX银行)来划分,每年大量的时间都在各家机构的分公司、营业部搞巡回路演,见不同的人,讲一样的PPT,目的只有一个——稳住存量,卖出增量。因为这些都是能算出来的收入。
像大部分行业一样,私募基金的销售也能用底薪+提成的方式计算报酬。提成的一个比较常见的参考标准是当年新增销量的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五,也就是说一个私募销售如果一年能够卖出10个亿的规模,那他当年的奖金就可以达到知乎人均水平。
但理论往往是灰色的,现实是会放鸽子的。实际上,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公司里并不存在这种计算规则,也没有什么事前的比例约定,全是到了年终,看老板怎么拍自己的脑袋。
“最后一个季度市场会怎么样,我已经麻了。反正老板预期已经给好了——今年没有奖金。”
2022年作为她经历的第一个“周期底部”,老板的大白马组合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回撤,她也被渠道和客户骂得狗血淋头。许琪已经不记得自己在坚强地保持了路演的体面后,在滴滴上哭了多少次,然后续上自己的核酸记录,赶往下一个城市和下一场路演,但今年依然卖不出量。
许琪也不觉得自己所在的机构管理上就是更粗糙,她认识的同行越多,就只觉得这种粗放的管理遍地都是。
“面子上说起来头头是道,里子拆开来大部分私募在管理上都是草台班子,业绩好的时候卖出去老板觉得是投资的功劳,业绩不好的时候卖不出去老板觉得是销售的问题。你只能拿个比例当自己的心理预期,给够了,开开心心继续卖命,给少了,就先苟着等下一个牛市。”
许琪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说自己的心态都是在“比烂”里练就的,“我们老板真还算好一点的,我朋友那儿才夸张,眼看2022年都快过完了,他们老板说2021年的年终奖算错了,发多了,今年不仅没有年终奖,还要从每月基本工资里把他们‘欠公司的钱’扣了。”
02
谁还买主观
资本市场的涨跌其实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主观多头来说,有更深层的不安在弥漫。
主观多头策略的私募基金,这两三年光景越来越难,客户随便两个问题就能让公司陷入“存在主义危机”——一个是为什么不买量化,另一个是为什么不买公募。
花木路堪称上海的私募第一街,对于要亲自算成本账的私募老板来说,一方面陆家嘴核心区的写字楼还是金贵了一些,另一方面再怎么金领的工种,对于上班都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离家近。毕竟看集中度的话,把家安在联洋的基金经理占比可能不输张坤组合里的白酒仓位。
像世纪公园西边的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私募基金的密集程度就令人发指。用陈真(化名)的话说,“我就在我们那层楼上个洗手间,都能感受到量化私募对我们主观多头的压制。”
从2018年开始,陈真就一直在这片5.34万平方米的写字楼片区工作,供职机构也一直都是主观多头的私募,然后见证着量化私募的异军突起。楼上的主观兄弟今年刚裁完员,二座另一家经常往来的私募就说降薪了,只有对门的量化和他的程序员朋友们办公室越租越大,视频号里出镜的小姐姐越来越漂亮。
在2019年、2020年那样的大贝塔行情里,诞生了许多百亿私募基金,新名字里大多数是成立了没几年的量化。牛市里,大家看收益,量化的指数增强产品线那时也都还有比较稳定的超额,每周五傍晚净值预估一出现在各个渠道微信群里,就是超额又增加了多少,简单粗暴的收益体验,让量化私募变得非常好卖。
从那时开始,陈真就已经开始感觉到了压力正在慢慢积累。路演上偶尔会遇到一些渠道的理财经理,拿着Preqin的全球对冲基金排名榜,关切地发问,以后中国的主观多头是不是也都会被量化取代?
面对这种“结构性”的冲击,主观多头们看上去并没有特别多的应对办法,基金经理们也很少认输,至少不会在牛市里认输。
2021年以前,主观、量化齐头并进,大家的净值曲线都在往上跑,陈真还能讲讲主观选股和量化指增的收益性质不一样,主观要找的是能满足预期收益率的十倍股,看的是赔率;量化看的是胜率,是不断地积累小胜,胜率高于50%就做交易了。“没什么非黑即白的,都买不就好了,还分散风险呢。”
但从2021年开始,行情一分化,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活在消费升级里的私募们基金净值下沉了,靠着苹果产业链起来的,风头被特斯拉产业链盖了过去。量化们倒也遭遇过指增超额衰减的阶段,但毕竟还有市场中性,中性额度不够了,也还有CTA,或者把多策略打包成复合产品,又是一条新产线。但主观们做来做去都是复制策略,产品再多,用周立波脱口秀里的话来说,“从6124点往下看,都是熊的传人”。
百亿私募开始新陈代谢般的大换血,新生的都是量化,代谢的都是主观。净值曲线增长一旦失速,老板一旦选择性断网,销售们就得主动站到渠道、客户千夫所指的第一线。
进入回撤如雪崩的2022年,私募基金2%+20%的费率结构已经被骂成了共同富裕税,专门收割高净值人群。“就算量化费用更高,客户也不会去问量化,他们知道私募量化比公募量化能做的事情更多,就盯着我们问,你们的净值波动也很大啊,我为什么不去买公募?你们还要计提业绩报酬啊,我为什么不去买公募?”
“每天就是回答不完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吗我比他们更难受。”陈真2020年下半年的时候卖掉了老家的一套房子,那时候老板2018年底发的产品净值刚翻了一倍。陈真自己身处资管行业,看着自己的老板意气风发,也对当时居民财富从房产到权益大搬家的逻辑深信不疑,卖房的现金直接申购了自家公司的产品。
在短暂的收益愉悦之后,持有到今年9月底的他,已经被套了40%,大半年亏掉的钱比老板这几年加起来发的工资还多。“说起来都是一个人亏的,客户还能怪基金经理不行,但他不仅是我基金经理,更是我老板,他和客户还说对不起,对我只说工作上再努点力。”
眼看着同行开始降管理费,陈真的老板也开始考虑表现出让利的姿态,十一长假前还专门找销售团队开了个会,陈真写下的纪要很简单,“降费也是为了帮助我们销售做业绩,让的利就从我们的提成里扣。”
03
今时不同往日
行情不好,卖不出量,提成拿少一点,路演辛苦一点,在许琪看来,都是销售这份工作的题中之义。只是当老板今年不想发年终奖时,说出的那一句“今时不同往日”还是让她十分沮丧。
在牛市的热闹里,挤进私募行业里当了几年销售,许琪在如今的市场低潮期里对行业也有了一些体会。“在这个阶段,国内好多私募基金本质上就是一个小作坊,你无法期待一个所有事情能按规矩来履行的治理架构。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和价值上的认同,销售只能活在短期的数字里。要保住自己的收入,牛市里火上浇油可比熊市里雪中送炭更容易。”
对于私募基金行业来说,这似乎也是一个难解的矛盾。
基金经理们是一群自信的精英,因为不自信很难做好投资,但太自信又很难做好管理。而当投资就是一个公司唯一的业务时,管理看上去并不重要,它听上去也与净值曲线完全无关。哪怕到团队分崩离析的时候,客户似乎也只关心一个问题——“我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去哪里?”
因此,在“基金经理-销售-客户”的三角关系里,销售面对的冲突最多,传播杠杆最大,又往往最脆弱。而当一种成建制的利益分配与治理结构在市场参与者中大量缺位的时候,明知这一切不过是一场又一场潮汐运动的人们,又如何去在乎所谓的长期主义?
短期业绩一好销售就疯狂上量,大量客户的钱套在市场山顶的事情,只不过是写在每一轮周期里的既定悲剧。
一切都像查尔斯·狄更斯在《大卫·科波菲尔》里写的那样——住在海边的人,不到潮水退到底的时候,是不会死的;不到潮水涨满的时候,他们也是不会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