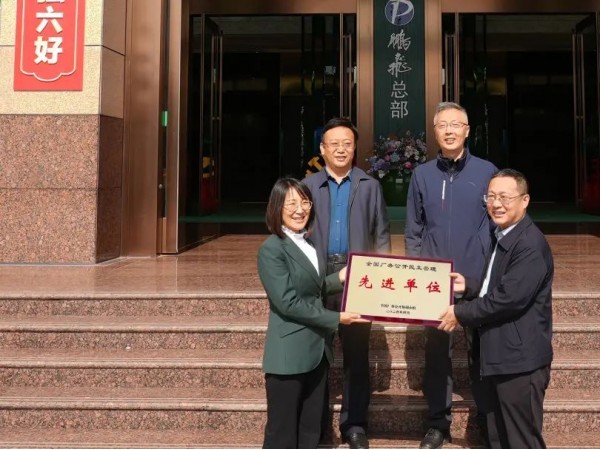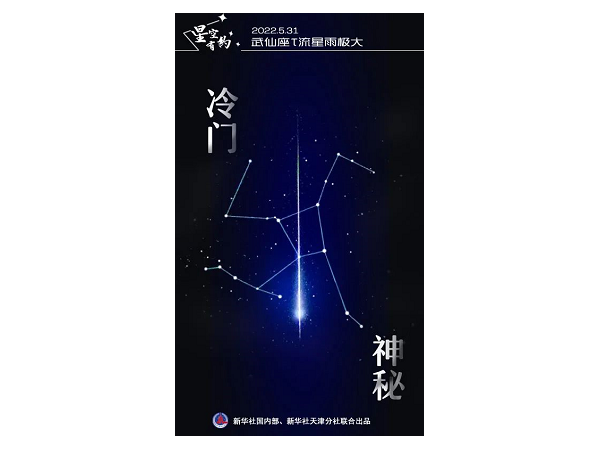“为了让历史读物变得容易理解和讨人喜欢,一般来说,我们要采用一种轻松的、口语化的风格;要在这里或那里制造一些适当的‘情调’;要提供一些必要的‘背景介绍’;要借助悲伤引导出一个适当的思维框架;要用幽默的微笑遮盖历史‘干枯的骨骼’;在了解当地人生活和特点的前提下,用我们自己的行话把不连贯的细节连接起来。”
这段话来自于帕特里克在第六章中引用的祖鲁人历史的收集者阿尔弗雷德·T.布莱恩特。他用一种被他比作艺术家组装马赛克的方式将信息联合在一起,他所使用的原始材料以及大众读者显然都对他用碎片拼凑而成的马赛克画产生了影响。首先,作为一个受过古典文化教育恩惠的基督徒,他通过组织素材,在祖鲁人的迁徙与《出埃及记》中希伯来人的流浪以及中世纪早期伦巴第人、哥特人和斯拉夫人传奇般的迁徙之间建立了明确的相似性;其次,布莱恩特不仅以希伯来人或欧洲人的族群演化过程为模版来构建祖鲁人的历史,他还将欧洲传统所反映的动机与意义加入到他理解祖鲁人历史的方式中。这是他有意为之的,考虑到欧洲的读者会认为他的题材既“无吸引力”又“太过陌生以至于无法理解”。
帕特里克同样如此。为了让陌生的内容对于非欧洲读者来说更加熟悉,他做了许多尝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断引出欧洲文化传统与新的欧洲族群之间的相似性。作者曾在一个讲座中明确地向读者解释,他要做的是在当下历史争论的语境中,去考察晚近发生的、以及他更熟悉的欧洲中世纪发生的涉及记忆和历史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会考虑到处理记忆、历史、历史与记忆的合流、对二者的滥用和套用的各种方法,并把它们置于当下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
在这段话中,我们首先要记住几个词语:历史、记忆、合流。帕特里克在这里所说的“记忆”,所指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个体的记忆”或“曾经发生过的具体事件”,也不同于艾略特所说的文学意义上的“回忆”,而是自19世纪以来,欧洲为自己的社会构成与生活方式所建造出的一整套的价值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观的认识体系,一个储存历史以便于我们能够使用它的模型。在过去的几年中,记忆与历史的关系以及记忆的历史始终是公共舆论的热点问题。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新范式,是对当下欧洲社会存在的根本性问题的回应。《民族的神话》在前言中向读者们说明,近现代以来的欧洲所面对的诸种问题——二十世纪的金融危机导致欧元贬值、国内恐怖主义的抬头、以及移民与难民问题的冲突——使曾以为在二战之后将会实现的统一性被强烈的身份危机所取代。1992年欧洲共同体确立经济和税收改革,一些人翘首企盼着统一货币、消除内部关税以及公民自由流动带来的前景,而另一些人却是在犹豫甚至恐惧中等待着这些改革的发生。然而今天,一些欧洲国家暂停《申根协定》,欧盟成员国在如何安置难民问题上争议不断,英国退出欧盟……不仅未来值得怀疑,过去的历史同样如此,许多历史学家致力于理解导致罗马帝国崩溃的那些认同、种族、宗教与文化,那么在现在的欧洲,它的人民应该如何诉说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在经历了材料综述、语言学转向与去中心化历史研究之后,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研究中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开始讨论“欧洲身份认同”的遥远起源,尤其是基于不同的族群认同。那么在这些族群、地区、宗教的复杂历史之中,欧洲的身份认同又在一个什么位置?这些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分散政治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否构建了一个更大的统一体呢?帕特里克显然将这种传统叙事纳入了考虑的范畴:“部落或家族这样的单位、划时代的战役和传奇般的迁徙,所有这些都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而且常常与犹太人出埃及的故事以及希腊-罗马时期的民族志联系在一起。这些历史绝对不是真正‘民族’的历史。相反,这些历史以作者所关心的政治和文化为基础,为了推进作者所处时代的进程,作者对他们进行了重构。”
引申来看,欧洲并非简单地为欧洲的国家与人民所构建,它本身就是历史的造物,是不断努力理解的结果。它当然是重要的。欧洲的族群和民族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才演变至今,这个过程剧烈而模糊,它不是用几个引人注意的词语——“共同体”、“民族主义”就可以概括的。
19世纪的历史学以服务民族主义为目的,它所遗留下来的认识已经不再恰当了。无论在欧洲世界的内部与外部,社会和政治群体始终都是复杂的、永远在变化着的共同体,它们的认同、身份和目标永远都是可以协商、争论和转化的。从一开始,跨越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蛮族就不是说着相同语言、有着相同文化的群体,他们既不是通过血缘也不是通过共同的民族传统联系在一起的。
在书的结尾,帕特里克强调了这一点:族群变化的过程绝对没有因为可以辨识的中世纪王国的出现而结束,欧洲人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且永远不会结束。
“我们起来吧,阴影常常对歌者不利:
刺柏投下的阴影尤其如此:
那阴影会大大伤害到作物。
回去吧,我的羊儿们,你们都吃够了,
晚星已升起,我们也该走了。”
——维吉尔《牧歌》第十首
这段诗描绘了古罗马浪漫旖丽的田园幻梦,在牧歌的结尾,诗人切切地唤着刺柏阴影下的羊群退场,并望着天边的晚星告诫我们,此刻的时辰不再利于滋养作物与他自己。维吉尔一生都以写作为职业,歌颂普通人民的崇高和民族精神的高贵。无论是作者还是听众,写作这一职业本身就假设了一个问题:一个民族的杰出之所以在于它自己,因为它部分的对自己所拥有的历史与记忆有一定的认识。但与此同时它是如此孱弱和纤细,以至于时时刻刻需要所在土地的滋养。在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暗喻的功效是消极的,但在历史编撰学的角度来看,则是阐明那些看似无关甚至被遗忘的,但却以各自的方式同经验、回忆和拯救暗地相通的具体而发人深省的实例,至少是让我们可以依仗历史语境的根本,去参验外缘民族问题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