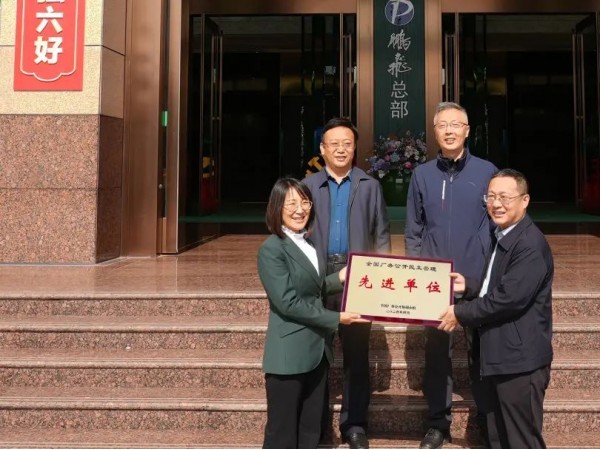在不确定的世界,当某个经济体用时间换空间的压力与成本越来越大时,当其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不及下行坠力时,当监管不及金融创新之时,也许有必要深剖其日后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无论承认与否,从债务链之险情看,按照国务院参事夏斌的话说,中国实际上已经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虽然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特殊国情,当下的中国不会发生美国式金融危机,但倘若依然是押后潜在风险,倘若长期市场不出清,难保某一天,30多年积累的国民财富不被侵蚀。
国际上,IMF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1%,较前次预测降低了0.1%。避险情绪卷土重来,股市和风险资产恐再度下跌。
从国内看,尽管二季度中国经济数据好于预期,某些领域亦呈现稳中有进的态势,但投资增速下滑尤其是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依然会延续,地产投资恐将继续回落。
经济下行时,多年积累的问题与风险也会相继暴露出来。
导火索可能是债券违约,也可能是房市泡沫破灭,包括一系列复杂的资管计划或隐含的潜在金融风险。
经济观察报特此采访了国务院参事夏斌。他正致力于其在2015年与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发起并成立的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之中国事业,鼓励理论创新,繁荣经济科学。推动寻找“历史的、理论的、实践的”三者中的理论创新之中国路径,期翼揭示体现国别经济或者是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普遍的、抽象的规律。作为政策谏言者,夏斌所言,剑指处于困难、微妙调整转折期的中国之痛点。
中国经济怎么了
经济观察报:你曾在2014年发表了中国经济形势的“万言书”,提到对于中国经济不必过度悲观,亦不能盲目乐观,从今天看,二季度GDP6.7%的增长率,是乐观多一些还是悲观多一些?
夏斌:现在,还可以坚持这句话,“不必过度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为什么?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确实还是好的,动力是强的,但短期压力确实很大。这矛盾吗?其实不矛盾。因为短期转型仍在过程中,问题还在逐步暴露,确实存在不少困难,也有不确定性。但是从长期看,我认为,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累积的市场动能趋势和改革文化在国民中已基本确立,这是最大的乐观,最大的希望。尽管近期改革有些缓慢,但大势谁也挡不住。而且,从经济增长的一些要素看,供给方面的人口与高储蓄率因素,需求方面的地区与城乡差别以及中产阶层形成的大市场因素等,能支撑中国继续增长,支撑中国在GDP总量上去赶超美国,这是大的经济逻辑。现在要比经济增速,中国应该与世界前五大经济体去比,不能与小国、小经济体比。如此思维的话,中国增速即使跌到6%,仍然是绝对的高增长。美国、欧元区、日本2016年上半年增速都低得可怜。
中国经济减速这一问题,现在为何这么敏感?第一,按照市场逻辑,这么大的经济体,增速下行较快,在这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和风险暴露。怎么解决?目前思路还没有太清晰,或者说在具体执行中效应还不明显,所以会比较焦虑;第二,在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已为第一的情况下,如果中国转型中的“麻烦”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会影响汇率走势,影响各种资产价格,影响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当今又是全球化的时代,这就不仅直接关乎中国经济能否走出转型期的问题,也直接关乎外部的世界,而外部世界本身又那么脆弱。中国经济要调整,世界各国都需要调整。
经济观察报:去年你指出,有两种调整方式:一种是单纯被市场规则强行约束,被强制性调整——类似经济危机。一种是适应市场的逻辑,政府进行适当干预,自觉调整。那么,从目前看,中国的调整是否符合预期?
夏斌:应该说调整是个长期的过程,还在过程之中,风险在逐步暴露与化解,经济结构在逐步改善,现在正处于痛苦与微妙的时期,分化和不确定性是其明显的特征。
回看历史,美国2008危机之所以爆发,也许可以从美国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合著的书《这次不一样》中找到依据。正如那本书所言,美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2007年之前,并不认为全球经济不平衡不可以持续。他们认为,中国高储蓄、美国高消费,只要一直这么延续下去——中国资金投入美国金融市场,美国就不会发生像1929年那样的大危机,因此有“这次不一样”的结论……这至少说明,当局者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想到,也没去预防危机,认为靠市场能自行解决问题。当然危机爆发后,为了稳定社会,最后还是需要政府出面。所以说,单纯被市场规则的强行约束去调整的话,很被动,很危险。
再看看我们,经历2003至2011年这样的“超级繁荣”后,现在大家都已看到这一模式不可持续。因为在“超级繁荣”时期之出口、投资为主的发展模式下,投放了几十万亿级的贷币,分布在制造业、房地产等领域,现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全球需求体量明显缩小,我们企业的收入与利润必然减少,金融机构过去发放的大量贷款和融资,必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本息偿还困难。因此,在今天,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坏账和资本损失,从市场逻辑看是必然的。如果任其市场自行发展,企业债务违约和破产倒闭事件会频频发生,弄得不好还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金融市场结构变得复杂的情况下,经济体内各主体有其复杂的紧密联系,风险传递速度是相当快的。
此背景下,在基本顺应市场逻辑的前提下,政府作些干预,主动进行调整,也是一种选择。目的就是守住底线——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和大规模失业。这是稳定社会的基本要求。说底线思维当然并非说严防系统性风险爆发就不坚持处理僵尸企业的问题。正如李克强总理曾表示的,要允许有个别的风险暴露,其实表明了“该破的就要破掉,不破不立。”搞市场经济必然会出现“市场出清”,我们要去解决“市场出清”问题,不是一下子全部解决,但也要有逐步解决的计划。
不过,目前而言,就巨额存量风险的系统性解决,还没看到明确的统筹安排。
系统性风险怎么看?
经济观察报:中国社科院学者说,中国发生系统性风险“是小概率事件”。你认为中国是否必然会爆发系统性风险?
夏斌:我认为,我国政府对系统性风险问题并没有掉以轻心,也没有像美国学者那样放松警惕,认为“这次不一样”。在政策上,我在2014年曾提出,“非常时期需要有非常政策”,央行必须要发出让全社会弄得懂的银行流行性是充足的信号。事实上,近几年我们的货币政策是松的,因此我们不会爆发美国式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发生银行债务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系统性风险的隐患,特别是现在理财市场发展快速,影子信贷的交易结构复杂,对风险的警惕,做市场交易的是深有体会的。我们的系统性风险之所以未爆发,是因为我们已采取了一些国家发生危机后采取的救助与化解政策,货币政策是松的;是因为有些行政干预,不让银行逼债和抽贷,不让企业关闭与破产。因此分析系统性风险问题,不能简单地静止地看当前的不良贷款率。要知道,一般而言,过高的不良贷款率往往不是产生在危机之前,而是在危机之后。
经济观察报:对这些系统性风险隐患要怎么解决?
夏斌:我在2014年曾说过,为确保经济不发生“崩盘”,必须要有事先的政策储备,并适时干预。对已经形成的资产泡沫,如果仅靠市场力量调节或市场化改革,按照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必然会造成对宏观经济不可承受的剧烈波动或爆发系统性风险。所以,若要坚持底线思维,必须在市场预期明显改变之前介入干预。
如果已形成的泡沫,那么泡沫破灭或早或晚会来临。拐点何时出现取决于预期,但预期是无法预测的。当可能触发拐点的因素发生重大变化之时,预期则随时可能改变。
泡沫破灭对经济影响的大小是无法预测的,但是在泡沫破灭之初,保持或者尽快恢复银行系统的健全性,是减少泡沫破灭风险对经济形成巨大冲击的关键。
我在2014年的那篇文章中指出,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处于非常时期,即面临着房地产泡沫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在经济走势关键看房市,房市持续下跌已成定势之时,启动过度扩张的总量货币对冲房地产投资的下滑,必然再次放大资产泡沫及加大产能过剩;但是如果简单放任市场调节,其结果又必然导致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及银行放贷意愿迅速下降,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因此,非常时期需出台非常政策,引导预期,稳定经济。
以上是我在2014年的分析。时至今日,情况更复杂。出口对GDP的拉动率已几近为零,消费增长缓慢,投资中制造业产能过剩、基础设施投资中地方债务压力较大,在此一系列情况下,对房市政策确实更要小心,要细腻。
对系统性风险隐患问题,一是要认识到,及时释放与化解风险不仅不会影响增长,而且有利于稳定增长。已形成的风险,是已经造成的损失,是客观的,最后必然要有人埋单或减记某些经济主体的资产或权益。当风险数量少时,往往不易被察觉,此时如果不愿意将一部分稳增长的资金省下来去埋单化解风险,由于市场不能出清,资金为僵尸企业所占有,或金融市场上无风险收益率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利润率,结果就会出现一部分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创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最终反而影响经济增长。
所以,第二,要有积极的态度,主动化解风险。我认为,中国当前的国情有其特殊优势。因为在有些市场国家,严厉的法治经济下,市场法律约束与企业破产边界是极其清晰的。在国外,当一个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时,不可能存在总理为“农民工讨薪”的怪现象。在国外,当委托理财失败时,当然也不可能成立“信托公司保障基金”之类的机构予以保障。当微观风险累计到一定地步,只要没有特别的法律依据,风险最后只能以自身危机或破产的形式解决,政府不具有在法律制度改变之前擅自采取特殊的风险化解政策的权力。
但在当前的中国则不然。金融尚未全部对外开放,各项体现法律意图的市场化改革制度正在一项一项推进中,相关的市场约束仍然“不硬”或尚不明确,因此各种债权债务纠纷和拖欠行为尚存在大量“可协商”的空间。某种意义上这是件好事。这为我国政府利用当前条件,抓紧摸清家底,重新完善和强化市场规则提供了可能,可以做到一边埋单整顿、一边制定规矩,为防范更大的风险积聚和系统性风险的爆发赢得时间。
经济观察报: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下,今年的债券市场也是信用违约事件频发,请问系统性风险隐患具体到底怎么化解?政府、监管层该如何化解信用违约风险?
夏斌:对于这些问题,我曾在去年初关于《十三五时期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认识和思路》一文中说过,目前我们要当心,各种经济主体的风险,最后可能集中表现为国家的财政风险。由于我国各类市场主体的刚性兑付问题尚未解决,目前不管是地方债务风险、影子银行风险、互联互保风险、信托理财风险还是国企亏损破产风险,最后七拐八拐,风险往往容易集中在“姓公”的资产上,减记“姓公”的权益。而且,由于地方财政风险、金融机构风险、货币风险(贬值)以及社会稳定风险胶着在一起,加上金融风险波及面大、传递速度快、非线性爆发的特点,实际上已难以区分区域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的差别,很容易酿成全局性的国家财政风险。
存量风险怎么化解?我曾提出应需遵循“止血、共担、成本、时间”四项原则。我坚信从全局看,我们只要将新债务成本控制在经济增长率以下(如6%),则仍具有稳定的偿债能力。因此,在设法控制债务成本的前提下,对已存在的巨额存量债务风险问题,应通过先堵住漏洞,然后贯彻银行、企业、个人、中央和地方政府共担风险原则,通过延长时间是可以逐步消化的。
对于增量风险的防范,除去实体经济面的改革措施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因素外,必须坚决贯彻打破刚性兑付的原则。国家变相的隐性担保——刚性兑付原则仍未打破,这是当今中国市场默认的“潜规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各类风险债务之所以越垒越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主因之一。这是必须确立的原则,是防增量风险的最基础原则。
当务之急怎么办?
经济观察报: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出清太少,动作太小,对困难与问题又遮遮掩掩。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政策刺激的效应在递减,进一步扩大刺激力度又会增加新的风险。面对如此窘境,该如何改变现状?
夏斌:当前的经济转型之局,如何破?总的原则应是,守住底线,改革为先。当前的中国经济,不刺激肯定不行,不仅是就业问题,系统性风险马上会爆发,社会不稳。但是,过度刺激也不行,效应在明显减弱。“两难”面前怎么办?根本出路在改革。又必须看到,不是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是有利于短期内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有的改革措施有可能在短期内会从某些方面影响经济增速和暴露风险,进而影响局部的不稳定。怎么办?只能在改革的力度、措施的选择、措施出台时机的把握上,以守住两条底线为原则。
怎么守底线?一是在“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中要容忍逐步释放些风险,但又绝不能主动引发大规模的、系统性风险。二是在改革与转型中,在企业破产重组中,尽量安置好下岗失业人员,不能出现大面积的社会不能容忍的失业局面。只要守住这两条,紧紧“咬住”改革不放,改革为先,中长期就会有希望。短期内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不必去在乎。
承认损失,统筹安排。面对经济由过去长期“超级繁荣”转向常态、健康发展中所暴露的存量风险,要认识到,这是已经发生的损失,要有人买单。“三去”中的单怎么买?仅靠安排1000亿资金安置人员费,“三去”问题根本落不了地。
因此要主动去研究,“三去”中全国共有多少债务缺口?准备让银行、企业、政府各承担多少?分几条渠道承担?如债务重组、破产、债转股、财政赤字债等。准备用多长时间解决?实际上是拿当代人钱还是后代人钱,是拿央行的钱还是拿财政发债的钱的问题。
抓住重点,倒逼改革。首先一定要认识,改革千头万绪,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命穴与关键,不是其他,是国企改革。我们都在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如何培育这一机制?一需市场主体,二需市场信号。前者,企业主体行为不端正,后者,价格信号肯定会被扭曲,市场信号永远建不起来。这已被30多年的改革历史所不断证明。
除需抓住的“命穴”改革外,另外还需重视的三项改革是,一是全社会养老保障统筹。应该借这次解决“三去”中资金损失时统一算账,尽快形成稳定社会的基本国策,一次性解决中国经济今后长期发展中早晚必须解决的社会养老保障这一“安全阀”问题。该补的补(补地方缺口),该统的统(全国统一)。二是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改革中“三块地”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收入进而扩大其消费,是我国短期结构转型、长期成为消费大国的一项需持续奋斗的战略任务。农村土地资产有约89万亿元,如何释放农民巨大的财产收入?三是面对民营投资占全部投资在60%,民营投资增速近来急速下降的困局,怎么办?看来靠一般文件指导、领导讲话和上级督查难以扭转。要有针对性研究,拿出实招,才能解决问题。
容忍减速,实事求是。面对近年内国际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国内经济的“两难”局面,破局之策,不能仅靠追求经济增速。过于强调增速,反而易在工作中造成被动。我们曾经讲增速是为了保就业。现在GDP每增长一个点所创造就业人数,已从危机前90万人增到2015年的193万人。按此推算,2016年GDP若降到6%,仍可达到就业人数1158万。看来经济增速与就业的关系在慢慢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能否结合国际国内新情况,对GDP的减速多些容忍?对这一纲举目张式的指标要求,多些弹性解释?这样一来,其他工作就不会太被动。但对十八大提出的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目标仍不变。这“一变一不变”的目标如果在适当减速的环境中实现了,则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经济结构将更合理,社会将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