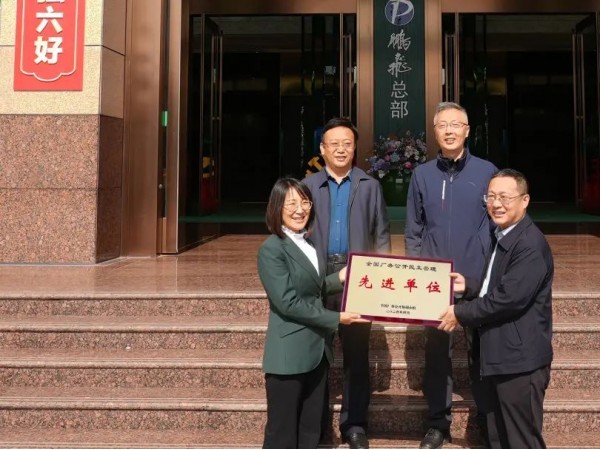“不好意思,我们现在不要教育机构的”。张方从面试官的口中听到这样的回答,“最近来面试的都是这行的”。
教育机构的裁员没有终止,寻找下一份工作也变得更困难。
从教培行业短期内涌出了大量人力,他们经历相似,求职心急。一名前教培从业者每天睁开眼睛就打开招聘平台,接受降薪,希望得到转行的机会,“几乎刷遍了所有有可能的岗位”。
一个月过去了,张方投出了近200份简历,但还没能找到新的工作。
躲过了教培行业的第一批大裁员,张方原本以为自己是幸运的。
但没过多久,整个校外培训市场急速收缩。生死压力面前,大多数公司选择压减成本、增加工作量,试图以最小代价撑过转型期。
第一批裁员中的“幸存者”们发现,自己的工资少了一大半,考核标准却更加严苛。一名从业者称,其被通知转签为非全日制合同,他认为,这意味着“从正式工变临时工,被裁就一句话的事”。
人心惶惶,他们开始羡慕第一批被裁也拿到“N+1”补偿的那些人,“好歹,给个痛快”。

一名前教培行业从业者求职时,得到了“现在不要教育机构的”回复。图源:某社交平台
幸存者:KPI大幅上升,压力越来越大
很少有人留意到一些福利是哪天开始取消的。每天供应的水果不再补充,办公室里的零食柜空了,节日礼物变得简单,赶上中秋节,几家员工在社交平台晒出的只剩月饼,“有就不错了”。
在线教育公司的福利曾让人羡慕,受资本追捧时,教培行业出手阔绰。李凡刚入职时,发现公司提供免费的合作健身房,是一家在当地“很贵很贵”的机构,庆幸自己选了份好工作。另一名辅导老师印象深刻,每个人每年有7000元的旅游基金。
好光景不复存在。“双减”政策发布前,听到风声的教培企业已开始收缩,李凡眼见隔壁部门的同事一组一组被裁掉,沉默地离开工位。
晚点LatePost报道,行业巨头之一新东方计划到年底裁员超过4万人,截至9月中旬完成不到1万人。高途创始人陈向东在7月30日的内部信中确认裁员方案,据媒体计算,涉及近万名员工,相当于企业人数的三分之一。
紧张的气氛从各处透出来,几乎没人顾得上对取消福利提出异议,“公司需要压缩成本,可以理解”。
值得在意的是绩效考核标准的变动,直接关系着工资。对李凡等辅导老师,最关键的考核指标是续报率。续报率越高,意味着公司用同样的获客成本留住了更多老用户,也意味着辅导老师们要用更多时间和方法说服家长。
续报率目标被提高了。李凡记得年初的要求是班级的30%左右,新目标却定到40%甚至45%。她觉得不合理,“以前都不一定能达到的,现在怎么做到?”大多数家长听说了“双减”政策要求不得面向学前儿童进行线上培训,也见了许多教培企业无力支撑、跑路破产的消息,不愿轻易续报。
拨给家长的电话里,没等李凡说完,对面就挂了。她必须得重新拨回去,耐心、礼貌,再说一遍。公司对沟通电话的标准也变得更细,一次沟通需要覆盖十几个要点,总结学情、指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等,如果漏了,就算沟通不成功。第二天,电话又会打给同一个家长。
李凡不敢松懈,同事的电话也从上班打到下班。绩效方案改了好几版,目标总在前面吊着。有一次,她刷后台,目标完成率已经达到了80%,第二天再刷新,数值又落回了60%。工作人员回复她的疑问说,最终的要求还没有确定。达不到要求,绩效就被大幅调低,同样的工作强度,有人对比,工资却少了近1/3。
从第一批大裁员中“幸存”下来的人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一位留下来的员工觉得,处罚机制变得更严苛。公司针对各类工作失误设置了“红黄线”,触碰了红线的员工不仅要被扣大量绩效还可能被开除,拿不到任何补偿。
根据她的过往印象,员工轻易不会受“红黄线”处罚,但这段时间情形不同。打开邮件,常看到数十例通报,原因是“工作态度消极”之类,但并没有说明具体理由。她提醒自己,千万小心。
熬到现在,谁也不愿以“淘汰”或“优化”的方式离开。人人自危下,一名教培行业从业者在公司待的时间变得更长。
九点上班,同事们大多提早一个小时到,企业微信24小时在线,随时待命,争取加班机会。领导敲打她,“公司留下你,是看重工作能力”,她希望证明自己,把工作计划排满了周末。
起初留下来的庆幸很快在煎熬中磨灭了。李凡和大多数同事已经对公司转型不抱什么希望,只剩下一个念头,“要裁就裁吧,不要折磨我们”。这是她能想到最好的结果了,拿到补偿金成了最后一个坚持的理由。
离职者:一份通知,全职待遇成了兼职
到裁员时,能否给出合理的“N+1”补偿被作为评价公司最重要的标准,许多人称其为“最后一份体面”。拿到补偿的人稍感安慰,有人在社交平台晒出转账截图,感谢公司,告别伙伴。
也有人为此与公司陷入了焦头烂额的争执中。
在教培行业工作近两年,王容格见过公司蓬勃发展的样子,她珍惜这份工作带来的收获,想着做好分内的事情,直到公司不需要自己的那天——各负其责,体面再见。
她没能如愿。一份突然下发的通知要求,她所在的组别换签合同,转签为非全日制合同,即以小时作为工作时间单位确定劳动关系。通知中说明,“教培行业形势严峻,像新某方、学某思等教培机构的全职老师都已经进行了换签”,“由原来的‘底薪+课时费’的模式变成‘无底薪+高课时费’的模式”。同事解释,就是把全职老师转为兼职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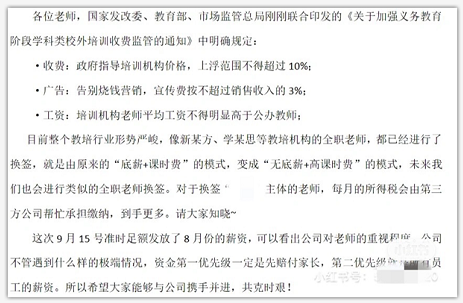
一名教培企业员工收到通知,公司要求其转为“无底薪+高课时费”模式
公司群里,人事工作人员不断催促老师们接受换签。王容格不放心,上网查询发现转签后明显不同的是,“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且“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位曾在教培机构被拖欠工资的朋友提醒她,就算到了维权时,兼职也是相对弱势的一群人。
“N+1”成了泡影。“对公司心灰意冷”,她觉得这是公司为了节省赔偿成本、变相逼退员工的手段,如果无法接受转签,选择辞职,公司不用支付赔偿。通知公布后,一些同事不愿继续“耗着”,已经离开。但即便接受转签,课时费成为全部收入来源,公司业务很难承载所有老师,不一定能排上课,收入变少,到“终止用工”时,依旧没有补偿。
愤怒过后是焦虑,一名被要求转签的辅导老师觉得自己似乎并没有什么选择。她原本计划一边上班一边备考,撑到十月底。她需要收入,也禁不起重新找工作的折腾,眼下这个变动,打乱了原本的安排,辗转到凌晨两点,她也没能想出好办法。
许多员工无法接受这一转签方案。在社交平台上,多家教培企业员工透露被通知相似的转签要求,正尝试表达诉求,争取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一些员工甚至没有协商“N+1”的机会。在地方某小型培训机构任职的一名老师经历了“闪电裁员”,前天上班时还没察觉到异样,第二天就被突然通知要“走人”,从接到通知到离开公司,还不到两个小时。
谈及补偿,公司态度强硬,并不愿意承担。她尝试沟通,电话被拉黑,工作群也被移除,能证实裁员的只剩口头通知。去询问仲裁解决的可能性,对方告知她,可能要排期至明年初,“听到心都凉了”。
有人在评论中提供经验,“保存好打卡记录,别怕麻烦”。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关于教培行业仲裁的求助帖增加了不少,一名求助者感叹,“没想到走到了这一步”。
转行者:“不好意思,不要教培行业出来的”
无论以何种方式离开教培行业的人们,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寻找新工作。
特殊形势下,求职的难度被陡然拔高。有人“出身”大厂教研,被裁员一个月后仍旧在海投简历,在无数次的拒绝中意识到光环不再。失意的教培人聚集在“离职、上岸交流”话题下,一个月、两个月,失业时间不断拉长,满是对自己的怀疑和丧气。偶尔有人成功“上岸”,回复中很快有人“蹭蹭福气”或者“求经验”。

在教培行业“离职、上岸日记”中,许多人讲述求职受挫的经历。
“大家都在问出路,大家也都没出路”。教培行业在过去几年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待遇丰厚、福利诱人。
张方毕业后到教育公司做辅导老师,发现工资比同学高出约1/3,同学都想挤进在线教育公司,学什么专业的都有,觉得“太有钱了”。她看着公司迅速膨胀起来,工作群越来越多,听说“一年能进一万名辅导老师”,感叹:“多恐怖的速度”。踏出校门的年轻人相信,自己踩上了风口。
这些人如今又被迅速甩开。李凡所在的公司分部员工超过1500名,大半是辅导老师,也是重新求职时觉得最艰难的那批人。
他们拿过高薪,“努努力就能上万元”,但教培经历在别的行业却价值不高。
李凡盘算过往的经历,运营、销售,都懂一些,也都不算深入,似乎也没有专长的技能,转去别的行业,实际经验没有,人力成本又高于应届生。
大多数人都接受了降薪求职的现实。被裁员后,李凡把薪资预期调低再调低,按“零经验”寻找工作机会。她不敢休息,“教培行业出来了那么多人,竞争压力太大”,而过程比想象中更难。
复试时,经理没等她说话,直说认为教培机构的辅导老师沟通能力不行,工资溢价过高。李凡像是挨了场训,准备好的介绍没能用上,甚至没来得及表达“从零开始”的想法。工作人员跟她解释,最近来面试的,十个有六个都是教培行业出来的,可能有些负面印象。
有人投简历时发现,一些岗位直接回复,“暂时不要教培行业出来的”。有同行觉得愤怒,李凡安慰自己,“虽然扎心,总比白跑一趟好一些”。
转行不易,但大多数人仍然选择离开培训机构。张方一毕业就入了这行,已经干了三年多。被教培企业裁员后,有朋友内推了一个大厂的教育岗位,面试到了第三关,她决定放弃,“我怕又被裁了”。行业动荡,她反问,“何必去了再被裁一次呢?”
家人的催促越来越紧。离开家乡到北京闯荡,工作是她和这座大城市唯一的联系,留给她缓冲的时间并不多。求职碰了几次壁,她只能回到老家。
生活一下就变了。她还没做好准备,再去找工作,提起“五险一金”,一些公司甚至觉得是个过分的要求,她又问了许多家,得到了相同的答复。“算了,先干着吧”,她安慰自己,上班时,同事们习惯了慢节奏,一个简单的问题讨论两个小时,她怕自己颓废,又迷茫不知道如何改变。
每天工作手机不敢离身的那段时间,如今回忆起来变得遥远。回到老家,很快有人催着生孩子,她以“收入不稳定”的理由拒绝,又觉得撑不了太久。她原本商量,趁着年轻,再在外发展两年,花了大力气说服了家人。被裁员前,她刚来到一家公司,打算挑战新岗位,她有信心干好,再过两年,体面地回家。
那道裁员通知成了潦草的结尾。她偶尔还会想起在教培机构工作的那段时间,劝慰自己:“付出了也有回报了,不必觉得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