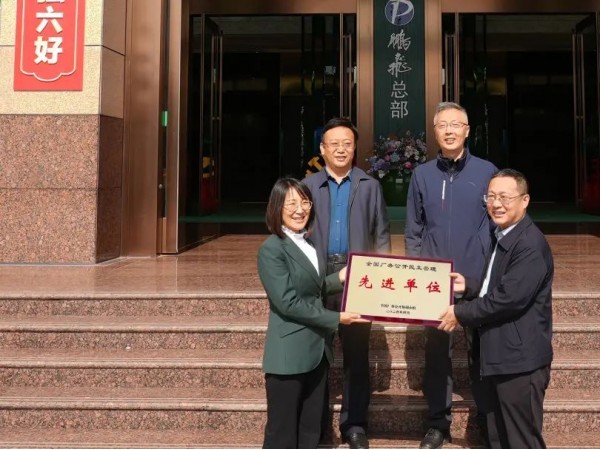《跨越财富鸿沟》一书篇幅虽然不大,但立意深远、主题清晰、观点鲜明、饱含激情。贯穿全书的是两个关键词、一个中心思想。一个关键词是“财富鸿沟”,另一个是“先富阶层”;前者是面临的挑战,后者是对话的对象。围绕两个关键词展开的讨论,指向本书的中心思想:共同富裕,即亿万中国人追求的目标。
先说第一个关键词。财富鸿沟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它既是一项老挑战,也是一项新挑战。
说它“老”,是因为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从原始社会瓦解、私有制产生起,贫富差别就开始出现了。考古发掘揭示,旧石器时代晚期,世界上已出现一些较为豪华的墓葬。进入新石器时代,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赵宝沟遗址(距今7200-6400年左右)表明,先民已存在等级高低之分;大汶口遗址(距今约6500—4500年)显示,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相当明显。孔子推崇西周(距今约3070-2800年)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然而,西周时期的贫富分化相当严重,大小墓葬差异巨大。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他观察到:“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战国时期,“不均”更加严重,“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接下来在秦汉至隋代时期,财富鸿沟依旧,“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出现了一个“豪民”阶层。唐宋时期,贫富分化进一步加速,造成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局面,“富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元明清时期,贫富悬殊远超前代,“贫民不得有寸土,缙绅之家连田以数万计”,令顾炎武感叹道:“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不能敌富者,少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
正是因为历朝历代财富鸿沟巨大,“均贫富”曾是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农民起义时打出的旗号。“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道出了千千万万贫苦农民的心声,因此往往一呼百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本质上也是要改变旧社会的种种严重不平等的状况。
财富鸿沟绝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2017年发表的一项对全球63个考古遗址的研究发现:从1万年前到2000年前,财富基尼系数一直呈上升趋势。比孔子晚一个多世纪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谈到他所了解的那些古希腊城邦,指出它们“定然不是一体,而是二体,一是穷人的国度,一是富人的国度,同住一片空间,却总是互相谋害对方”。有人估计他所在的雅典,财富基尼系数至少达到0.7的水平。罗马共和国后期,财富在统治阶层中大量积累;进入帝国时期,不平等变得极端严重,顶端富豪的收入几乎等于普通人年均收入的150万倍。
黑暗时代的社会崩溃、混乱降低了欧洲不平等程度,但到1347年暴发黑死病的前夜,其整体上又变得极为不平等,据估算,那时巴黎与伦敦的财富基尼系数分别达到0.79和0.76以上。
黑死病过后,财富鸿沟再次迅速扩大。到1427年,佛罗伦萨的财富基尼系数已接近0.85。从中世纪晚期到现代早期,西欧各地的财富基尼系数至少都在0.75以上;某些地方(如德意志的奥格斯堡与英格兰的都市区)该系数高达0.85以上,意味着财富高度集中在极个别家族手中。
1500年到1800年之间,几乎在欧洲所有存在数据的地方,财富基尼系数都呈上升趋势。在内战前的美国南部,基尼系数更高达0.9;美国整体的财富不平等水平在1800年后也一直持续上升,直到二战爆发之前达到巅峰。

1980年-2016年,美国基尼系数逐年上升

财富鸿沟也可以说是一项新挑战。说它“新”,有两层含义。
一是从过往的趋势看,从大萧条后20世纪到70年代中叶,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强大时,不仅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如中国与苏联)的不平等水平相当低,全球各国的财富不平等水平也曾持续下降;然而,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弱化、社会主义阵营式微甚至崩溃,全球各国的财富不平等水平都开始回升,并在过去十余年上升到引起广泛关注与警惕的程度。
在这方面,美国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例子,它的突出特点是,20世纪70年代是个分水岭,之前,其财富不平等水平低于欧洲国家;之后,其财富不平等水平超过欧洲国家。在本书第三章(撕裂的美国)里,作者对美国个案有生动、细致的描述。毋庸讳言,中国的财富不平等水平也有一个由低走高的趋向,序言(站在历史分水岭上)与第一章(财富的欲望)为此提供了详实的数据支撑。
二是从未来发展方向看,“与传统经济发展不同,数字时代的财富创造与集中速度前所未有,”有可能“放大了当前财富分配机制的缺陷,造成更为严峻的贫富分化问题,使各阶层之间的财富鸿沟越来越深。”本书第四章(数字财富鸿沟)对数字财富鸿沟鞭辟入里的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如作者所说,“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领先跑者之一,中国有责任探索规制互联网平台这种新型的经济现象,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方法。这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世界。”
再说第二个关键词。“先富阶层”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提法。
书中谈到占人口总数极小部分的顶层财富精英时,不知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在中国语境,称他们为“先富阶层”或“先富人群”,在国际语境,称他们为“富豪”。在严格意义上,所有富豪都是先富人群,因为大多数人远远落在他们后面。
但是,在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与像印度、巴西这样发展中国家,那里先富人群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先富”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一项对佛罗伦萨社会流动史的研究发现,虽然历经1427年至今的六个世纪,财富继承性和精英职业持久性的证据依然十分显著,意味着“存在着一个保护上层阶级的后代不至于在经济阶梯上跌落的玻璃地板”。
其实,佛罗伦萨并不是特例,意大利其它地区的情况大同小异,美国、英国、法国的情况也差不太多。也就是说,中国人常说的“富不过三代”未必适用于这些国家。久而久之,人们已对高高在上的财富阶层习以为常,不会再将他们视为“先富阶层”,而是直称“富豪”。
中国则不同,革命曾推翻了一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财富阶层。在人民共和国的头三四十年,不管是收入基尼系数还是财富基尼系数水平都很低。那时,社会相当平等,不存在一个与众不同的财富阶层。过去三十年多年,收入差距逐步拉开,一些人的腰包率先鼓了起来;日积月累,增量的差异变为存量的差异,财富差距逐步扩大。
不过,毕竟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形只存续了一代人的时间,大家都很清楚,现在中国的财富阶层还只是一个“先富”起来的阶层,暂时领先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由于先富起来的时间还不长,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虽然增长很快,但其水平还不算太高。
根据瑞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9》,截至2019年,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在有数据的173个经济体中,排名112,不仅大大低于美国,也大大低于瑞典、丹麦、挪威等以收入差距水平低著称的北欧小国。
除此之外,虽然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在降低,但直到不久之前,流动性水平依然高于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今天中国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几乎没有几个来自大富大贵的家庭。如果财富基尼系数不再大幅攀升,如果社会仍保持较高程度的流动性,如果消除出现社会固化的隐患,先富带后富,后富超先富,中国完全有可能跨越财富鸿沟。
作者担心的是,先富阶层中的不少人正在试图完成从自在到自为转化,希冀将自己的先富地位永久化,并千方百计地为此寻找理据。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200年前,就有这么一个先富阶层试图这么做。那时英国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收入与财富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等,一些人赚得盆满钵满,但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没有改变或变得更加恶劣,人均预期寿命在19世纪上半叶不升反降。

当代英国贫民窟(资料图)
面对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先富阶层需要自己的辩护士。边沁(1748年-1832年)的功利主义应运而生。边沁以所谓功利原理和自利选择原理为理据,为经济自由放任摇旗呐喊,主张除了保护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安全,政府不必做任何干涉。他安慰众人,自由放任的经济将会带来最强的财富创造动力,饼变大了,分配亦将趋于平等,从而使幸福达到最大化。
但那时也有人对先富阶层及其辩护士的所作所为十分警觉。整整两百年前,1821年,在其著名的《为诗辩护》一文中,英国诗人雪莱告诫“提倡功利的人们”,不要同时强化“奢侈与贫困,使之各走极端,像近代英国经济学者之所为”。他所谓“近代英国经济学者”很可能指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鼻祖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
在雪莱看来,斯密与边沁“已经用实例证明了这句话:‘有了的,应该再给他一点;没有的,就连他仅有的一点,也应该夺去’。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使国家在放任与专制两端进退维谷,好比一叶轻舟驶入危岩与怒浪之间。这便是无所顾忌进行算计的恶果。”
此前两年(1819年),雪莱还写过一首小诗,题为《人们的正当所得》,鞭挞“以欺骗讹诈和阴谋诡计强取豪夺的人物”,主张“人们的正当所得,理应归他们拥有”。雪莱出生在一个世代贵族的富有家庭,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却试图用自己的笔,创造一个公平自由的“新世界”。因此,马克思对雪莱赞誉有加,称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除了斯密与边沁,过去两百年,与富豪们站在一起,千方百计安抚他们心灵的理论家大有人在,这些理论也成为中国先富阶层中某些人偏爱的安魂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宣扬“选择的自由”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被人引入中国。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二十年,把社会正义称为“幻象”,极力反对“分配正义”的哈耶克在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加,著作大量出版,掀起了一股“哈耶克热”。即使在欧美国家的大书店,哈耶克的书也不常见;但在那时的中国,连街头书摊上也充斥着他的《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虽然很多人未必读得懂哈耶克的那些生硬的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哈耶克当作自己的精神偶像。
过去十余年,嫌哈耶克还不够右,把哈耶克称作“真正的毒药”“我们最有害的敌人”的安·兰德,在中国的一些圈子里红了起来,其主要著作几乎都被译为了中文。哈耶克虽然排斥公正,但他起码支持有限度的最低保障,以“防止严重的物质匮乏”,以“确保每个人维持生计的某种最低需要”。而在兰德看来,“如果一个人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维持生计,谁必须给他‘安全’,而且为什么必须给?”兰德将自私称作“美德”,其哲学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认为“自私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没钱没势的人则应该为自己的无能感到羞愧与自责。她推崇财富的创造者,痛斥财富的分配者,反对国家推行任何福利政策。

哈耶克与安·兰德
由于兰德的著作通俗易懂,不像哈耶克的著作那么诘屈聱牙,他对各国富豪(如商人出身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前国务卿蒂勒森、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等)更有吸引力,有人还贴心地为他们编辑了一本《为什么商人需要哲学?资本家如何理解安·兰德<阿特拉斯耸耸肩>背后的思想?》,这本书很快也译为了中文。
据说,兰德关于判断财富创造者品质的标准,更是已成为中国先富阶层的共识。对先富阶层中一些人最有吸引力的,恐怕是兰德的一个基本观点:财富创造者创造的财富是他们应得的财富,无须与他人分享;任何人也没有权力和权利要求他们分享。于是,兰德的理论便成为这些人的护身符。
对此,曾长期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香港著名专栏作家林行止也看不下去了,他怒斥:“宣扬这种哲学,在新经济潮流中成功的弄潮儿和官商勾结有道的财主从此有了精神寄托,理直气壮地牟取暴利,并心安理得地享受飞来横财!”
不过我们也应该记得,先富阶层中固然有斯密、边沁、弗里德曼、哈耶克、兰德的拥趸,但并非都是如此。前面提到的雪莱是一个例子,把雪莱称作“天才预言家”的恩格斯是另一个例子,中共早期领导人中还有大量例子,如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这些“富二代”们信仰公平和正义、追求崇高的理想,甚至不惜舍生取义。
他们警示今天中国的先富阶层,一定要明辨是非、区分善恶,再富有也不能忘记自己是无数人“奉献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普通公民与其他普通公民之间有一项不可撤销的共同富裕契约;决不能唯利是图、为富不仁;决不能听任财富鸿沟不断扩大;决不能须臾淡忘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
作为风险投资人,正如沙烨所说:“我自己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大学毕业后,我去美国留学。2001年,我学成归国,又投入到祖国的经济热潮之中。从创业到投资,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十几年里,我目睹了很多身边的造富传奇”。围绕财富创造、财富分配、社会责任,想必沙烨曾与身边那些有钱的朋友有过无数次的交流、讨论、甚至争辩,从而激发他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于是才有这本书。
不同于无病呻吟的舞文弄墨,有感而发的书最有读头,值得向大家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