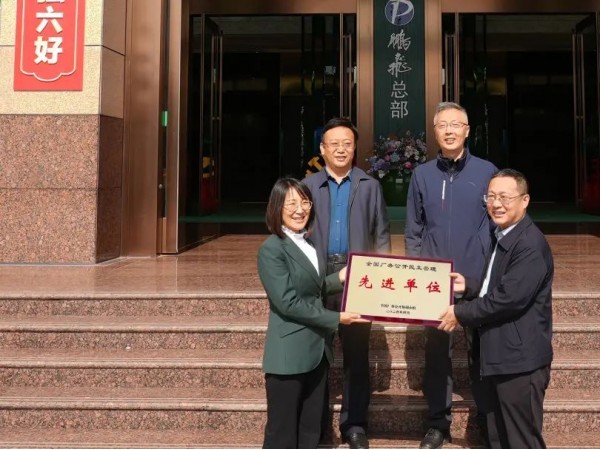8月10日,“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宣布解散。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作为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有48年历史的“教协”是如何从维护教师合法权益一步步走向反中乱港,沦为教育界“毒瘤”的?在反对派阵营中“位高权重”,如今解散,对香港社会又会有哪些影响?
观察者网就这些问题,采访了香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教联会)前会长邓飞。
观察者网:“教协”解散,这消息对你们来说突然吗?之前有没有风声?
邓飞:非常突然,没有风声。这“突然”倒不在于它解散本身,因为随着央媒持续的抨击,再加上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批评,它已是江河日下;这组织解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或以什么方式解散而已。所以10号忽然就冒出来说要解散,有一点意外罢了。
我所说的“突然”,在于严格说来,根据“教协”自己公开的章程,当下的这种解散其实是不符合它自己的章程规定的。按照其自己拟定的章程第20条,它应该要召开会员大会,根据2/3以上会员无记名投票来决定解散与否,而不是由他们的理事会、领导层自己说了算的。
说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好比一家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没开,一个总经理单方面决定公司倒闭,这是很匪夷所思的一件事。现在香港的媒体和社会人士都在关注这事,想知道他们在玩什么,是真解散还是假解散。
这一操作让我错愕——为什么它到最后要解散的时候,仍给教育界和社会大众展示一种负面的榜样作用?他们自己制定的章程,最后都不照章工作,那你还能指望他们会遵守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的相关规定吗?

香港“教协”8月10日突然宣布一致决定解散(图/港媒)
观察者网:对于“教协”,内地很多民众了解不深,大概印象可能仅限于它怂恿包庇“黄师”恣意妄为。您作为教育界业内人士,能否介绍下“教协”作为一个教师工会,其历史上曾主导或参与过哪些事情?
邓飞:“教协”不是一般的社会团体组织,而是注册为教师工会。其创立于1973年,成立之初正好赶上两次教师劳资纠纷,比如老师不同学历对应不同薪水的“同工不同酬”问题,再比如老师怀疑学校管理层在财务上手脚不干净,于是投诉到廉政公署,等等。作为教师工会,“教协”在这两件事上的处理比较成功,最终让政府妥协,确保老师薪水相对公平,就此打响名堂,吸引来一批铁杆。
到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开始讨论回归历程。那时候还不存在什么泛民或反对派,参与创会的会长司徒华当时是乐于拥抱回归的。《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全国人大决定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他属于草委会成员之一。整个1980年代,作为香港最大教师工会的代表,他都保持着跟中央政府合作的态度。
1980年代末,因政治风波,司徒华与中央分道扬镳,可以说大家彻底翻脸掀桌子了。司徒华辞去了草委会的职位,同时“教协”做了几样很重要的工作。
司徒华首先联合多个民间团体一起创办了“反中央政府”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支联会”最初的核心会员都来自“教协”,甚至连财务管理也都由“教协”负责,两者可以说是一体两面。
1991年,港英政府开始搞立法局选举直选,此前就连任教育界议席的司徒华把教育界议席的机会让给“教协”接任会长张文光,自己转战九龙东选区,并凭借在政治风波后暴涨的人气高票当选。换言之,他已经“出圈”了,名气不仅仅局限在教育界。

司徒华(资料图/港媒)
因为这首届立法局选举直选,司徒华还和李柱铭等人成立了“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也就是“香港民主党”的前身,其最核心成员仍出自“教协”,若论组织内部影响力,司徒华超越李柱铭。而在这次选举中,港同盟拿下了绝大部分直选议席。随着后面选举的持续进行,反对派政党开始成形。换言之,“教协”是这些铁杆“反中央政府”的团体组织的核心。
在九七过渡之后,2000年起,香港的教育开启了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包括学制和课程的更改。学制的改革很简单,大学从三年制变成四年制,中学从“5+2”七年制改成跟世界接轨的“3+3”六年制。学制改完后,所有科目课程也必然要改。这个过程中就发生了两件事,不过都跟政治无关。
第一,课程改革对老师的工作量有很大的影响。你想想,如果你已经当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老师,课程习惯到在教室几乎闭着眼都能讲课,现在不行了,要从头再来,那你是不是要烦死?任何改革必然会触动到既得利益,这既得利益未必跟钱有关,而是不想改变自己固有的工作时间、工作习惯、工作量等等。所以,势在必行的教改让相当一部分老师产生了不满、怨恨的情绪。
同时期又发生了另外一件更要命的事——1998年出现的金融风暴对教育界产生了间接的冲击。
香港的教育,无论是官立学校还是资助学校,基本上99%的学校都拿政府资助,而且政府的资助是占压倒性地位的,有的学校经费100%由政府承担。事实上,很长时间里,教育一直在香港政府的所有财政支出中占据最大比例(20%左右)。所有中小学老师的薪水都按公务员的等级发放,而且你每学年即使什么都没干,薪水的等级都能自动向上调一级,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包袱非常大。
金融风暴过后,香港特区政府开始出现了罕见的财政赤字,时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于是提议所有政府部门都必须要节约。教育作为政府财政最大支出,肯定跑不掉,也要想方设法节约用钱。当时教育统筹局的一位官员就将财政压缩与学制、课程改革结合起来——具体做法很简单,用内地的说法,就是将工分折算成一次性补偿,赶紧走人;留下来的人,得接受工作量的改变。
老师们的“奶酪”被动了,“教协”作为一个工会,当然要做这方面的抗争动作,用内地的说法,就是开始维权了。我刚入行当老师的时候,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会收到“教协”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呼吁大家去游行示威。游行示威的由头很多,但是说到底基本上都是跟教改和财政压缩相关。从2000年到2012年,我可以肯定地说,大部分的游行示威都跟教育界相关,而这些游行示威都是“教协”动员起来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教协”的政治-商业模式就开始高度成熟了。
现在很多人说“教协”有很多超市、网店,它通过这些廉价的超市网店来吸收教师当会员,所以它就多了很多支持者。不是的,这个没说到点上。
其实它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财政压缩和教改的过程当中,把教师的饭碗问题、权益问题抓住,作为一个突破口,然后把它无限放大,进行所谓的帮老师维权——我保你的饭碗,维持你所谓的权益。老师对特区政府有怨气,又看到“教协”愿意帮自己维权,自然更多地聚集在“教协”的旗帜之下。
1998年的立法会选举、2004年的立法会选举,等等,在这一连串的立法会选举中,“教协”都借助它所谓的帮老师维权来积攒人气,再把人气转换成立法会的选票,最后拿到议席。这套政治-商业模式就成熟了。
一般人可能觉得教育界在立法会只有一个议席,算啥?不是的,我刚才说过,“教协”不光是在教育界,它在泛民阵营,比如在“民主党”、在“支联会”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力,所以一些反对派议席,尽管不是教育界的,但也都跟“教协”保持统一战线。因此,“教协”在立法会的影响力实际上绝对不仅仅是一票,它可以串联起立法会的多个议席。
在这种情况下,特区政府就只能偏靠那边。因为你要想通过什么政策、进行财政拨款,都必须要立法会先通过,而在立法会里面,“民主党”或“教协”这些是大头,你就不能不跟他们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教协”也就自然而然会要求得到特区政府更多的帮扶,可能有一些咨询架构的委员会、主席等等,就得率先委任“教协”的人或者“教协”同意的人。这些委员会包括课程委员会、考试局的委员会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最后无论是课纲也好,还是考试卷的提供,都有“教协”的影子在里面。
换句话说,在特区官方的帮扶之下,“教协”进一步做大了它的实力。之后,它又继续把这些做大了的实力,投资搞超市等等,更重要的是,它把用所谓教师权益问题积攒人气换取选票以谋得议席的模式运作得更加流畅了。


“教协”解散后,一切会员服务将停止,其中包括超市。(资料图:港媒)
到2012年,事情就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这年出现了所谓“反国教”事件。
“反国教”事件可以说是香港第一次出现这么一种大规模的、极端的、政治上的行动。这时候,“教协”就不仅仅满足于通过所谓的维权来积攒人气、赢取选票这么简单,它进一步政治化了。
本来在意识形态层面,它就只是“反中央政府”,现在则是借助所谓的国民教育问题,更赤裸裸地进行“反中央政府”、反“一国两制”。为“反国教”,它开始动员组织罢课。
2012年的“反国教”还只是围绕香港课程问题,2014年违法“占中”更上一个台阶,就直接跟中央政府叫板了。
反对派的策略是,如果中央不允许民主派等反对派的政改方案,他们就通过“黑暴”活动瘫痪香港。“教协”也深度卷入其中,表面上是组织动员学生去进行一些所谓的教学活动等等,实际上是组织人员到现场参与;而它表达出来的一些立场、宣誓等等,也都配合着违法“占中”进行。
时间来到2019年,就真的上了巅峰了,他们彻底黑色暴力化了。“黑暴”期间,“教协”深度参与其中,对中央的叫板也更加赤裸裸了。
其实,对于“教协”来说,那个时候它也没有其他选择。当整个反对派阵营都走向这种极端化政治行动的时候,它作为一个老牌反对派团体,自然也不能落下。它那时可能也害怕,如果自己吞吞吐吐的,支持得不痛快,很可能就被年轻一代的反对派抛弃了。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参与其中,走到最前头,也因此真真正正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去了,走到了跟中央政府彻底叫板的份上了。
观察者网:内地不少读者对香港的政治光谱不是十分清楚,比如一提起“教协”,他们可能就直接简单地归到“港独”一栏。但就早几年的新闻来看,“教协”也曾跟黄之锋等人公开对峙过。在您看来,“教协”离真正的“港独”是否还有一定的距离?
邓飞:整个反对派阵营的政治光谱也是很广阔的。从意识形态上来看,极端的“港独”或者主张“本土自决”的本土派,以年轻人为主,尤其是大学里的学生会、黄之锋这样的中学团体表现得比较明显。比较传统的反对派,如“民主党”、“教协”这些,它们表面上还是拥护“一国两制”的,表述不支持“港独”,但它们本身对中央政府、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基本上也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也乐于看到现有的社会制度被颠覆,乐于看到颜色革命在香港发生。
在行动上,传统的反对派多是走议会抗争这条线,不像那些新生的“港独”派、“自决”派,跑到大街上搞社运。“教协”也会参加一些社会运动,但暴力程度没“港独”派那么厉害。
观察者网:您是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的副主席,之前采访您时您提到过,你们这个联会和“教协”在香港是两个比较大的教师组织。请问除了立场不一样,在其他方面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邓飞:首先,我们教联会成立于1975年,成立时间比“教协”略晚两年。教联会和“教协”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组成教联会的学校是传统的爱国学校——就是最早升起五星红旗的学校,被称作“红校”或“左校”——再在这基础上去团结其他学校的人。换言之,我们的核心长期都是由跟内地官方关系比较紧密的一些学校组成的。
其次,两者法律基础不同,“教协”是工会,而教联会是一般的社会团体。这个分别就很大了。如果有一个老师觉得自己遭遇校长或校长会的不公正对待,“教协”有权代他出头,而校长(雇主)是不能拒绝见工会的;如果找教联会出头,雇主有权拒绝见教联会,会觉得我没有必要和你讨论这个劳资纠纷问题。
再次,“教协”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立法会有议席,而教联会没有,所以特区政府会朝他们靠拢,我们就只能是尽力去做自己能做的工作,得不到特区政府的特别扶持。
观察者网:作为教师最大工会的“教协”解散了,这对于香港的后续教育工作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邓飞: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影响,可能在情绪上,他们会有一个惯性。虽然大家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但香港是一个很现实的商业社会,它解散了或靠边站了,没过多久就人走茶凉,这是必然的。
更何况,“教协”虽然是最大的教师工会,但不是唯一的工会,还有其他工会存在,只不过以前被边缘化而已。现在包括我们教联会也会另外成立工会,相信还会有新的教育团体和教师工会出现。香港教育界不会因为少了一个“教协”就不转了,相反,还可能转得更快了。

没有了“教协”,香港教育界可能运转更顺畅了。资料图来源:港媒
观察者网:一些港媒开始炒作,称可能由此掀起“工会解散潮”。
邓飞:我觉得不能排除这种情况,不过重点不在于因为它们是工会,而是因为它们往往借工会之名去做一些有违“一国两制”原则的政治行动,这才是致命的。同时,这些工会极可能跟外国的工会有组织联系,甚至有资金上的联系。在香港国安法的规范之下,跟境外势力有勾结,这肯定是不行的。
一些工会可能会因这些原因面临执法部门的调查,工会本身是没问题的。工联会(香港工会联合会)也是工会,就不担心这问题了,对不对?
观察者网:我看到有些“教协”成员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抱怨称“老师和会员的发声空间收缩了”。从《苹果日报》停刊到如今“教协”解散,关于言论自由的悲观论调不绝于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消解?
邓飞:他们从来都是这样吹的——他们从九七之前就说“一国两制”是没有希望的,肯定是骗人的;当九七过渡之后,他们每年都烧《基本法》,每年都说“一国两制”已经死亡,每年都在大街上喊“香港已经没有言论自由了”。我都不知道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是在搞行为艺术吗?既然没有言论自由,那么他们为啥还可以在大街上这样喊呢?这是自相矛盾的。
这也反映了他们内心存在傲慢的情绪,仿佛他们的存在才是自由的存在,他们的消失、倒闭,就是自由的消失与倒闭。这未必太自大了吧?把自己看成自由的化身,这也是让我最难以忍受和恶心的一件事。没了“教协”,其他教育团体多了去了,不是非你不可。
不光是“教协”,很多其他的反对派都是这样的,经常就把自己看成是垄断自由的一个人肉的象征,这个基本上不值一驳。
观察者网:现在香港教育界面临多项改革,除了上次采访聊到的教材、课纲改革,现在组织也有变动,除了这些,您认为教育这领域还有哪些方面在后续改革中要多加注意?
邓飞:现在基本上该改的都已经在动了,无论是课程、考试也好,还是推动国家安全教育、《基本法》教育,这些都在实施过程当中,而不是还停留在打嘴炮阶段。接下来要多注意的,我觉得主要是两方面——
第一,关于教师的职业操守,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无论是师资培训机构、大学进行的一些相关教育,还是进入学校之后,教育局的督学巡查或学校自己的行政管理层对老师教学质量的监督,这些都必须要重视。
第二,虽然说整个选举制度已在完善过程中,但是教育界功能组别依然是存在的。我觉得要把工会维护老师合法权益这块,跟参与政治选举分割开来,不要让“教协”当初那种政治-商业模式再运行下去。
接下来无论是新成立的工会也好,原有的工会也好,我觉得教师的工会应该就只管工会的东西,帮助老师维护合法的权益就得了,不能再把工会的运作跟选举的操作结合起来。这两者之间必须保持一个距离,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做法。否则,就等于重走当年“教协”的旧路,整个香港真真正正的教育问题就一直被所谓的教师权益问题所劫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