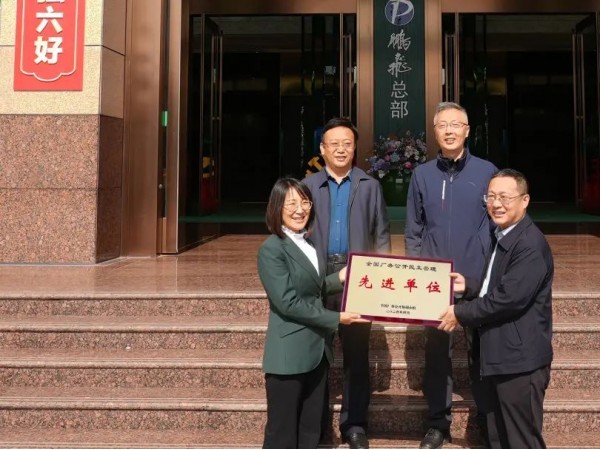01
导论
此次新冠疫情爆发,美国防疫失利,累计死亡人数至 2020 年 12 月已超 30 万,世所共见。有的人归因为美国是联邦制,(1)但很快有人反对这种归因:加拿大与澳大利亚亦为联邦体制,却未见有明显失分,于是又有人归因为美国独特的联邦体制制度框架不利于防疫,这可能有一部分的道理,因为在 1918 年大流感爆发时,当时民主党威尔逊总统主导的防疫也是一团糟,以至于最终死了 67.5 万美国人。此外,从公共医疗的视角看,美国联邦体制决定应对新冠病毒的防疫权限是被各州、各更基层地方和印第安部落的 2000 余个公共健康机构分割与各自享有的,基本不可能实现整齐划一的行动。有学者认为这种公共卫生领域的联邦制化,实际效用其实很有限(overrated)。(2)更有论者认为美国各州之间防疫措施及成效的彼此差距和多元样貌,比欧洲各国之间都要来得更大和更突出。(3)最新的一项研究也指出,现行的美国联邦体制至少在两个方面使疫情状况恶化:一方面,加剧了不平等性,因为有不少州对特定社群的社会福利与保障项目长期投资不足;另一方面,不少在疫情管控方面最吃紧的州却恰恰由于长期奉行低税政策及配套基础设施不够完备而难以有效应对和处理疫情。(4)米歇尔·梅洛(Michelle Mello)等美国医疗政策领域的研究者直言:联邦政府实际做的事情显得太少了(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done toolittle)。(5) 法学界如南希·克瑙尔 (Nancy Knauer) 等学者指出联邦层级的防疫政策缺乏一致性和确定性,是极大的不足。(6)也有的学者认为同为联邦体制,澳大利亚的制度值得美国参考和学习,尤其是设立如澳大利亚各级政府间理事会(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emnts,COAG),澳大利亚卫生保障领域主要官员联席委员会(Australian Health Protection Principal Committee,AHPPC)等常设性政府间论坛,会有助于构建一种合作性的组织框架以应对疫情,并将有助于减少联邦政府在应对疫情时无益的泛政治化(politicization)取向。(7)
但是,笔者认为,美式联邦制并非美国防疫失败的主因,如果联邦层级充分发挥统筹协调诸州的作用,针对疫情形势变化而稳健可靠地因应,也许美国的形势不至于像现在我们所见的这么糟糕。坦率地说,若美联邦政府能和各州一道共担责任(shared responsibilities)、同履使命,美国防疫甚至有可能做得不输于其他联邦政体。(8)当然,此刻其时间窗口早已流逝和关闭,美国疫情失控已成定局。美国政治学者罗斯·贝克(Ross Baker)非常形象地形容了美国联邦体制在此次防疫作战中的进退失据:一方面,联邦政府对疫情缺乏强有力的回应和处置;另一方面,各州行动亦不得充分自由而受到牵制和掣肘。(9) 更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现状就是联邦政府、各州和更基层的地方政府乱成一锅粥,针对公共健康、经济和大众安全等议题各自为战,互斗不休,彼此捉对厮杀。(10)美国政治学者唐纳德·凯特尔(Donald Kettl)教授则指出,美国在面对新冠病毒时,其治理体系无法胜任工作,部分原因是美国在防疫的早期阶段不如其他联邦体系有力,部分原因是在全国范围内各州人民所享受的待遇差异很大。而其治理和应对模式广泛存在的(有时是疯狂的)差异性意味着人民遭受的痛苦超过了他们所需要承受的“剂量”,而且在某些地方,人们遭受的痛苦远比其他地方要多得多。(11)甚至有分析指出,本来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财政联邦制的表现一直优于欧元区,但此次新冠疫情危机下,欧元区联盟的表现却远优于美国的财政联邦制。(12)
的确,有一些事情在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之前就已经长时期地存在,例如,一个价格高昂且效能不彰的医疗保险体系,人民中普遍的对政府行为的不信任感及笃信强者至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思潮,广泛存在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种族因素,中下阶层人民往往开销模式“月光”而并无足量保障性存款以救急(导致大规模的封城无法开展),民粹主义取向的政治极化(13),放任型社会(permissive society)模式(14),占有式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盛行,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当道而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难以形成等,都不能说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才有的新现象。(15) 不过很难否认的是,特朗普的执政加剧、恶化了这些既有的老问题的新延烧。同样的情况是,正如戴维·琼斯(DavidJones)等人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特朗普政府在若干个方面的做法都是在实质上助长了疫情的扩散和蔓延,包括对各州的帮助扶持明显不平等,资金拨款和物资供给到位的大幅度延迟,对于疫情信息发布的信口乱说,导致资讯混乱及全美新冠病毒检测试剂供给量不足等。(16)更让人感到颇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联邦主导的关于全美病床数和确诊病例数的统计汇总的真实性都遭质疑。(17)
在联邦制的防疫效力上,特朗普政府干得也是一塌糊涂,完全不能有效统筹协调各州的防疫进度。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美国的中央和各州政府间关系即已开始走向不协调和趋于紧张,联邦政府对各州领导力不够时,往往导致各州只能选择独自行事。这样的情况到特朗普时代愈加显著,(18)并在此次美国疫情爆发后集中体现出来。一些学者更着重指出,特朗普主导的联邦制在此次防疫中最大的败笔,即是由一部分非常无能的州长率先带头推进政策实施,佐治亚、亚利桑那、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这几个州的州长明明封城时间未够却率先解封,造成防疫破口的恶例,问题一发不可收拾。而这几个州长之所以如此做,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都是共和党人,意在积极响应特朗普的尽速重启经济以抵御疫情压力和冲击的主张。特朗普在联邦统筹防疫方面做的工作本就严重缺失,而在这种严重缺失和不足的工作里,因应 2020 年大选情势,特朗普还将原本应属科学和卫生领域的防疫一事高度“政治化”,和政党政治的操作直接相连,这就进一步导致了美国疫情的失控。(19)公共卫生学者阿希什·贾(Ashish Jha)看得相当清楚,在目前美国联邦制主导的防疫体制下,由于联邦中央欠缺重视和领导力,各州之间步调、措施无法协同,一州在协同防疫方面所做各种努力的有效性最多只能等于它的表现最不尽如人意的邻州。(20)
02
略述美国联邦体制之形势
追溯问题根源,我们可以先来简略看看美国联邦制的基本制度设计。
美国现行的联邦主义体制,联邦政府独享的权力包括铸币、规管各州之间及美国与外国之间商贸、管理邮政系统、组建和维系军队、惩罚造假、对外宣战等。这一部分权力是法律明白宣示和详尽列举的(enumerated powers)。各州所保有的权力(reserved powers)包括批准对宪法的修正案,维持民兵(国民卫队),组建更基层地方性政府,举行选举,规管本州之内商贸(regulateintrastate commerce)和提供公共卫生、公共福利、公共安全等服务。还有一些权力介乎两者之间,这一部分权力叫作联邦与州共行之权(concurrent powers),包括征税、借钱、制定和施行法律、组建法庭、在必要时征用私人财产并给予补偿等。严格来讲,防疫的确主要由各州主导,但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仍有统筹协调规划并给出明确指针性建议之职责,因为疫情随着人员和物资而流动,即于很多时候会发生在各州的彼此交通往来之间。
美式联邦主义的特征,早在民国时期,宪法学者张君劢已经明确说过:“中央各省权限之划分,计有三法。将中央之权列举之,如美是也……依第一法,则中央之事权明确规定,至各省之事权,则以剩余权之意义解释之,即凡不为宪法所禁止者,皆省之权力也。此法也,于划分权限,虽甚简单,然往往剩余权之中,有关系全国利害者,乃各省根据剩余权以抗中央,而动摇及乎全体。”“美以各州权限之不列举,而徒凭剩余权之名义为根据。”“凡不列举者,既属于各邦,各邦之行使此权,大抵专为自己着想,而不为中央计,于是因剩余权问题,而各省与中央,常起冲突。亦有宪法上已有明文规定,双方解释各异,中央曰此中央之权,各州曰此各州之权,因此而发生误会者有之矣。”(21)从学理上讲,美国联邦体制下各州权力不小,下面举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在美国,绝大多数公共政策的推行都发生在政府间交互作用的层级,因为联邦政府往往将政策推行的权力交付到各州民选机构的手上,州政府对政策的实际推行往往有比较大的影响能力。在具体推行时,州政府往往会将联邦政策转化成一种会使州政府受益的模式,他们或者控制规管联邦项目的实际施行,或者通过立法的形式来执行联邦意图,而最终目的皆是操纵控制联邦公共政策,为己增加实际利益。(22)美国政治学者大卫·杜鲁门(David Truman)曾说,美式联邦制的核心要旨即是其创造出了一系列各自独立分散开来的,且能自给自足的,关乎权力、威势和利润的多个中心。(23)但是我们都知道,疫情来如山倒,流窜扩散、多震中爆发且各州联动,在这一情势下,若离开联邦政府的统筹兼顾、宏观调度,各州单兵作战、各自为政,势必很难解决问题。正如美国防疫专家们在总结前阶段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的那样,基于新冠疫情的传播特性,现在远不是强调地方政府的自由权力的适当时机(when epidemiologists warn that a pathogen has pandemic potential, thetime to fly the flag of local freedom is over)。(24)事实上,在疫情早期阶段,由于特朗普政府缺乏有效作为,曾有数州打算结为类似“州际互保”的联盟(尤其以新泽西、康涅狄格和纽约三州为代表),(25)但是实际效果也并不显著。这里又涉及所谓“水平式联邦制”的问题。美国政治研究领域一般将联邦层级与各州层级之间关系称为“垂直式联邦制”(vertical federalism),而将各州彼此之间的范畴领域称为“水平式联邦制”(horizontal federalism)。在美国,“水平式联邦制”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长期以来,各州普遍缺乏足够主观能动性去解决彼此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人们往往最终还是诉诸和依赖于联邦政府的介入去处理和解决那些问题。(26)有的研究认为将公共卫生领域的州际协作框架(interstate partnerships)常态化与组织化,也许是对抗联邦政府缺位的一种有效措施。(27)
其实,在美国建国时代,对于联邦体制的准确定位已有不少相关讨论。比如杰斐逊在一开始时将联邦制定义为一种就州内之治与州外之治间的区隔,后来则渐渐转向将联邦制定义为非常时期与一般时期政府管治目标之不同。在非常时期,政府必然需要更高层级的有效运转,因此也就需要联邦政府对州的内部治理进行一定程度的介入(the intrus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28)疫情爆发固然属于非常时期,且依美国现行体制,在此种时期联邦政府也需调动力量、有所作为。(29)此外,我们需考虑到美国不但是总统制,而且是强总统制,亦即总统手中握有之权力与各总统制国家相较为强,因此,美国联邦体制与强总统制必有一定之关联性。在美国建国时代,处于政治光谱两端的分别是汉密尔顿代表的北方相对较保守派势力(但不蓄奴)和杰斐逊代表的南方相对较自由派势力(但蓄奴),两派都同意联邦制原则,也都同意总统制的设计,但相对而言,杰斐逊派较为强调各州手中之权力,汉密尔顿派较为强调总统握有之权力。美国宪法创立时,杰斐逊正出使法国,汉密尔顿则正主持其事,故美国宪法的基本精神里并未特别强调或突出州权,且给予总统之权算是比较大的,后来 20 世纪里因应各种国际国内形势,总统之权进一步扩展,而联邦中央层级所握之权亦进一步增大。
另外,在美国现行联邦体制下,联邦所拥有的税收资源远远大于各州和各地方政府(stateand local)之总和。在 2008 年时,前者与后者的比例已是 63% 比 37%。(30)在 2018 年,如果以各项政府收入加总(包括税收和社保项目收入等)计算,联邦政府与各州和各地方政府加总后的比例是 64% 比 36%,(31)可见联邦手中资源之多。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各州更为依赖华盛顿给予财力拨款上的支持。目前学者一般将当代美式联邦主义称为“有连带条件的联邦制”(stringsattached federalism),意思即是各州必须推行依联邦所定规则而生成的公共政策,如果各州未能依照联邦指针纲要而行事,将可能失去联邦拨款的支持。(32)此外,正如美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的那样,美国联邦制政治当下的一个特色是行政机构主导的联邦制(executive federalism)的兴起,比如对于政治拨款的主导性影响力就已渐渐从各州与联邦层级的立法机构移转到行政机构。凡此种种,皆可见美国总统对联邦制日常运行所拥有的重大影响力。
事实上,早在 2015 年,就已经有美国学者详细讨论过大规模传染病爆发对联邦体制可能产生的冲击。当时揭示的最主要问题有:一是大部分的州皆无力应对可能导致患者大规模死亡的公共卫生事件;二是在应对处理这些事件时,各州手中实际掌握的财政资源都是远远不足的。(33)2020年的美国新冠疫情发生时,这样的情况亦无大的根本性改善。从原理上讲,当各州因疫情产生财政收入损失时,联邦应介入并予以补贴,但是此次美国实际抗疫中在这方面也做得非常不足够。(34)更遑论有学者预计全美各州加总,在财税收入方面共将面临 1050 亿美元的巨大损失。(35)
03
集权与分权之两歧
如上所述,当特朗普主导的联邦制直面全美防疫时,颇有一战即溃之象,很多的观察者和分析人士都深感极端失望,但同时,他们其实也多所顾忌。
其中一种矛盾心态便是,一方面很多人都希望联邦政府能更有效统筹指导各州抗击疫情的工作,但另一方面基于特朗普荒腔走板的执政记录,他们却也不愿赋予特朗普更大的总统权力。早在 2019 年时,特朗普就曾公开说“作为美国总统,我想干吗就干吗”(I have the right to dowhatever I want as president),并援引美国宪法第二条支持自己的立场。在被弹劾时,特朗普怒称整个弹劾进程都是“虚假的闹剧”(phony hoax),是一场政变(coup),是“不合宪”的;而当弹劾有惊无险顺利避过时,特朗普更富热情地到处宣称他所拥有的巨大总统权力。在 2020年4 月,美国面临严峻防疫形势时,特朗普更公开说作为美国总统,其所拥有的权力是完全的,并声称联邦政府享有绝对权力。特朗普团队中人,尤其是前后任司法部部长,没少为这种所谓的“强总统制理论”摇旗呐喊、保驾护航。特朗普的基本思路就是他手中的权力多多益善,最好能让他无所不能、免受监督,但是有些具体权力,如领导统筹全美的防疫工作,则因相关的责任担当(responsibility)极端重大,一旦做不好可能引发重大政治后果,无法轻描淡写地搪塞敷衍过去,而非他所喜,故干脆推卸和抛开。对于其他责任较小而收益较大的权力,特朗普则是趋之若鹜,一心追求索取。有些学者分析特朗普执政记录,甚至得出结论,认为他在试图将总统职权置于整个美国联邦体制和权力运行架构的核心地位(presidential-federalism)。(36)但问题在于,特朗普以上这些话明显是错误和没有根据的。就连保守派的知名法律学者、以支持强总统制著称的加州伯克利大学柳约翰(John Yoo)教授都认为特朗普说的话大有问题。他承认总统的确有权参与形塑公共意见和施压州长向联邦政策靠拢,但是,在国内事务上总统权力实际有许多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只限于宪法所定的受限制的和确切宣明的部分,并无权规管公共卫生或全美所有事务。各州公共卫生事务之权在各州州长,各州对其境内发生的大小各项事务皆有监管巡查之权。总统在这些事务上真正能做的,更多地只能是一种劝说(persuasion)而非指令(command),比如以联邦抗疫资源的调配相招徕,或使用公共舆论平台发出总统的意见以影响大众看法等。也就是说,特朗普讲的“完全的权力”从本质上讲是根本不存在的。(37)有些论者认为疫情中联邦政府表现差劲,而各州及地方政府则表现相对较好,因此反而是仰赖于联邦制,美国才不至于全盘皆输。(38)这种看法也许夸大其词,但核心正是担忧若给特朗普更多权力,只会导致局面更坏。从理论上讲,如果联邦政府勇于任事,且重视防疫,于此疫情爆发之时适当向中央协调统筹机构更多赋权,然而特朗普领导下的联邦政府恰好是轻忽、回避疫情,顾左右而言他的那种情况,这就自然而然会让人倍感踌躇和疑虑。
政客新闻网(Politico),则观察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新冠病毒全美大爆发之后,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将应对的权力和责任都下推到各州层级政府,以示自身并不需对疫情大爆发的后果直接负责,而各州一方面从特朗普那里得到更多的权力,另一方面却仍得不到足够的联邦层面的防疫技术和工具支持。如此情况下,有的州长(如科罗拉多州和马萨诸塞州)就干脆绕过联邦政府,直接向中国采购防疫材料。此外,人们也注意到,当纽约疫情大爆发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开启了互相“甩锅”模式,特朗普说民主党先前主导的弹劾客观上导致他在应对疫情方面分身乏术,又认为情况恶化主要是由民主党籍的纽约州与新泽西州州长防疫工作太晚起步而造成,但纽约州长则直指联邦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支持、援助和相关指引,才是问题延烧的罪魁祸首。当有人提出是否要全国封关防疫时,特朗普也说交由各州层级自行决定,不会在联邦层级进行全国性封关。特朗普还表示现在各州州长与其动辄叫联邦援助,不如先全面清查州内现有资源(尤其是私人医疗体系手中掌握的资源),然后再合理统一调配,来得更实在有效。许多评论者都认为特朗普是在拒绝执行领导整个国家的任务,也许,在此可以为特朗普稍微辩护一下,因为我们回看当年特朗普选战时的口号,的确有一条是这么说的:他上任后,将减弱联邦政府扮演的角色,并让地方政府有更多发挥的空间。(39)总体而言,就美国民众观感来说,2020 年 3 月底的一项民调(monmouthpoll)告诉我们,大约 50% 的受访民众认为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表现优良,而有 72% 的受访民众认为其所在州州长防疫工作做得好,相较而言,还是各州州长占上风。(40) 同年 7 月的一项民调显示 70% 左右受访者认为其所在州州长的防疫工作做得比特朗普好。(41) 同年 12 月的一项民调显示51% 的受访者认为其所在州州长传达了清晰的防疫计划路线图,46% 的受访者认为候任总统拜登做到了此点,而只有 33% 的受访者认为现任总统特朗普做到了此点。(42)但我们也需要明白,即使在美国的联邦制制度框架下,州层级的政治实力归根结底也仍是比较有限的,且普遍而言,各州都需要平衡其预算,因此州层级很难运用赤字性开支(deficit spending)去纾困救市,各州亦无联邦储备系统那种开机大量印美钞的权力。
美国学者格雷格·高兹豪瑟(Greg Goelzhauser)等人归纳分析美国联邦制度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时,将其总结为:极化的和(联邦政府对各州的)惩罚性的政府间关系结构(polarizedand punitive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43)美国学者乔纳森·菲斯克(Jonathan Fisk)等人的研究则称特朗普领导的联邦体制在疫情面前表现皆系“交易性质”的,总统与各州州长间、各州州长彼此之间的行为模式都由交易的目的来主导,显示出一种“交易型的联邦体制”(transactionalfederalism)的特征。(44) 这显然是不尽如人意的。若按哈佛大学丹尼尔·艾伦(Danielle Allen)等学者的看法,应对疫情理想状态的美国联邦体制应同时将集权与分权两股态势并进处理,使两种态势各司其职且相互配合,而不是非黑即白,硬要在两股态势间择其一而弃另一。(45)
可以预见的是,此次疫情之后,特朗普与美国联邦主义政治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势将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乔治梅森大学伊利亚·索敏(Ilya Somin)教授早在 2019 年就已敏锐地观察到,在特朗普时代,越来越多的左翼进步主义者开始对联邦主义原则心存好感,他们寄望于各州层级和地方政府层级能有效制衡来自华盛顿的政令,并对脆弱的少数派势力提供一定的庇护。(46)2020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特朗普时代,美国联邦制的一个特征是各州州长、首席检察官和各州立法机构经常与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相对抗,并致力于减低其影响与冲击的力度(尤其是在健保、气候和教育等领域)。(47)目前有的学者认为疫情过后美国将进一步地方分权化。(48) 从美国现代政治史的角度而言,一般规律是大的危机之后联邦权力会得到进一步扩张,但由于特朗普政权将防疫任务主要交由各州层级执行,这一普遍趋势很可能会被逆转过来。(49)
本来,美国各州层级的党派间斗争就是很激烈的,甚至曾有美国学者指出,在不少州的情况是,州一级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远比联邦国会层级的两党之争来得更为厉害、更为水火不容。(50)随着地方分权化的大规模展开,各州层级的政治极化互搏现象可能愈演愈烈。
04
被高度政治化的联邦防疫体制(51)
从一个层面看,特朗普的防疫不力也许或多或少还和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设计相关,毕竟依照现制,真正关系到特朗普是否能成功连任的就只有那几个“摇摆州”的选情,特朗普只需将海量选战资源不断注入那几个州即可(而且若该“摇摆州”现为民主党人执政,则特朗普更可在需要时“甩锅”给“民主党州长防疫不力”),(52)“红州”基本盘防疫再差、再崩坏最后也会含泪支持共和党,“蓝州”防疫再好、再健全也不会把票投给特朗普。选举人团制度作为一种绩效考核体系,阴差阳错反而给了特朗普不少活动空间和余地。(53)但实际上,一国之内的防疫必是联动的,岂有可能有哪一州真能苟全于乱世而独善其身。因此,似乎可以说新冠疫情爆发在大选之年,冥冥之中注定二者必有一番纠葛。因为疫情防控工作在美国政治体制下必然要和各州扯上关系,所以连带着会更加凸显选举人团制度下“摇摆州”所扮演的左右全局走向的关键角色。
很有意思的是,从一个侧面看,特朗普似乎并未完全把握住“摇摆州”的机会,比如人口大州佛罗里达,共和党州长执政,又是特朗普海湖庄园所在地,却沦为疫情重灾区,又如亚利桑那(54),亦是共和党州长执政,而一跃成为疫情重灾区。因为客观上疫情的态势是否严峻左右了各州经济能否顺利重启并持续运转,因此这些共和党执政的“摇摆州”的重大防疫失利不仅会有疫情上的冲击,(55)而且会产生经济上的连带效应,(56) 并最终影响到整场大选的走向。汇总选后数据可见,虽然特朗普成功守住佛罗里达、俄亥俄这两个由共和党州长执政的“摇摆州”,但疫情的恶化明显让他失掉了佐治亚和亚利桑那等同样由共和党州长执政的“摇摆州”。若特朗普能更多投入资源将佐治亚、亚利桑那等共和党执政州的疫情控制住,他和拜登之间的差距将会缩小(尽管仍不一定能赢),而特朗普基本放弃了这些机会。而早在选举进行时,美国媒体已注意到疫情正在那些关键的“摇摆州”里肆虐和升温。(57)笔者进一步分析原因,发现各“摇摆州”内,若一州为“红营”州长执政,11 月大选时确诊病例排名低于或持平该州人口排名,则该州较可能“翻红”,如俄亥俄、佛罗里达;若一州为“红营”州长执政,11 月大选时确诊病例排名高于该州人口排名,则该州较有可能“翻蓝”,如佐治亚、亚利桑那。由是可见,特朗普轻忽疫情的态度最后也确实伤及自身。
于是另一个问题就是:特朗普是如何守住俄亥俄与佛罗里达的,又是如何抢到“蓝营”州长执政的“摇摆州”北卡罗来纳的呢?一个原因可能是与州长防疫的相对表现相关,如北卡罗来纳的情况就是一州为“蓝营”州长执政,11 月大选时确诊病例排名高于该州人口排名,是以该州“翻红”(“蓝营”州长抗疫无成)。但很明显,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特朗普将疫情的政治化操作(即国内可怪政治对手民主党,国外可责难中国)。
选前笔者已预估,如果特朗普在疫情问题上无法挽回,那么他很可能将狂打“中国牌”来试图对其选情进行急救。而且我们还要看到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即“摇摆州”的防疫失守、疫情蔓延,可能反而会让特朗普在这些州内更加方便地将“中国牌”和疫情关联起来,进而得分。因为近年来美国各项选举一再告诉我们,有时选民并不追随理智,而是诉诸情绪和激情的发泄。有可能出人意料之外,防疫失败反而正好给特朗普以怪罪、归因于中国的借口。从选后汇总的实际情况看,特朗普确实这样做了,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只是通过这样做的得分不如防疫失败的失分多,因此总体来看无法弥补缺口罢了。具体而言,特朗普能守住佛罗里达,在不小的程度上即是拜此种群众心理的机制所赐。
特朗普作为一个擅长操纵话术的总统,巧舌如簧,指鹿为马,功夫深厚,在近期防疫问题上更是展现无遗:当美国被测定为新冠感染者人数大幅爬升时,特朗普说就是因为检测做得太多太好了,才有这么多人被确定为感染;当全美确诊者人数飙升而死亡患者数并未在短期内剧烈上升时,特朗普说美国确诊患者中的死亡率天下最低;世人有目共睹,美国明显防疫失败,形成令人瞠目结舌的多震中的疫情结构,特朗普却硬是要说美国防疫是全世界做得最杰出的之一。此类话术的效果,在中间选民那里也许买单的人并不多,但在特朗普的核心拥趸中则毋宁说是典型的谎言重复一千遍,自然就成为真理。在特朗普与各州关系上同样也是如此:一旦有了成绩,全归于自己领导有方;一旦出现失误,则是州长们的失职。作为超级大国的领袖,这实在可说是一种德不配位。
总体而言,上述高度政治化的操作是远水难解近渴,或者说是杯水车薪,虽亦在局部略有所得,终究抵不过防疫全盘失败造成美国选民普遍印象上的所失。
05
结论
笔者还想略谈一下学界关于不同国家的联邦体制在防疫上的表现的相关研究。马克·罗泽尔(Mark Rozell)等人比较了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美国这四个联邦体制国家对疫情的反应,认为其中三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德国)在危机中表现良好,行动迅速,进行了广泛的病毒检测和接触者追踪,并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了一套相对统一的政策。相比之下,美国的反应则是灾难性的,在病毒爆发之初就浪费了数月时间,其病毒检测工作开展有限,各级政府间合作不力,各州间,甚至在某些州,连一州之内的政策差异都显得很大。而特朗普需要对美国的防疫失败负重大责任。(58)奥古斯丁·吉罗迪(Agustina Giraudy)等人对墨西哥、巴西和美国等不同联邦体制应对新冠疫情的情况做了比较研究,他们认为似乎非总统制的联邦体制国家在应对疫情时表现尚佳。(59)尽管不同学者研究侧重点不同,但大家不约而同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地位对美国联邦防疫体制造成的影响和冲击。
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能说联邦制度是美国防疫失败的本质原因。但美国的防疫因其联邦体制的固有设计,必然需要一个有能力、有威信,且愿意担责任、尊重科学专业意见、做事顾及后果和影响的联邦政府,统筹、兼顾、协调并强力支持各州防疫以齐头并进,而当这样一个角色明显缺失或不作为时,美国的联邦体制可能正好反过来会对疫情的持续延烧产生某种“助燃”的效应。而当防疫逐渐混合政治极化现象,并联系到 2020 年 11 月的总统大选时,这种“助燃”可能更甚,舆论的口水战变成大幕的中心,真正的问题端倪则被隐埋。一般在学界看来,美式联邦体制的好处包括使各州的法律与制度较具灵活性,有助于实现更为规范的财政纪律(60)等;坏处包括增加了复杂性与使人困惑的特点,使政府公共服务在不同地区间有不平等性,使统筹工作难以展开,有时使政府的资源重复投入产生浪费,但是相关的监控把关机制却非常薄弱,使不同行政区之间在管治上可能产生冲突等。(61)结合新冠疫情在美国的爆发,我们可以说,一个不称职的美国总统足以遏制美式联邦体制的既有优点,并极大化美式联邦体制的传统性缺点。明乎此,则问题的本质原因似乎并不直接在于联邦体制本身,而是联邦政府理应扮演的领导者角色的极度缺位。联邦制未必一定与防疫的科学逻辑相悖,但一个中央政府不愿高度负责且希求通过政治化途径应对和处理疫情的联邦体制,对疫情的防范与化解很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一国依据其历史、民俗与传统,自有不同之制度脉络,联邦制(尤其是大邦与小邦间之调和)确为美国作为由英属殖民地派生的国家自建国时代起之典范(paradigm)。联系到我国实际情况和历史传统,(62)众所周知,早在民国时代的联省制辩论中,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现实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包括美国体制在内的各种联邦制度在中国土壤上的适用性。而通过此文之分析,我们应可看到,即便是在以强调地方权力而著称的美国联邦制里,中央仍需有一定统筹规划之权,且必得负起协调诸方之责,方得统御全局应对如新冠疫情一类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当联邦政府缺位或不作为时,仅凭地方一域之力,难以真正有效遏制态势、稳定局面和摆脱问题。在公共政策领域,制度固然关键,但人的因素也同样极端重要,所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即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