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这个人间奇迹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为了让全世界不同文明、不同信仰的人民也能一听就懂、理解透这个精彩故事,不能只用中国大陆人民所熟悉的叙事语言讲述,还需要通过更加世界性的叙述方式对这个故事进行多角度的解释。本文就是这样一个尝试。
时政评论员
两会召开前夕的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以隆重的仪式对脱贫攻坚进行总结表彰。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两会开幕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重提:过去的一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中国政府“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关于中国扶贫这个事业,中国自己这方面是这样叙述的: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帮助那么多人摆脱贫困。
世界银行2008年确定的贫困标准是每人每天1.25美元。2010年,中国政府制定了每人每年2300元的新贫困线。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这一价格相当于国际上每人每天2.3美元,已超过世界银行当时执行的1.25美元贫困标准,也超过联合国每人每天1.9美元的标准。
2012年至2020年,中国开展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中国实际执行的最低贫困标准从每人每年收入2625元提升至4000元,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不仅如此,中国提出的脱贫目标任务,除了从数字上衡量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变化,还强调多维度提升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稳定实现吃不愁,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安全住房有保障。
这的确是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够得上“伟大光荣”之称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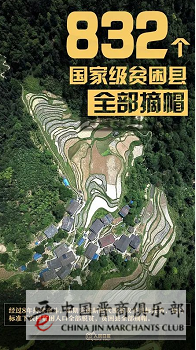
但还要看到,这个人间奇迹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为了让全世界不同文明、不同信仰的人民也能一听就懂、理解透这个精彩故事,不能只用中国大陆人民所熟悉的叙事语言讲述,还需要通过更加世界性的叙述方式对这个故事进行多角度的解释。
本文就是这样一个尝试。
1. 放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上看,验证“三级解绑”理论
中国数亿人口的脱贫、数亿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在现代化这个进程中顺势实现的。中国政府通过大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经济发展,带动了整个扶贫事业,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么,这个近代以来发生的现代化进程,到底是如何为相当于一个大洲规模的贫困人口创造了摆脱贫困的机遇和条件的呢?
关于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宏观理论,是由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的国际经济学教授理查德E.鲍德温在他2016年的《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的全球化》(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一书中创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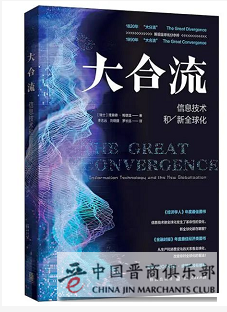
理查德E.鲍德温在《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的全球化》一书中提出“三级解绑”理论
这个被称为“三级解绑”的理论,为理解近代以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这样一个理解框架:
人类交往活动受到三种成本的约束:交通运输成本、思想交流成本和人体本身流动的成本。在历史进程中,三种约束条件渐次放松。
1820年以前,由于三种成本都极高,人们基本上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共同体内,大多数人的生产和消费都被捆绑在同一地点;1820年之后,由于蒸汽机、蒸汽船以及铁路的技术创新,交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出现了生产和消费的第一次“解绑”分离(Unbundling),但思想连贯交流的成本和人本身流动的成本仍然很高,电报和固定电话的发明还是不能把思想交流的成本真正降下来。这次“解绑”直接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大分流”的发生,即工业生产集中在了率先从交通运输成本降低中获益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使它们迅速拉开了与其他欠发达国家的差距。
1990年代之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革命带来的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成本。信息技术的发展遵循摩尔定律,即计算能力呈现指数增长,芯片的性能每十八个月就会翻倍。而吉尔德定律则表明,带宽的增长速度要比运算能力的增长快三倍,即每六个月就会翻倍。梅特卡夫定律进一步指出,一个局域网对用户的效用和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由于第二种约束条件(思想交流成本)被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放松,全球范围的生产协调成为可能,生产和消费的第二次“松绑”带来了与“大分流”方向相反的“大合流”(The Great Convergence)和一次新的全球化。
但是,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虽然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成本,却还是未能放松第三种约束,即人本身流动的成本。可喜的是,第三次“松绑”已经初显端倪,即降低人本身流动的成本的技术已出现,只是目前还十分昂贵。遥控机器人(telerobotics)和远端现身(telepresence)技术将实现劳动者和劳动服务的地点上的分离。鲍德温认为,“三级解绑”完全实现之后,一种大合流的全球化就可以惠及所有国家。
鲍德温教授创造出这个理论,主要是为了解释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不平衡,应用这个理论,他解释了西方发达国家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贫富差距的经济-技术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第二次“解绑”发生后,只有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多数国家还是没有实现追赶,有些国家甚至距离更大了。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种理论多少有点“技术决定论”的偏向,还带有曲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历史的误导,不能当作关于近现代世界历史的主流理论。但如果只作为一种中性的分析工具,这个“三级解绑”的理论框架其实还是很有用的,尤其在解释贫富差距的形成和分布,以及政府的扶贫事业方面。

2021年春运热门迁入地,截自百度地图
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一国,即可将中国在全面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前的大部分农业经济地区,理解为“三级解绑”实现之前的状态,好像是1820年之前的世界。由于交通运输成本、思想交流成本和人本身流动的成本这三大成本每一个都极高,人们的生产和消费都被紧紧束缚在同一个狭小空间内,经济发展停滞,人们长期处在贫困状态。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后,部分地区率先实现了交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的第一次“解绑”,大中城市、部分通衢辐辏之地和沿海通商口岸的居民都开始享受到遥远地方生产的价廉质优商品,于是,就像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一样,中国一国之内也形成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大分流”,贫富的地区分布格局很快形成。
从理论上讲,一国政府的扶贫事业从“大分流”发生之后即应及时启动,以免贫富差距在一国内地区之间形成固化,积重难返。但在现实中,一个按计划、分阶段、统筹协调推进的扶贫事业,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心有余而力不足,进行起来非常困难。因为这个事业的推进,所要求的前提条件非常多——没有完全独立的主权不行,没有外部和平环境不行,没有国内政治稳定不行,没有适宜的社会制度不行,没有经济和财政基础不行,没有决心和意志也不行。
所以,中国的扶贫事业,从长程历史观察来讲,是中共从新中国建立之前就开始的,因为创造完全独立的国家主权、和平环境、保持政治稳定、改革土地制度等与扶贫事业直接相关的大事业,都是建国之前中共作为解放中国人民的大目标,就已经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和财政基础日益雄厚,中国共产党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初心,解决本国人民贫困问题的决心和意志也日益坚定。以1982年国家启动“三西”(甘肃定西、河西,宁夏西海固)专项扶贫计划为标志,中国特色的开发式扶贫拉开了序幕。1986年中国成立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开始实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国家扶贫行动。1994年以后,国家先后颁布实施“八七扶贫计划”和两个为期十年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两次提高扶贫标准,持续推进扶贫开发工作。
应用上述的“三级解绑”理论,中国由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本质上就是依靠国家的力量在一国之内对因第一次“解绑”而自然形成的贫富“大分流”进行一种“逆操作”。
一方面,针对那些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根本不可能实现第一次“解绑”甚至还会继续“紧绑”的地区,投入政府行政资源人为地帮助它们实现第一次“解绑”,首先大力降低交通运输成本;典型的一个体现就是所谓“要想富,先修路”的政策配套。
另一方面,针对那些因为实现了第一次“解绑”而率先发达起来的地区,通过政府行政性安排,将其中的知识、经验、创意等思想资源转移到贫困地区,人为地帮助它们实现第二次“解绑”,大力降低思想交流成本;典型的体现就是所谓“对口支援”、“精准扶贫”和“驻村扶贫工作队”等政策配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意志,投入前所未有的资源,动员前所未有的党员干部,对最后近一亿最难“解绑”脱贫的偏远贫困人口的千年沉疴,发起一场历时8年多的攻坚战。

通过建立脱贫攻坚的责任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动员体系、监督体系、考核体系,系统性地解决了“扶持谁”、“谁来扶”和“怎么扶”的问题。最终在2020年完成了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任务,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进程,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
从“三级解绑”理论上看,在最近这几年的扶贫开发最后攻坚阶段,中国政府实际上是把当代技术条件下能够做到的“解绑”,都尽可能地做到了,包括最为困难的降低人际交流成本这一个“解绑”,也通过各种政策配套和新技术应用尽可能地做到了。中国扶贫事业中大量出现的各领域农业技术专家学者,深入到扶贫工作第一线帮助农民解决各种生产问题,以及驻村扶贫工作队、基层政府部门利用互联网平台帮助农民解决各种市场销售问题,本质上就是在解决单纯依靠市场不可能解决的人际交流成本过高的问题,也就是第三级的“解绑”。
中国扶贫事业的口号是“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既富口袋也富脑袋”,何为“扶志扶智”?何为“富脑袋”?从“三级解绑”理论上看,无非就是中国政府与贫困人群同心协力,共同实现最后阶段的思想交流“解绑”。
2. 放在世界贫富分布格局上看,验证“大象曲线”理论
2月25日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在讲话中说: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特别是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这里所说的“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是指近4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贫困人口总的脱贫情况。
那么,这个总的情况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2013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政策研究报告《全球收入分配:从柏林墙倒塌到大萧条》,作者是两位当时服务于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拉克纳(Christoph Lakner)和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这份报告中,两位作者首次提出了一个被称为“大象曲线”(Elephant Curve)或称“Lakner-Milanovic曲线”的图表(如下),反映全球不同收入人群在1988-2008这20年里差距很大的收入增长发生率。

图表的X轴代表全球收入分布的百分位数,Y轴代表收入的累计增长百分比。大象曲线因其与大象身体的侧面轮廓相似而得名,从该图中可以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1)在截止到2008年的这20年里,从横轴左端开始,类似于大象尾部的10%-15%世界上最贫穷人群,收入累积增长极小,几乎没有从全球化中受益;
2)图表的中间部分,从第15到第50个百分点类似于大象躯干的部分,代表了全球中产阶级,得益于以中国和印度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较高的增长率,收入累积增长了70%至80%;
3)在类似于大象前部向下陡降的部分代表了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即全球的中上阶层,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该阶层的工资在20年里几乎没有增长,甚至还有负增长;
4)从第80到第100百分点类似于翘起的象鼻子的部分,代表全球最富有的人群,20年里收入增长了60%左右,而全球收入最高的1%人口还有更高的收入累积增加。
自2013年“大象曲线”问世以来,已经又出现了许多改编版本,通过不同方法来说明全球收入不平等。有的对部分人群的收入增长数据进行了调整,有的将时间段扩大到了更长的1980年至2016年,但最终的几点主要结论——最富有的那部分人群是全球化带来的收入增长的“赢家”,最贫困的那部分人群被全球化“锁死”在了原来的收入水平上——没有改变。
考虑到从1980年以来的这40年,正是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狂飙突进的40年,那么,“大象曲线”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理论定律:
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运动,必定加大全球收入的两极分化程度,恶化全球的不平等现状;
全球最贫穷的人口不仅不可能通过“新自由主义革命”摆脱贫困,反而会被固定在贫困状况当中,无法获得任何改善。
通过了解这个可以被称为“贫富分化大象曲线”的理论,人们便很容易明白“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这句话的意义了。
一方面,在反映全球收入分布的“大象曲线”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本国扶贫事业中取得的成就,就是将原本处在“大象曲线”左端10%-15%最贫穷的人群,通过持续不断且卓有成效的扶贫工作,整体地向右方进行了平移,使这部分人群大部分进入到了“大象曲线”的中间部分,并使其能够分享全球中产阶级的较高收入增长;
另一方面,在反映中国一国之内收入分布的类似的“大象曲线”中,中国扶贫事业所做的事情,就是将原本处在“大象曲线”左端10%-15%最贫穷的人群,通过持续不断且卓有成效的扶贫工作,整体地进行了向上的提升,使这部分人群大部分与“大象曲线”中间部分逐渐拉平,成为更大的中国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分享其较高的收入增长。
很显然,这在客观上,就是一种针对同时期世界范围“新自由主义革命”所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运动的反向操作。
历史见证,“新自由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地推广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并未在任何一个国家取得真正的成功。在拉丁美洲,实施“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各个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全部低于先前的时代。在东欧,正如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科勒德克教授所总结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在东欧25个国家的实践是完全失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批评“华盛顿共识”时说:“无论新的共识是什么,都不能基于华盛顿共识。”
而这个反映贫富分化程度的“大象曲线”,就是推行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出的一个结果。而就在这同一个时期,中国通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让中国逆势而动,大踏步走出了“大象曲线”的左端,而且在本国国内,彻底改变了“大象曲线”的形状,使这条曲线越来越向中间部分收敛,越来越体现出了共同富裕的特征。
3. 放在发展主义演进路径上看,验证“遭遇发展”理论
事实上,这一点,只有中国这个国家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的。
关于发展中国家崛起这一现象,世界上的分类有多种,一种划分是将因本国快速实现了工业化而崛起的国家分为一类,被称为I6国家,即中国、韩国、印度、印尼、泰国和波兰6国;还有一种划分是只看崛起,不区分凭借工业化还是凭借本国丰富自然资源,被称为R11国家,即I6国家中国、韩国、印度、印尼、泰国和波兰,再加上尼日利亚、澳大利亚、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土耳其5国,共11国。
再有就是传统的分类,在“中心-外围”世界体系理论中将“外围国家”又分为拉美型、非洲型和东亚型三种。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东亚型“外围国家”是一种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了拉美和非洲“依附型国家”地位,获得了自主发展空间的“发展型国家”。

新冠疫情让拉美雪上加霜,图为志愿者在巴西贫民窟消毒
正如德裔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阿尔伯特·赫希曼在他《经济发展的战略》一书中所指出的,由于东亚国家普遍脱胎于反帝战争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得这些国家将自身定位为加快追赶先发国家的后发国家,因此其发展就成为一种人为的、刻意的进程,整个国家可以完全为发展的目标而组织起来,既不是像先发国家那样发展作为一个自发进程,也不是像拉美那样发展作为一种依附状态。
但无论怎样分类,中国还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既不是一个仅通过快速的工业化而崛起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仅通过出售本国自然资源而变得富裕的国家,同时也不是一个仅通过刻意追赶先发国家而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国家。
中国的发展由于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而避免了被哥伦比亚裔美国人类学教授阿图罗·埃斯科瓦尔所说的“遭遇发展”的路径陷阱。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在他1995年出版的《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一书(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中推出了这样一个理论:
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发展,不仅没有使这些国家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反而普遍发生了贫困状况的“现代化”。他在书中写道:
“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当市场经济的扩展割裂了人们与社区之间业已建立的纽带,并且剥夺了千百万人民使用土地、水和其他资源的权利之后,现代意义的大规模贫困才开始出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巩固,系统性的贫困化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
虽然发展主义都以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为目标,但在二战后“三个世界”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随着西方全球霸权的重建,发展逐步蜕变为一种建立在发展主义话语和政策之上的新型殖民主义。一方面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完成了从“该不该发展”的问题到“如何发展”的问题的跨越,通过经济增长解决社会变革问题成为了一个普遍信仰,另一方面却是“现代化”的贫困、“现代化”的落后、“现代化”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大规模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欠发达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就成了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根据经济学家们的计算,鉴于欠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在经济起飞之前约为发达国家的20%-25%,假定发达国家保持年增长率2%的情况下,那么欠发达国家要想在两代人的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增长率就必须在长达至少60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在6%以上。从二战后全球经济发展总的情况来看,这显然是一个极高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进行追赶的这些欠发达国家必须在工业化、城市化、基础设施现代化等各个方面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而且必须持续几十年的“大跃进”式发展。
这不仅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真正的现实还恰恰相反。在二战后发展主义浪潮的冲击之下,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陷入了与追赶方向正好背道而驰的多重恶性循环。最终结果就是今日第三世界的普遍状况: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频发、失业率与犯罪率居高不下、生态失衡加剧、贫富分化严重、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陷入了一种被称为“遭遇发展”的陷阱。
二战后,每个发展中国家都以加快本国发展为总的行动目标,但几十年来五花八门、各显神通的发展,最终大多数国家都落入了不期而遇的“遭遇发展”陷阱;而只有中国,不仅没有跌进这个陷阱,而且正在大踏步地进入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新发展阶段。
通过这个“遭遇发展”理论来反观中国的扶贫事业,很多事情更加一目了然了。

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在中国,截止到2019年年底,全国农村公路里程已达42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100%通硬化路,通客车。十三五期间,农网供电可靠率达99%。截止到2019年,全国行政村通光纤、通4G比例均超过98%,电子商务已实现对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全覆盖。在“互联网+健康扶贫”项目推动下,远程医疗也已经覆盖所有贫困县。
这就叫“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中国的扶贫事业不仅仅是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这一个方面,它实际上是中国全面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的全面发展,则又是更大的奋斗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近100年来的历史上看,对于中国来说,所要为之奋斗的远不止通过高于发达国家的GDP增长,实现国民收入水平的追赶这一个单纯的经济目标,比起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除了经济增长以及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基础设施升级等工程在内的现代化转型等任务之外,中国还要同时完成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彻底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直至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等一系列重大任务。
这就是为什么唯独中国成功避免了落入“遭遇发展”陷阱,并成功跨入新发展阶段的根本原因。
综合上述,从人类近现代历史、世界贫富分布格局中以及近百年世界发展主义演进路径这三个角度进行深入考察,中国的扶贫事业验证了西方的“三级解绑”理论、“贫富分化大象曲线”理论和“遭遇发展”理论,也赋予中国扶贫事业更加深刻的本质和更加重大的世界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再运用通俗、科学、客观中性的语言,向世界不同信仰、不同文明传统的人民进行讲解,应该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