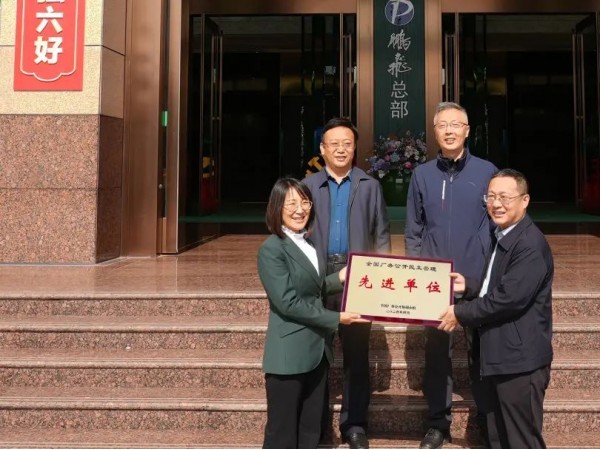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那五十年后呢?
这是回归之前,香港人最大的担忧。但今天来看,在香港国安法的重拳出击之下,中央加强对香港的管制权,将香港纳入国家发展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中,香港的未来,更加清晰。
观察者网专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解读香港当下和未来。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
观察者网:上次见您还是去年12月份,我们聊的是“修例风波”的影响。当时您刚刚去过香港,还看到香港街头运动的痕迹。这之后,您还去过香港吗?
► 田飞龙:其实是有计划去香港的,特别是原定立法会换届选举是在今年的9月6日,所以我是想申请去香港大学做三个月的短期访问学者,希望能够从一个学者的视角近距离、第一现场地去观察、分析、研究香港的政治变迁,但遗憾的是疫情加上香港推迟选举的安排,再次访港的计划就搁置了。
从去年12月到现在大概快有一年时间了,其实还是比较想念香港。原因是2014年我有一年的香港访问学者经历,理解了香港社会的丰富性和它的活力,也理解了“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时代更替,还有它的政治发展当中,遇到了一些比较困难也困扰很多人的议题。但是香港社会自己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没有进行很好的梳理。从管制体系到社会文化,都出现了很多冲突和不适应,特别是与内地之间的磨合,对全球化还有世界体系变革的不理解以及难以有效的适应。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疫情的影响,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最近因为疫情蔓延,香港中小学和幼儿园再次停课。我们也看到,有了SARS的经验,香港这次在一开始非常重视,包括到现在,隔离措施都非常严格,但防控效果和内地相比还是相差很大。从制度的角度分析,原因有哪些?
► 田飞龙:这其实恰恰可以从“一国两制”的角度解释。
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它应对这样一个重大公共疫情的应急机制,和西方是一样的。首先它是一个法治程序,各级管制机构要严格按照条文、按照规则去办事,包括行政长官制定了相应的应急律令,其实是一套标准化的操作流程,没有表现出对超出常规的新冠疫情的重视,也缺乏全社会的教育和动员,所以应对起来就沾染上了和这次欧美社会面对新冠疫情时同样的毛病,始终将疫情当作常规现象去处理,认为可以通过常态的法治程序以及既往一般的应对经验去处理,而对疫情的突发性、长期性以及挑战估计不足。
两相比较之下,内地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突发事件,从社会动员、应急体制以及精细化防控方面,都体现了内地体制的相对优越性。所以恰恰“一国两制”当中“两制”的差异,在防疫成绩表上出现了非常大的差别。
常规的法治高度尊重个人隐私、个人自由,很难配合全社会动员和预警机制,难以有效应对突发危机。在这方面,国家体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我们看疫情经过武汉首次暴发之后,短期内是有一个忙乱、反应迟缓的现象,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出现的正常现象,但很快我们这一套体制完成了疫情研判、动员管制、疫苗研发、经济复产的过程,在最近局部出现疫情反弹后也能够快速检测和控制,这些使得中国经济在下半年以来,在全世界经济体的复产效率和结果上独树一帜,这是香港需要从体制上进行反思和学习的地方。
“一国两制”中,香港政府是弱政府角色,再加上此前“修例风波”中民众对香港政府治理能力和公信力也有了很大的怀疑,对这次应对疫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修例风波”当中,反对派煽动的仇警以及对特区政府管制威信的怀疑,造成了激进主义氛围下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心态,这种心态和一种追求完全自治的政治浪漫主义以及社会层面的“揽炒”主义正好相结合,这实际上对在新冠疫情之下,如何信任和配合政府做好防疫工作,非常自律地去思考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造成了非常大的难题。
对于香港来说,刚刚从“修例风波”中还没有缓过神来,社会心灵也被冲击的七零八落,碎裂化、撕裂化的社会价值体系还未得到修复,又遇到新冠疫情,等于是大病未愈又遭大难,是一个雪上加霜的打击。“修例风波”加上新冠疫情,对香港的管制能力,对香港自治的信心,对香港社会认同和团结所造成的冲击,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复。
而我们也看到其实特区政府在国家的支援之下,特别是香港的爱国爱港力量,能够顾全大局,支持政府抗疫,他们在非常艰难的时刻负责任的行动起来,所以复苏的力量也在露出曙光,在其中隐含着将来还有可能重建的契机和希望。

此次新冠疫情,香港再次经受考验。图片来源:中新社
观察者网:说到复苏,一剂强心剂就是今年颁布的香港国安法了,重新确立了中央对香港问题的主导权。以这部法律为一个节点,您认为对于我们继续推行“一国两制”政策有哪些影响?
► 田飞龙:香港国安法既是意外,又是意料之中。
说它意外,是因为出乎香港本地社会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既往的理解。他们理解的起点是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以及用普通法传统所演绎的香港高度自治的体系,所以他们习惯于将宪法和基本法、“一国两制”对立起来,根本没有做好准备以及非常不愿意接受中央管制权过深圳河在香港落地执法,而香港国安法实现了这样一些制度上的突破,并且是中央主动承担起国家安全立法的中央事权管理的限制性责任,其实是对既往理解的一个重要突破。
但这种突破只是对香港社会以及国际社会惯常理解的突破,并不是对“一国两制”本身的突破,恰恰是“一国两制”本身所包含的价值和制度责任。“两制”的所有自治权都来自于“一国”,来自于主权和制宪权的授权。在这种授权之下,授权者也就是主权者负有理性保障的责任。
但是我们看到,“修例风波”以来,无论是香港立法会还是特区政府,还是香港法院,都没能有效承担起止暴制乱的法治任务,不知道怎么结束这场骚乱,都找不到出路。并且随着基本价值、基本制度还有基本信心的破坏,整个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信誉也在受损,这些都是对“一国两制”底线的挑战,满足的是本土极端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在香港策划颜色革命,颠覆国家主体制度的政治图谋。
在这种情况下,主权者就必须要基于自己对“一国两制”整体制度安全、宪制秩序安全的根本责任,主动立法来保障和引导香港社会回到一个繁荣稳定、重新信守法治、聚焦发展的社会常规理性状态。
所以香港国安法给了这样一个兜底保障,让香港民众更有信心,并且给香港爱国者一个积极的信号,国家与一切爱国者同行,国家的保障力量才是“一国两制”50年不变、行稳致远的最关键的保护性力量,而不是任何其他外国势力,所以国安法起到了一个止血止损的作用。
在国安法之下,香港社会迎来了繁荣稳定的新时期,共同合作抗疫,思考怎么从教育、社会、文化、司法等等领域完善香港社会的管制体系和能力,修复香港社会的裂痕和群体之间的对立,并且国家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在深圳新改革里也仍然聚焦深港合作,希望香港社会能快速完成社会能力的调整和复苏,及时赶上国家新一轮发展的快速列车,让香港社会的转型发展抓住最后一次机遇。
当然了,一个巴掌拍不响,国家不可能包办香港的一切,香港的未来到底如何,还取决于香港社会自身的反思、修复、重建的理性力量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多长的时间内,从结构上完成一个自我的更新。
从香港在近代史以来面对历次国家危机和全球性变局的应变和适应能力来看,我觉得香港社会有这样一种灵活的适应能力,重新找到自己的角色和进取的方向。
观察者网:其实“修例风波”之后,可能香港人自己现在都特别迷茫,未来到底在哪里。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该如何定位香港?香港还会是那个东方之珠、金融之城,中国向外看的窗口,还是会被边缘化,甚至取代?
► 田飞龙:在改革开放之初,内地对香港有高度期待,希望通过香港来学习经济现代化经验,走向世界,融入香港背后所依托的欧美现代化全球体系,所以香港在当时是一个优等生,对内地有示范作用。当时无论是党政干部,还是一般的青年大学生,甚至是普通市民,对香港都非常向往,能去香港工作,在香港拿到永久居民资格,让小孩从小在香港上学,都觉得是高人一等。
可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内地主场取得的成绩越来越大,中国在全球的分量以及发展战略日益定型成熟。这种巨大变化也引起了香港社会内部的精神不安,包括在世代更替中,香港青少年与自己父辈相比,与内地相比,产生了一个心理落差和认同困难,但这是发展性的事实,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
这其中,包括对“一国两制”,确实有一个更新认知的问题。如果说既往的“一国两制”比较偏向于尊重“两制”,今天的“一国两制”更加需要通过精准地认知“一国”,来完成对“两制”的理解。如果香港社会不能认识到“两制”需要更多地依赖“一国”,才能找到发展的意义和基础,香港很难寻找到出路。
在这方面,香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都认识到,无论从“一国两制”里国家本来就有的主权者和宪制秩序最终保障者的这样一个地位,还是从整个香港在中国和西方全球化体系当中的角色演变来看,香港都越来越需要借重国家的力量来巩固其国际地位。特别是美国因为香港国安法问题进一步结构性的制裁香港时,尤其是通过美国所谓的香港法案来否认其自治地位,引入了人员制裁和金融制裁时,香港传统上依赖美国体系的全球化地位和角色逐步会遭到削弱。而且香港牌会继续为美国所利用,在这种条件下,香港在原有全球化中的地位将不可避免被边缘化。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香港在“一国两制”里依托国家的全球化角色可能在升高。而新香港的命运和前途,恰恰就取决于在新旧全球化体系的博弈与更新之间,能精准把握好自己的机会,把已有的优势转化成发展的新基础。通过更好的融入大湾区来融入国家发展,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增强其在“一国两制”体系中的影响力和战略性功能,增强对西方体系的相对自主性,未来香港的定位将是战略性的。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中。图片来源:Licensing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美国打“香港牌”,实际上美国围绕香港问题、围绕国安法做了很多文章,包括制裁香港、颁布所谓的涉港法案、舆论攻击等等。但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以及发展定力,您认为美国还有能力打香港牌吗?
► 田飞龙:其实美国打香港牌也受制于自身国内政治。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它既是中国对外开放所依赖的一个平台,同时也是为全世界最发达经济体利益提供服务的共享性基础设施。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平台上,外资能非常方便地以它为跳板向中国内地投资,抢占中国内地市场份额。
同时在香港这个平台上,还能看到外国设立了大量的地区总部,通过香港与整个亚洲形成了紧密的经贸联系,包括人文联系。如果美国打香港牌,不断推动在香港与中国内地脱钩,过分削弱香港的国际地位,不仅对它盟友的利益,而且对美国自身的金融利益、商业利益都是巨大的损毁。因为美国不可能简单地放弃中国市场,不可能绕开香港,仅仅从台湾来对大陆进行补偿性的商业网络重建。
所以我们要看到香港问题是一个全球化合作的问题,合作网络的破坏对各方都是不利的,这一点越来越清晰地为西方国家和中国政府所共同认识。所以中国政府一方面制定了香港国安法,正当合理行使属于中央事权的国家安全责任,维护“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繁荣稳定,这一点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
另一方面,中央并没有放弃香港作为中国与西方相融通的关键平台,通过这个平台继续扩大后疫情时期经贸合作的规模和深度,中国在香港问题上、在“一国两制”问题上转守为攻,越来越稳健地通过香港平台推动更高层次的国家战略,同时这也契合了后疫情时期,各国经济复苏都依赖中国市场的诉求。如果美国仍然对香港牌揪住不放,而且加大制裁的深度和力度,我觉得美国会成为全球化的孤家寡人,并且它的政策实施也会到处碰壁,很难奏效。因为这些制裁都是反全球化的,也是反美国自身根本利益的,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二。
观察者网: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打香港牌的过程当中,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美国这次对疫情的糟糕应对以及美国衰落,深刻暴露了美国制度的弊端。对于同样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来说,如何在“一国两制”下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弊端?
► 田飞龙:我们原来讲“两制”,都是假定和推定香港各方面制度是完善的、是发达的、是先进的,而我们内地很多制度是不完善的,是要改革的,是要对标向香港学习的。把香港作为现代化的优等生,作为西方现代化体系在东南亚的投射,这样一种简单的、线性的现代化观念已经受到了批判。而且有意思的是,这股批判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于我们中国自身的理性反思,而是来自于西方自身的衰变。
西方所出现的民粹化和逆全球化,实际上破坏了二战以来全球对西方体系的基本信心和信任,以至于美国所维持和控制的自由霸权体系摇摇欲坠。随着西方本身的自我衰变,也就是基辛格所说的自由国际主义的衰落,美国出现了一种危害全球和平发展,危害国际组织合作体系,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的美国式实用保守主义,也被称为“特朗普主义”。
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需要对自身制度进行反思,香港并不是与西方一致的,所有制度都是好的,它的普通法虽然好,但是如果普通法没有正确的宪法和基本法国家观,没有国家利益的基础性视角,普通法其实会变形走样,不能有效维护“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的法治权威。
“占中”和“修例风波”以来,我们越来越看到香港法治和司法能力的弊端,这种弊端不仅是它不能够履行正常的维护秩序的功能,甚至起一个反作用,助长示威者破坏法治。反思香港司法制度,要增加国家法的维度。
另外一方面,香港的教育制度也不再是完美无缺,“黄丝带”教师错误的国家历史观和政治观,对“一国两制”割裂性的理解,暴露出香港教育体系也出了大问题。另外香港整个社会文化生态,本来应该是中西价值和文化传统的荟萃之地,应该有一个增量的综合性比较文化优势。但是我们却看到在香港出现了一种将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对立起来,并且衍生出一种非常畸形的本土主义文化。这样一种畸形的文化冲突,后现代化、后物质主义里对某一种特定价值观的偏执,以及极端放任的个人主义、自私主义、本地主义,其实对于香港社会团结产生了侵蚀作用。
同时我们看到香港的公务员体制在“修例风波”中表现出来的能力短板,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没有能力预警风险,没有能力化解危机。香港立法会在“修例风波”中被砸,缺乏权威,其代表性也受到损害。甚至香港立法会内部出现了严重损害宪制秩序和民主功能的破坏性行为,有些行为甚至达到了香港国安法在颠覆国家政权罪里面要制止的这样一个程度。
所以种种方面,香港社会要有反思,要有制度改革的议程,这样不是说要把“两制”变成“一制”,而是说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够固化僵化,完全无视事实和变化了的世界。要引入制度改良,增强共识,增强对香港民众的教育和动员,增强对国家战略和体制的理解程度,这样香港才能抓住先机,继续贡献于国家又助益于自身发展的双赢局面。
观察者网: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老问题,1984年邓小平曾提出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当时就有人问“50年后怎么办”?不同的是,当时这样提问内心里其实是有一种对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感的,但现在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要反过来了。
► 田飞龙:这个问题一直刺激挑动着“一国两制”里双方的神经,实际上我们要用动态的、辩证的眼光去看问题,所谓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都不是在原地踏步,所以我一直讲,“一国两制”最终的结果既不是内地的香港化,也不是香港的内地化,而是内地和香港追求一种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的是50年之后,可能“两制”朝着一国方向有更高程度的扬弃、融合和提升。尽管“两制”之间还有一些重要差异,但这些差异已经被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共同的部分越来越多,比如在现代化、对人的价值、对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共同点。
我始终相信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有一定的交叠重合,有能够直达人心并且流之长远的东西。“一国两制”恰恰是要超越这种姓资姓社、具有冷战意味的二元对立,探索在一个主权国家的秩序内部,如何能够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长期和平共处,在这种和平共处中创造一种互动融合的公平法则,以及将双方的焦点面留给历史实践来检验和塑造的高度政治自信,到2047年给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一国两制”的完美解法,这个解法将向全世界宣告“姓资姓社”的二元鸿沟不是不可以跨越,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包容式、创造式发展,通过吸收资本主义当中有益的价值和制度元素,使自己在世界历史更高的舞台上实现自我提升。到那个时候,“一国两制”的历史使命和历史定位,才能更好地被完整理解。
其实从习近平主席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当中,从中央所制定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和战略功能定位上,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两制”之间可以通过一种方式,达成更高的历史第三方的存在状态。
观察者网:我们看到现在美国也在挑起所谓的新冷战,出现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回潮,今年又是抗美援朝70周年,我觉得是很巧的一个事情,70年前是旧冷战、是抗美援朝,70年后又是新冷战、是中美贸易战,似乎美国人很难理解中国提出的“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这些概念。
► 田飞龙:美国用旧冷战打垮了苏联,又试图用新冷战来打垮肢解中国,这说明美国文明或者西方基督教文明遇到了自己的最高瓶颈,不能跨越自身的文明限度跟尺度,去真正公平、平等地与其他文明进行交往。它始终是以一种文明冲突、你死我活的异教观念和敌我二元思维去对待其他文明。当其他文明俯首称臣的时候,它可以暂且表现自己道德优越性包容之;当其他文明也按一种现代理性方式发展起来之后,它却要对其他文明发动战争。
比如对中国,我觉得美国没有找到超越冷战,实现人类持久和平发展这样一种康德理想的真正的、文明的解法。它在世界和平的方法论上已经落后,只能重复冷战的思维和故事,期待中国作为第二苏联的政治悲剧发生,从而再次展现所谓美国作为历史终结地这样一种道德制高点和制度制高点,这其实是产生了一种历史的妄想症和臆想症。而中国却能抛开这种冷战对立,用一种东方文化里的天下主义、和合文化、共存文化,有效去治疗和补救西方文化当中不可救药的二元对立,在世界和平发展的方法论上更高一筹。
接下来,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负责任地去解决国内政治和全球治理当中存在的问题,用东方文化厚重的和合伦理,去化解我们面对的矛盾和冲突。这种面向人类共同体的哲学和制度建设的视角,才能最终给人类带来一个永久和平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