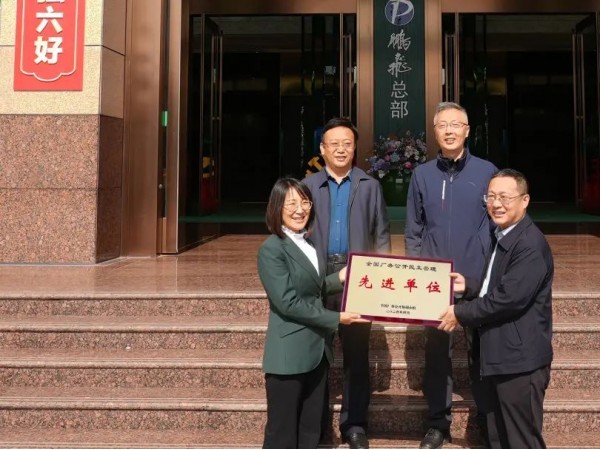王石从 57 岁开始“成熟”。
在那之前,王石说,“我是著名企业家,我珠峰都上去了”。2008 年在很多人看来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汶川地震,北京奥运和它背后的大国崛起,此消彼长间还有一个全球性金融危机又增加了中国的莫名自信。那一年,57 岁的王石事后反复说这是他的至暗时刻。
那年,他对汶川地震和其后慈善的观点冒犯了很多人。
所谓成熟,就像所有用来形容离开青春期的男生一样,成熟意味着不能畅所欲言,学会妥协,从“想”做的事到“应该”做的事……
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之一“成熟”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过了 10 年,王石深陷其中,可能也还没来得及全面冷静审视。
一些话已成空。比如吴晓波曾经给王石的书作序,“不再视自我为政府的依附及寄生物,并能够以更积极和现代的方式参与社会重建……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之一”。
到了后面宝能事件的时候,这样的人设或者期许也结束了。
“我是著名企业家,我珠峰都上去了”——上去了再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个有着不一般成就,贴满了强者标签的企业家、公众人物、励志偶像,自信几乎成了本能,甚至目中无人。
在我们的对话中,他表现出强烈的表达欲望,虽然他并不缺表达的机会;急切想表达自己的看法,虽然看法过于正确了。他经常使用反问句式,力量在身。
“你觉得我今天是一种不想讲话,谨小慎微的姿态吗?”
“言多必失,躺着都中枪,我是那个姿态吗?”
“那我要聪慧的话,我至于那样吗?”
“你觉得我在谈话当中是消极呢还是乐观呢?实际上你还需要答案吗?”
“不担忧,那是生活吗?”
“不是说我退了不适应,我怎么会不适应呢?”
“中国改革一直是自上而下,所以未来还是会自上而下,为什么不乐观呢?”
此次《十年》系列,我们联系了汶川地震时活跃的几位公众人物,但几乎都拒绝采访,有的提到汶川甚至避而远之。
王石并没有刻意回避,并且还为自己的自由表达颇为自豪。
但事实是,王石并不像从前那么“自由”了。
他尽量避免谈及他人。关于未来,他有诸多担忧,但却不愿意谈及具体内容,“谨慎乐观”是能得到的最接近的答案。
2018 年 5 月 23 日,我们在深圳万科总部见到了王石,这幢长 380 米的建筑由建筑师史蒂芬·霍尔设计,被称为“躺着的摩天大楼”。67 岁的王石坐在办公室里,穿着一件蓝色西服,西服口袋里点缀着白色胸巾。
10 年时间,王石的家国企业面目全非。他的自信也面目全非。
“ 2005 年我出了本书,我当时在后记上曾有这样一段话,“2004年,也就是万科 20 年的时候万科不会再有什么故事,为什么呢?伟大的公司是没有故事的,你说可口可乐,M&M's 有什么故事?”
当然万科不是伟大的公司,但是已经很接近了,接近了也就没故事了。但实际上你才发现,故事才刚开始。只能说我自大,自以为是,现在万科 34 年了,14 年又过去了,现在看,他妈的离伟大还远着呢。
过去的这十年太有意义了,二战期间讲丘吉尔的电影叫《至暗时刻》,我觉得我的至暗时刻就是 2008 年。很多人说过去的两年万宝之争是不是你的至暗时刻,我说不是,是 2008 年。
我 1983 年到 1984 年在深圳创业,那种经历,那种生不如死,明天能不能过得去都不大清楚,那一年经历了,就没有比这个经历更刻骨铭心的了,但它不是至暗时刻。
因为明天过不去,并不是说你人生过不去了。
我创业可能失败,可能打道回府,甚至深圳都待不下去,回广州,都有可能,但是这条路我不是被动的。我 33 岁到深圳前,我的经历基本都是被选择的。工作是分配的,不是你想做什么做什么,是分配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包括当兵,也不知道会分在哪。一切都是被动的,社会在安排。
但是我第一次辞职到深圳创业,这是我的选择,选择失败,我没有什么怨言,努力做到最后还是失败,那就失败了,不行再做其他的。就算那种艰难也没有让我感到人生过不去,因为至少你没有道德批判上的压力。什么叫至暗时刻?就是 2008 年,整个是道德上对我的批判,尽管你登上了珠峰又怎么样?
我记得 2008 年底,有个纪录片问我,“过去这一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说“三个感谢,不是感恩,是感谢,第一是汶川地震当中,我的表现让几百万网名对我排山倒海的怒斥和谩骂,让我重新认识自己。积极的讲,我意识到我个人的影响力比想象的大,万科的影响力比万科管理团队想象的大。”
既然比想象的大,我不知道,说了不适当的话,受到这样的谴责,是理所当然。
从消极意义上讲,一下把我打翻在地,从零做起,让你知道你是老几。原来我是著名企业家,我珠峰都上去了,但我还得重新界定自己。我并没有说,啊,想不到原来这个社会是这样,我没有。
但更多也显示出了我的固执,汶川地震时有另外一个著名企业家,他在我之后也说了类似的话,原来对我的谩骂即刻排山倒海转到他身上,但他没有固执,公关三天就紧急处理掉了,然后又哗哗哗转到我身上来。我还是说“我没做错,没说错啊,我凭什么妥协,我凭什么道歉,我凭什么解释?”
这也能看出来万科的公关能力相当缺陷,万科这么多年了不应该这样。
本身这不是一个坏事,我们想盖住,怕被揭发出来,比如三聚氰胺被揭发出来,不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说了大家不愿意听到的话,这不是说话对错的问题,是不失时机。我们又不紧急公关处理,就显得企业很不成熟,尤其在这种互联网时代,很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回顾这十年,这个事情对万科团队的成长影响更大。
虽然是因为我的言论引起,但整个处理是万科团队,因为毕竟我已经是执事董事长,很多事都不具体过问。我们最后决定把重点放在绵竹的遵道,从资金的投入到防震建筑,和那里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之后的雅安地震,我们从过去的只是激情澎湃和无序,慢慢看到理性和有序,应对自然灾害也成熟多了。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地震,我会不会说类似的话?我不会,因为我进步了。第二,假定我还会说类似的话,网民也不会用原来那种极端的不可原谅的态度对待我,因为社会在进步。
通过这个事情我们也意识到了万科太清高,太自以为是,但是不是 2008 年就彻底解决问题了?没有。而且过去的万宝之争又反映出来了,我们还是太清高,不接地气。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讲,你说这是一次股权危机,还不妨说是一次人事危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外界对我们有怎么样的认识,我们该怎么去处理。
尽管这样,但你觉得我今天是一种不想讲话,谨小慎微的姿态吗?还是一种觉得哎呀,我很成熟了,我不说了,反正言多必失,躺着都中枪,我是那个姿态吗?
今年 1 月 23 号我从万科退下来后做了第一次公开演讲,在水立方,我选的地方就是张扬的地方,对不对?
导演问我能不能选首我喜欢的歌渲染气氛,我说“蓝莲花”,“蓝莲花”的主题是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永不凋零的蓝莲花,这是我选的歌。
你说这是一种比较自信、狂妄的表示,还是一种谨小慎微的表示?

2018年1月 王石在水立方进行退任董事长后的首次演讲
这 10 年我最大的变化是对自由的认定。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做你想做的事情,因为很多原因,你都没法做你想做的事,所以追求对自由的向往,最高境界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现在这不是我的定义。对我来讲,自由是做你应该做的事。什么叫应该做的事?就是这个社会需要你做的事,这可能是你不喜欢做的。比如我做公益,整个社会需要公益的推动,但公益有很多种,我可以选择环保生态,我很喜欢,保护濒临灭绝的动物,比如大熊猫、雪豹、东北虎,我本身就属虎的,我也喜欢。
那垃圾分类、残障,我喜欢吗?坦然来讲,我不一定喜欢。但社会需要你做,所以我选择了应该。我完全不是从社会变化,政治变化角度去考虑,我是从我自己的成长考虑后这么决定的。
改革开放已经 40 年了,我创建万科 34 年了,我到深圳 35 年了,我一直在这样一个渴望自由但不自由的过程中,一直在挣扎,一直挣扎,一直往前推进。
这样的过程中,我一直考虑自己,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很多事情最后做了,发现结果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妥协,所以 2008 年才出现那个情况。如果我还是做我想做的事,不是不可以,也会很精彩,但是不是太自私了?
中国发展到今天,我是不是既得利益者?我是不是很成功的既得利益者?中国需不需要进步,需不需要改革?
如果我眼中还是做我想做的事,是不是太自私了?是不是应该更多考虑社会需求?从想做什么变成应该做什么,这是我对自由的一种更新的理解。换句话来讲,本身自由和约束也是一致的。如果自由没有约束,就有很大的问题。
2008 年,我 57 岁,那时候已经年龄不小了。我 50 岁的时候什么感觉?50 岁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活跃,是中央电视台的常客。我也比较势利嘛,现在中央电视台不是请什么我都去了,但当时只要中央电视台请,我就去了。
其中一个栏目我一进去,就发现答应错了,一看是“夕阳红”栏目。观众里一群老头老太太,我觉得我进错棚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跟导演说我答应错了,我说有一天我会是夕阳红,但不是今天。
我觉得这就像昨天一样,今年我已经 67 了。

深圳万科中心
2000 年,王石 49 岁,那年开始,他几乎每两年出一本书,讲述万科的创立以及自己的登山游记。书的内容和封面无不展示着他敢于挑战、个性张扬的一面。
如此经营形象,让王石成为企业家中少有的在自身企业外,还为其他公司代言的人。他代言过的品牌不下 10 个,且品牌必须符合他一向的形象,和顶级奢华相关的代言,都被他拒之门外。
王石的个人英雄主义塑造了他的个人形象,同时也决定了他大部分的人生轨迹。
1983 年前,王石人生的所有选择都是被动的,分配工作、入伍当兵,直到 32 岁从广州辞职,到深圳创立万科,他开始追求个人实现,并且首战告捷。1991 年万科成为中国大陆首批公开上市的企业之一,1998 年成为中国上市公司当中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王石从一开始就被标签化。
直到 2008 年,王石遭遇了被他称为“至暗时刻”的捐款门事件,“明天都可能过不去了,怎么会不是至暗时刻呢?“
2008 年 5 月 12 日,万科宣布向四川灾区捐献 200 万元人民币。网友一致认为这一数字太不体面。
5 月 15 日凌晨,王石在微博上回复:“对捐款超过 1000 万的企业,我当然表示敬佩。但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 200 万是合适的,这是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 200 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万科在内部号召进行的慈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 10 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这条微博引起了大量的批评和嘲讽,王石迅速成为了众矢之的。王石在自己的书中回忆起那一天时说:“我被全国网民共讨之,口诛之,随后,强烈的情绪发酵,爆发,酿成了万科史上最大一次舆论危机。”
王石始终认为多数人的慈善也会走向多数人的暴力,直到今天,他也不认为自己说错了什么。
但 2008 年 6 月 5 日万科的股东大会上王石还是道歉了。大会以他的道歉开始,以他的道歉结束,会议决定向灾区追加一亿元捐款。
2009 年后,王石开始在香港科技大学和北大讲授商学院课程,同时担任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会长,2011 年又担任了壹基金公益金会的理事长。
“公益”逐渐成为了万科和登山之外的第三个标签,现在王石担任 40 多个公益组织的顾问,10年前这个数字是 4。
这个时候,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慢慢开始褪去,利他主义更多出现在他的生活中,王石认为这是他过去 10 年最大的变化之一, “但是利他主义也有前提,还没出名的时候,就义不容辞的去利他,很多人可以做到,但我做不到。那时我是不损人的利己主义,在利己的前提下可以利他。”
1983 年王石从广州到深圳创业时,他对这个新的经济特区的未来毫无把握,深圳当时被他当做了“间隔年”,他计划着 2 年后就到美国加州留学。但创立万科后,他就再没动过这个念头。
直到 50 岁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留学梦还未实现。
2010 年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的答谢宴会上,基金会执行主任邀请王石到哈佛访学,王石立马应下来。但哈佛内部因是否应该邀请一位中国企业家到哈佛访学引起了不小的争议,3 个月后哈佛又安排了一次小型“面试”后,才给王石发了正式邀请函。
到哈佛前,王石几乎全然拥抱西方文化,“过去我的经营、管理理念一直是‘拿来主义’因为现代工业、现代化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王石说。
并且,对于王石来说,接受和学习西方并没有太大障碍,他的家庭里没有知识分子,初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王石就没受过正统的中国教育,因此并不存在两种观念互相碰撞的情况。
为此他甚至感到如释重负,“我一直把这当作自己的优势,之前我的主观意识里对传统文化是有距离感的。”王石说。
本身我对西方是全然拥抱的,但是你会发现建国这么多年,我们搞的工业体系、人类文明和西方的工业现代化是一致的。尽管我们是计划经济,不同的体制,但很多地方并不矛盾。比如制造、工艺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只是财富的分配,市场的运作、竞争模式不一样。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也是以现代西方的契约精神为导向的市场经济。
所以我到美国后并不觉得自己是一张白板,本身我已经有很多经历,因为新中国建立后很多地方和人类文明的大方向一致。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相比,显然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批判的,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虚无的。什么叫批判?你得知道为什么不好。我们受的教育导致我们虚无式的批判,我们本身不了解,但又否定它,实际上就是虚无主义。
对虚无主义,我一直是沾沾自喜的,我觉得这是我的优势,为什么?因为我没受过污染,我是一个初中二年级就开始文化大革命,文革之后就没怎么受教育的人,一直是批林批孔,打倒孔家店,过去的五四运动一直到现在,我受的教育都是空白的。
所以到了深圳后,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知识。之前我读小说、文学,看有限的进口片子,对西方也很崇拜,很向往。
而真正到西方后,我了解的西方不是就西方谈西方,更多是进行比较,因为我还是中国人,骨子里是东方的。像我是工科学生,我没有受过非常系统的逻辑训练,到了哈佛,接受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什么好什么不好我会按照同样一个逻辑比较,但一比较我就发现没法比较。
原来我觉得对西方的理解不够,结果发现我对自己的文化了解也不够。即使我们的文化不好,没问题,但你得了解它为什么不好,不能虚无的说就是不好,是封建,就是糟粕。
我去哈佛前,我本身就在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和北大光华开课,讲企业文化,第一课讲的就是企业精神,我说中国没有企业精神。
我到哈佛和老师谈话,老师说中国是井田制,平均主义。每人一块田,中间是公田,是契约性质。刚解放的时候还有地契,后来烧掉了。地契是契约吗?当然是。如果没有契约精神,地契怎么延续这么多朝代,一直到解放。
中国的契约传统和西方不同,当然有传统的弊端,比如中国的企业是连带责任人,我们俩签契约,中间有保人,你出了问题,你还有保人,更多是连带,为什么中国讲“父债子偿”?在西方没有,因为西方是有限责任,有限导致你再完成不了,老婆是老婆,孩子是孩子,和他们没关系。
这就是现代西方的契约精神,这样一种进步导致它繁荣发展,但在中国不行,你会发现中国现在还有这样的事,明明我是有限,不用承担责任了,但还是父债子偿。

哈佛大学
再一个中国的契约精神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同情弱者。西方有什么同情?从竞争来讲,你败就是败,不会同情弱者。而中国不但有保人,还同情弱者。
在农业文明,平均土地的时候,谁是弱者?肯定是卖土地的,买土地的是强者。
你卖田或者卖房你想收回,或者买方想把土地卖了的时候,原来的卖方有优先选择权。第二,不但有优先选择权,卖给他还必须是原价。
所以你会发现中国更多讲平均主义,社会就会缺少竞争行为带来的进步,但同时,它讲的更多是大家都有饭吃。
有了这个认知,我就知道现在中国政府处理问题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同情弱者。
发生大公司和业主冲突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了,不要认为我法律上占理,我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同。举个简单例子,市场不好的时候降价,他就会闹事对不对?我心想,你房子已经买了,那是你的,我现在新的房子我要升价降价,这是我的事。我提价你不管我,因为你跟着占便宜,对吧?我降价你找我说“你降价我受损失了,你得补偿我”,我需不需要政府制止他们这种行为?
发展商和客户谁是强者?我是强者。所以怎么办?不降价不行,降价还得降,是市场调整,但我不能理直气壮,我讲“过节促销”总可以吧?变相降价,他就不会这样闹,这就是中国文化。
2008 年地震我的言行不慎也得出了拐点论,拐点论怎么来的?不就是我降价吗?降价一下引起除了中央政府和准备买房子的人以外所有人的愤怒,中央政府希望降价,同行不愿意降价,地方政府不愿意,准业主不愿意,买了房子的人也不愿意降价。
我去哈佛之前,对于这些我都是很愤怒的。那些买了房子,还没拿到房子的准业主,他也很愤怒,闹事啊,闹事就围着万科售楼处不让万科卖房子,阻挡那些要买万科房子的人,“你不给我补偿,我就不让你卖房子”。
我们担心就请公安局过来,说你们得维持秩序,这是市场经济,这法制社会啊,你不能不管。警察来了,不管。
你说我愤怒不愤怒?警察说只要不出人命,只要不发生殴斗就不管。
为什么?到哈佛后我就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情弱者的原则决定了我是强者。但你说是不是不搞市场经济,不搞企业精神了?不是,政府那样处理有它的道理,所以更多认识中国文化,比较东西方差异,才知道在中国我应该怎么做。
现在我们学习西方更多的是技术层面,方法论上他们比我们先进,我们拿过来可以怎么用,很少从这个层面去想。

王石在美国登山
我在哈佛有双重身份,作为一个踏踏实实的学生在学习,另一方面也是模仿,模仿老师上课。
我百战归来再读书目的是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最大的影响是教育,要把我总结的经历和理论系统整理,和学生交流。2009 年我就接受香港科技大学邀请去教书。
本身我就有一个老师的姿态,所以在哈佛我不单单是听课。我记得我选了一门阿拉伯颜色革命的课,我一推门,就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我想肯定错了,后来下一节课我再去,就我一个人,我问“你是不是那位老师?”他说“是”。
在哈佛我才知道,必修课你必须听,选修课就是你选的。很多老师开选修课,规定只要有三个学生选你的课,你就得开。
他告诉我当时有三个学生选了课,第一节课听了之后这俩都跑了,现在就我一个了。就是说就你一个学生,你也得上,这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原来想我本身就是著名企业家,肯定有面子,我讲课那 50 人是最少的,得上两百三百人,所以我非常在乎听的人数,后来我才发现,真正显你水平的是听的人越少,你还能讲下去,这才是水平。
类似这样的例子,真的就像开了一个天窗式的。
我选了一节关于新能源的课,那个我印象非常深刻,20 多个学生,教授拿了一副扑克牌,分给我们一人两张,一张红,一张黑。他说咱们做个游戏,这两张牌,你选一张。
选择红的,你可以得三分,其他人都选红的,再给你加一分。你选择黑的,你得一分,但其他人选黑的,可以给你加两分。
诶哟,有意思吧?因为你不知道其他人选了什么,你选红选黑要根据其他人的选择决定。那你算一下,你如果选红,你首先就得分多,三分,比别人多了 2 分。
最后我选了黑色,最后证明选黑的得分多。
老师接着讲了两个数学概念,第一个是囚徒困境,第二是纳什均衡。他说现在的新能源政策,就是囚徒困境,他妈的多精彩,是吧?
你让我讲数学的囚徒困境怎么算,会讲得很复杂。从新能源价格上讲,就是政府的补贴,补贴多少,政府怎么考虑?为什么?
唉呦我说,这他妈,卧槽,什么叫大家?真是精彩。
完了之后,他接着讲数学的公式推导,听懂听不懂没关系。大学微积分我他妈早忘了,我又回去复习了两个月的微积分。
但是你感觉到兴奋的一瞬间,即可进入痛苦状,因为我还是有完成作业的压力。当然访问学者不用完成作业,但是我给自己压力,没有压力怎么进步?我不是抄同学作业,我是借同学笔记,因为我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我是个哑巴英语。
我巴结同学就是请他们吃饭,有一位同学叫 Eirc,离开哈佛后我在北京见过他,他问我:“你知道你请我吃了多少顿饭吗?200 多顿”, 就在哈佛的两年半。
在哈佛我一切都非常紧张,压力非常大,本身就处于一种防御状态,紧绷着自己。做作业真的是在炼狱里煎熬自己,平时做作业觉得吃饭都是耽误时间,20 分钟解决问题后就做作业,做到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很少说是完成了。
我绝对不是那么聪慧的,我绝对是笨鸟。我要聪慧我至于那样吗?什么叫学霸?我根本不是,这也不重要。

2017 年王石参加深潜艇扬州大师赛
王石第一次到日本是 1986 年,之后的多次考察让他开始对一个面积仅相当于中国云南省的岛国如何成为世界工业强国颇感兴趣。随后,万科的管理也参照了二战后日本企业比如索尼、松下和丰田的模式。
但王石一直没搞明白的问题是,中国和日本同时开始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为何日本成功,中国失败?江户时代的日本工商阶层在运动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这成为了他在哈佛研究的课题之一,同时也是今年即将完成的两本书。
我在哈佛两年半,本来是想把我关于日本的书写完,主要是写日本江户时代,也就是十六十七世纪到 19 世纪末,这 260 年,第一是国民普及教育,第二接受西方文化知识分子界的准备,第三是中国和日本工商业的比较,这段时期对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有什么影响?2011 年之前我就写的差不多了,希望在哈佛能完成这本书。
不好意思啊,我差不多是每两年出一本书,我实际上更多写的是随感,《道路与梦想》是以编年史的方法写我创立万科,每一年万科发生的事。当然也有专门写登山,但更多是游记,常常是去一趟以色列一个礼拜,我可以给出一本书。为什么不好意思呢?就是有点粗制滥造。
我2011年走的时候,正好新书出版,叫《生命高处》,就是所谓灵魂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步是《让灵魂跟上脚步》,第二步叫做《徘徊的灵魂》,第三部《生命高处》。你看,还是挺有这个逻辑的啊,是吧?(笑)
他妈的,到了哈佛之后,就出不来了。我希望这本书有点不同,希望有逻辑训练后多少沾点学术,比原来更逻辑更强,更系统。
但是到了哈佛之后,我发现我不会写书了,我想要立足和原来不一样,有所提高,但你发现你回不去了,写的不三不四。你看今年是 2018 年,这本书已经是第 11 稿了,13 万字,一稿不行,再一稿也不行,一直到现在。
不是不满意,是觉得没法看啊。我争取今年完成两本,虽然我出不来,但是是一种进步的出不来,我还是觉得每年都在提高。
在哈佛我的收获非常大,离开哈佛后我的心态是想回去但不敢回去,一直到 2016 年才回去了一趟,我才发现我他妈也太在乎自己了。为什么?我觉得待了两年半,回来我总得交个答卷,总想把我那本书完成了,后来才发现不能太自以为是,谁他妈把你当回事?只有你自己。
后面到剑桥就完全另外一回事了,到剑桥我就不做作业了,我不逼迫自己了。换了环境,我原来紧张防御的状态也放下来了,在剑桥人家不知道我曾经那样说话结结巴巴,虽然现在英语也讲得结结巴巴,至少原来的那些障碍没有了,不那么紧张了。
在剑桥我转成了研究犹太人在东亚的迁徙史,很多人包括犹太人都觉得我选择这个课题非常意外,第一中国的商人研究犹太人很奇怪,第二犹太人也研究犹太人的现代问题,所以就更感到奇怪了。
我选它逻辑很简单,我之前在哈佛研究日本问题,在对日本的比较中发现日本人和中国人对犹太人的看法非常不同。
历史上,2000 年前最后一个国家被罗马摧毁后,犹太人基本就是全世界迁徙,一个被迫害的历史,到最后大屠杀,种族灭绝。
中国人觉得我们和犹太人挺亲近,第一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反犹,犹太人在全世界被排斥,但在中国没有。第二,我们都还挺会做生意。第三,我们都非常在乎大家庭。第四,我们都很重视教育。二战期间我们又包容和支持犹太人,让两万多名犹太人移民到上海,就感到一种亲切感。
但我接触了学术文章,接触这段历史才发现,我不敢苟同。
我讲一个典故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的犹太社区已经有 1000 多年了,追溯到北宋年间,那时候就有社区记录,但他们记录的不是犹太人,是回民。他们根本不知道他是犹太人,你怎么反犹?民众不允许在中国建立教堂,但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犹太教,真正说要摧毁教堂的时候,你能说犹太教不摧毁,我们把基督教天主教摧毁了?我们历史上是这样吗?不是。

剑桥大学
2015 年王石在剑桥大学的访学因为宝能之争被打断。2015 年 8 月宝能集团成为过去20年时间以来万科的第一大股东。4 个月后,王石宣布,不欢迎宝能系成为股东。去年,战争以深圳地铁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而暂时告一段落。
王石办公室门上的职务从“董事长总经理办公室”变为“董事长办公室”,到最近的“董事会名誉主席。”
故事还没结束。
卸任董事长当天,王石在朋友圈写到“我在万科 34 年,当了 17 年的甩手掌柜,现在将开始自己新的 17 年。再过 17 年,我也才 83 啊!”。
王石认为塞涅卡的诗最能代表现在自己的态度:
“灾祸对于真正的大丈夫来说是机会。我们有理由说,那些因为过多的好运而变得迟钝的人是很可怜的,那些人可以说是在波澜不惊的海面上过着风平浪静的悠闲生活,遇上一点儿事情就会顿感不适。”
2013-2018 我最大的变化,还是在 2016 年。因为 2015 年发生了宝能之争后,我更多精力就转到国内,处理公司的事了。
我原来的主要精力就是在学校讲课,校园访学,2015 后基本就停止了。
我去年 7 月份退下万科董事长,基本的时间分配就是 3331,30% 是公益,30% 华大,30% 远大,10% 是个人时间。
我做华大董事长可不是像万科这样,只是精神领袖,我必须发挥作用,公司时间长短不一样,涉及的业务也不一样,第一我要了解他们的行业,第二要熟悉企业,第三我要在企业发展中,出谋划策,深入下去处理事情。
我要感谢我生在这个时代,进入了长寿社会,寿命比以前长了。按过去来讲,人到七十古来稀,你 60 岁的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去体会,生命快对你关门了,你怎么发挥,怎么扮演角色?但现在我还有机会去体验,提高修为和认识,所以访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今年秋天我就计划去希伯来大学,之后还要去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原来我记得 2011 年去哈佛的时候定了三年计划,但我在哈佛就待了 2 年半,剑桥一年变成了两年。我计划去希伯来大学半年,但我估计也得 2 年,我又觉得伊朗也应该待一年,人不能太贪心。
再一个我从万科退休了,做一个企业家,我要做什么?我觉得有 2 年的调整期,现在一年过去了。
我离开是需要做准备的。不是说我退了不适应,我怎么会不适应呢?我早就是甩手派,早就是一个精神领袖了,我做公益活动,做和万科没有关系的事情。所以我从万科退休,万科无缝衔接。
我可以这样说,从我开始登山,和万科保持疏离我就在做退休准备了,但是我原来准备的时间不是去年,我是提前退休了,所以我退休后万科做什么?我作为企业家,我离开万科我要做什么,我到现在我也没想好,但这要做准备的,准备的时间是2年。
不能说我乐观,我就没有担忧,乐观和担忧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没有担忧怎么可能?不担忧,那是生活吗?那只是你的期望。担忧就是生活,担忧是什么不重要,生活当中无论怎么样都会有担忧。
我非常坦诚布公来讲,改革开放 30 年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标杆人物,回忆过去30年我最大的感受是我没有想到我个人、企业、民族和国家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我对未来不确定。
我记得在阿拉善 2012 年的年会上,我的发言题目就是面对未来的不确定,自我修正。
今年改革开放 40 年,我还是那句话,尤其是过去十年,我更想不到有这么大起大落,这样波澜壮阔的时候。
面对未来我从“不确定”,变成“谨慎乐观”。
我是乐观的,但这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十年前我出事了,我不确定,这种不确定一直持续到 2012 年。
但到了 2018 年,我在总结改革开放第二个 10 年,我担忧什么?我担忧的东西多了,我们不去展开讲,这个也说不清楚,是吧?所以才要谨慎乐观。
这个乐观怎么来的?
从个人讲,万宝之争现在至少有一个大概的结果,但对未来,这个故事还没完,我还在看,我是乐观的。另外我投入环保,从某种意义来讲,在国际舞台上,对应气候变化,我是标杆人物之一。
从国家来讲,我们国家是不是一个污染大户?我们碳排放最多,我们是不是在讲经济发展不顾环境破坏?现在环保是非常大的问题,比如雾霾,比如食品健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