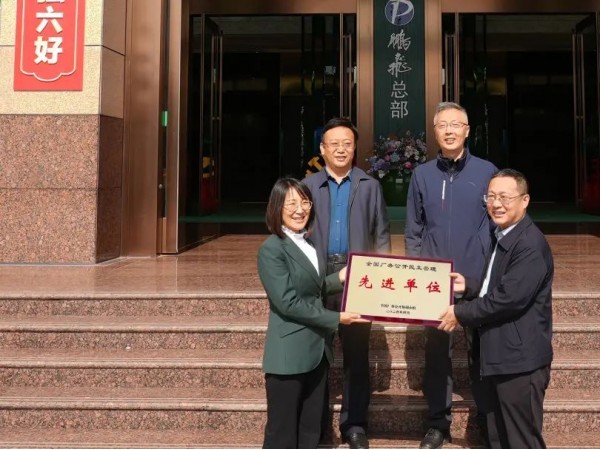——《国家能源转型与碳中和丛书》序言
2024年6月29日,第一届国家能源转型与碳中和论坛召开,会上,发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朱彤研究员主编的“国家能源转型与碳中和丛书”第一本专著《转型中的电力系统》(张树伟著)。本文是该丛书的序言部分。
将“系统思维”和“效率原则”贯穿能源转型始终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这不仅充分体现了我国在气候变化这一全球危机问题上责任担当,也标志着我国能源转型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在“双碳”政策推动下,我国能源转型与减碳进程进一步提速。比如,2021-2023年间,我国风能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总和从6.34亿千瓦增加到10.5亿千瓦,两年增长65%;新能源汽车销售量从352.1万辆快速增加949.5万辆,两年增长1.7倍;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从400万千瓦猛增到3139万千瓦,两年增加6.8倍。截止2023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含水电和生物质)发电总装机达15.16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51.9%;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2.07万亿千瓦时,约占发电量的31.3%。此外,我国电力部门碳减排也取得明显成效。2022年,全国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碳排放约541克/千瓦时,比2005年降低36.9%。
然而,我们在为上述成绩而欣慰的同时,不应忽视我国能源转型实践中逐渐显现的一些问题。这里仅举三例:
一是可再生能源规模快速增长遭遇的网络瓶颈制约日益凸显。比如,2021年为加快屋顶分布式光伏发展而实施的“整县推进”政策对推动分布式光伏发展效果明显,但该政策实施不到两年,全国很多地方就因电网冗余度消耗殆尽而对分布式光伏并网亮起红灯。
二是一些应对“风光电”波动性和间歇性的政策措施面临“必要性”与“经济性”的两难困境。比如,2021年7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发布的“鼓励”集中式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站配建储能的政策,在实践中演变为20多个省先后实施“强制配储”政策。各地“强制配储”政策一方面推动了我国新型储能短期出现爆发式增长,另一方面给配储的新能源发电企业带来沉重的成本负担,且至今缺乏完善的储能成本补偿机制。不仅如此,在这些被要求配置储能设施的企业“两小时”配储成本还难以消化和承受时,一些地方在“风光电”规模快速增长的压力下,强制配储的要求从“两小时”,扩大到“三小时”,甚至“四小时”。在这种情况下,配储成本恐怕不单单是“完善配储成本补偿机制”了,而是首先需要对这些成本的“合理性”进行评估。
三是高比例波动性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的高“系统成本”问题。随着电力系统重风光电占比的增加,未来电力系统需要的“系统灵活性”规模可能数倍于目前的电力系统,从而导致“系统成本”大幅上升。OECD和国际核能协会(NEA)2019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当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系统渗透率为10%时,其所研究的案例系统成本为7美元/MWh;当渗透率提高到30%,系统成本相当于10%时的2.5倍;渗透率达到50%时系统成本相当于10%渗透率的4.3倍。当然,由于不同国家现有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差异较大,波动性可再生能源相同的渗透率下的电力系统成本也不相同,甚至差异很大。现有电力系统的技术灵活性和机制灵活性越强,现有机制对大量分布式、小规模灵活性资源的利用能力越强,波动性可再生能源规模扩张导致的系统成本上升幅度越小。但无论如何,系统成本大幅上升趋势是能源转型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是否有减少系统成本持续增加的替代方案,以减少我国能源转型的代价。
上述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是能源转型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而第三个问题则是根据能源转型理论研究而“发现”的、在不远的将来大概率会发生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本质上反应了能源转型与碳中和进程中“效果”与“效率”实际和可能的冲突。
所谓能源转型与脱碳政策“效果”,是指能源转型和脱碳政策目标实现的“程度”和“速度”。比如,2023年底我国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合计装机容量已接近11亿千瓦,距离2030年完成12亿千瓦装机的发展目标仅一步之遥。这表明我国推动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的相关政策无论从实现的程度,还是速度“效果”都很好。然而,政策“效果”好,并不意味着政策“效率”高,即实现具体能源转型和脱碳目标所支付的“经济成本”低。从实践看,由于种种原因,能源转型与脱碳政策“效果”与“效率”对立的案例并不鲜见。笔者认为,其关键原因在于:
第一,气候变化倒逼的能源转型决定了“效果”的地位重于“效率”。历史上发生的能源转型,比如,煤炭替代植物薪柴,石油替代煤炭等,都是效率提升的技术创新驱动的。“每当效率更高的新“能量原动机”出现取代旧的原动机,显著提高了人类所能利用的能源的量级,能源转型就会发生。”然而,当前正在进行的能源转型则是气候变化倒逼的。这从两个方面导致能源转型实践中“效果”优先的局面: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缓解全球变暖的紧迫性所形成的舆论氛围和心理压力导致加快能源转型和脱碳进程的“思维惯性”,实践中倾向于采用能短期迅速看见“效果”的措施(即短平快政策工具);另一方面,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外部性”导致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博弈中表现出“鞭打快牛”的特征,试图让积极落实承诺的国家加快转型,提前实现碳中和,对由此发生的成本不置一词。
第二,当前能源转型不仅仅是不同能源品种替代,更是能源系统的转型。化石能源时代的几次能源转型,比如石油替代煤炭、天然气替代石油和煤炭,都属于同一能源系统中不同能源品种的替代。这两次转型同属于化石能源系,其能源系统技术经济特征相同:都是大规模、集中式能源生产、运输和使用系统。当前的能源转型不仅仅是不同能源品种的替代,更是不同能源系统之间转型,即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零碳能源系统替代目前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高碳能源系统。由于可再生能源的能量密度低、分布相对均衡,其能源系统的基本技术经济特征必然是适度规模和本地化(分布式)系统。目前的化石能源系统和未来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特征、网络架构和用能的商业模式差异很大。这大大提高了能源转型与脱碳政策实施中“效果”与“效率”兼顾的难度。因此,如果仅仅在“能源结构变化”层面来理解当前能源转型,对现有能源系统及其背后的能源体制机制不做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来推动能源转型,很容易导致“低效率”能源转型与脱碳“效果”,并且这些“效果”从中长期看有难以持续。
因此,将“系统思维”与“效率原则”贯穿于能源转型实践,对于缓解、甚至避免能源转型与碳中和进程中“效果”与“效率”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我们用“系统思维”和“效率原则”去分析前面提到的三个“问题”,可以极大拓展认识视角。
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我国“能源系统转型滞后于可再生能源规模扩张”的现实,以及调整我国能源转型政策重心的必要性:应该把加快系统转型置于我国能源转型政策的优先地位。过去,我国能源转型政策一直以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为直接政策目标。这一政策一直行之有效的前提是现有的能源(电力)系统存在一定的冗余度,有足够的灵活性应对波动性风光电发电量增加。然而,我国风光电发电量占比从2020年的10%快速增加到2023年的15%,电力系统的冗余能力已达到极限。这意味着我国能源转型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需要通过加快能源系统根本变革,大幅提高系统灵活性来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更大空间。而且,随着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技术进步带来发电成本大幅下降与竞争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扩张应该主要交给市场,政策重点应该转向难度更大,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身难以解决的系统转型方面来。
第二个强配储能政策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系统”问题,其基本逻辑是:电网难以承受风光电大幅增加带来的波动性,因而需要由风光电发电企业配置储能设施来解决。然而,无论从“效率原则”还是“系统思维”角度,“强制”风电和光伏发电企业配置储能设施的做法都存在很多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从“效率原则”看,电化学储能目前成本过高,提高电力系统灵活性还有更经济的手段。比如,改变抑制系统灵活性的网络运行规则,在部分负荷增加电转热设备,加快提升负荷灵活性的技术改造和机制构建,增加区域电网联络线,等等都是提高系统灵活性更有效率的措施。当然,尽快完善电力现货市场与辅助服务市场,提高机制灵活性是当务之急。
其次,从“系统思维”角度,用强制风光发电企业配储的方式来解决波动性风光电增加导致的平衡问题,实际上是假定现有电力系统是最优的,已经没有提升灵活性的空间和潜力。如前面所分析的,这显然不是事实。波动性风光电规模扩大的应对思路是大幅提高电力系统灵活性,灵活性可以来自电源侧、电网侧,也可以来自负荷侧。决定灵活性资源的提供方来自哪个环节,哪一种资源取决于其经济性(即效率)比较。
最后,要求一定规模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企业承担的系统平衡责任是合理的,但以强制配储的方式要求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企业承担平衡责任显然是低效率的。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企业是以自建储能设施的方式,还是以购买灵活性资源方式承担平衡责任,应该是企业自主的理性选择。由于目前并不存在企业能够做出这些理性决策的体制机制环境,因而构建有利于发现灵活性资源(包括大规模灵活性资源和本地分散的灵活性资源)及其价值实现的体制机制才是有效率的系统灵活性提升之道。
第三个问题更值得深思。它意味着即使我们基于能源转型的逻辑优化思维和政策,避免了不必要的转型成本,也不得不承受能源转型必要的高系统成本。因为高比例波动性可再生能源电力需要比现有电力系统更多的“备用”和其他灵活性资源来平衡系统,导致系统成本大幅度上升。这一结论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有趣的是,德国学者Lion Hirth等人通过长期跟踪研究发现的“德国平衡悖论”现象再次让我们开了脑洞:2008-2023年德国的风能+太阳能装机容量增加了五倍,平衡备用容量反而减少了50%,平衡备用(aFFR和FCR)价格在2008-2020年间也下降了80%左右。这至少表明,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增加与备用容量增加不是简单线性关系,存在着抑制系统成本增速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拓展思路:随着零碳能源(包括节能)技术成本大幅下降,构建(一个或多个)以终端用户为主的分布式零碳能源(电、冷、热和作为储能介质的产品)系统,而不仅仅是分布式电力系统,同样可以起到降低其系统成本的作用。
总而言之,笔者想强调的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系统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零碳能源系统转型,是“百年未有之变局”。其转型的困难和阻碍不只来自实实在在的“利益冲突”,更来自在应对能源转型问题时难以跳出的、基于200多年来化石能源系统及其体制机制所形成“惯性思维”,以及由气候变化倒逼的能源转型所伴随的特殊问题和风险。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决不受他人左右。”笔者认为,要将习总书记这一要求落到实处,针对实践中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对当前能源转型的微观机制研究,理解“系统思维”和能源转型逻辑对提升能源转型与脱碳“效率”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本套“国家能源转型与碳中和”丛书就是上述思考的产物。丛书围绕当前我国能源转型与碳达峰碳中和实践中的前沿问题选题,力图通过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探寻实践问题背后的理论本质,并通过不同风格的专著传播有关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的客观、理性观点。
此外,笔者的研究团队还将与丛书出版机构——经济管理出版社——密切合作,围绕丛书的写作、出版和推广,通过举办系列论坛、发布会、研讨会、委托研究等不同方式“聚合”各界志同道合者跨界交流与合作,共同为推动我国走“可持续”的能源转型和碳中和之路尽绵薄之力。
朱 彤
2024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