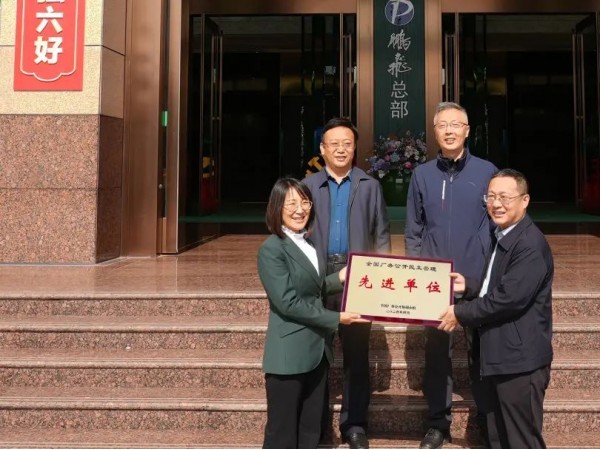今年初开始,国际市场就在等待美联储降息和美元指数走弱。但直到现在,市场并没有等到美联储降息,反而是美元指数已经升值近4%,美元的韧性超出了市场预期。
美元的这种强势不仅仅来自于美国自身通胀的黏性和相应降息时间的推迟,而且还体现了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重估、对各个发达国家基本面的重估。从中长期来看,美元指数的中枢可能已经显著上移,因此不宜在中期内对美元指数的下行抱有过高期待。
首先是地缘政治风险的重估。2022年初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延宕至今,地缘政治冲突不但没有出现缓和迹象,反而又爆发了新一轮巴以冲突,该冲突已经波及到了周边国家以及红海局势。即使在欧盟这样的和平地区,6月初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公布:该地区的极右翼势力正在快速崛起。由于法国现任政府感受到该势力的威胁,随后马克龙宣布提前举行国民议会选举,这些不确定性也导致欧元大幅下跌和美元指数的相应上升。
放到百年变局的大背景之下,这些局部冲突和社会、政治撕裂的发生绝非偶然。一方面,全球化在很多国家的民众当中面临很大的质疑甚至是信仰崩塌,欧洲和美国不同程度上都面临这种挑战。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全球治理赤字不断扩大,联合国、WTO等机制的功能显著弱化,其对地缘政治冲突的预防、协商、解决功能都面临很大挑战。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美元本身作为避险货币的吸引力就在上升。同时,近年来,日元明显丧失了传统避险货币的作用,地缘政治动荡的背景下全球安全资产更显稀缺,这也进一步凸显了美元的避险货币地位。
其次,市场也在重估各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美国经济显著强于欧洲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2023年美国人均GDP已经超过8万美元,分别是德国、日本的1.7倍、2.4倍。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目前只有美国经济回到了疫情之前的趋势线上。从美国自身来看,美国有望在AI等新技术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进一步带动劳动生产率提升。美国通过吸引大量移民也保持了劳动力、科技人才的优势,尤其是相对于日本和欧洲国家。2024年一季度,美国实际GDP同比增速为3.0%,远高于欧元区的0.4%、日本的-0.2%和英国的0.2%。
根据IMF的预测,2024年至2029年,美国平均经济增速将达到2.2%,显著高于欧元区的平均增速1.3%和日本的平均增速0.7%。近期我们团队在东京的调研中,日本经济学家也坦言,日元的贬值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即使美联储降息、利差回到正常水平,日元恐怕也难以回到135或更强的水平。这也意味着,美元指数的底部有了更多支撑、美元指数的中枢明显抬升。
通胀方面,美国较其他发达国家也更具有黏性。美国通胀的中枢水平较疫情之前已经有了显著抬升,这可能导致未来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幅度将低于预期。中期来看,美国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力市场趋紧,工资增速明显高于疫情前水平,劳动力成本上升推高了通胀中枢。此外,更为强劲的经济基本面,也将从需求侧拉动通胀。根据IMF的预测,2024年至2029年,美国CPI通胀率的均值为2.2%,这意味着美国的通胀水平将显著高于2010年至2019年的均值1.8%。另外,美国的通胀黏性强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在此背景下,2024年3月瑞士央行率先降息,5月瑞典央行跟随降息,6月加拿大央行和欧央行也启动了降息进程。这意味着美联储晚降息、少降息就等于有加息的效果。而如果今年底的大选中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其对外贸易政策可能进一步扰乱全球供应链、提高未来预期的通胀水平,其国内经济政策可能导致2025年至2026年期间美国迎来新一轮总需求扩大、经济扩张和物价上行,这也可能加剧资本流入和美元强势。
最后,历史上来看,美联储降息与美元贬值之间没有必然联系。1980年代以来美联储有七轮降息周期。观察这七次降息启动之后半年内的情况可以发现,两轮降息后美元指数甚至仍然出现了显著升值(1995年和1998年),仅有两轮降息后美元指数出现显著贬值,另外三轮降息后美元指数走势大致持平。
如果把时间延长至首次降息后的三年内,则情况还是比较相似:两次美元指数显著升值(1995年、1998年)、三次美元指数显著贬值、两次美元指数大体稳定。在1990年代,美国处于新经济时期,本轮美元走势也有技术进步的支撑。与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是,当前和未来还伴随着更多的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对于美联储降息能带来美元多大程度的走弱,我们不宜抱有太高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