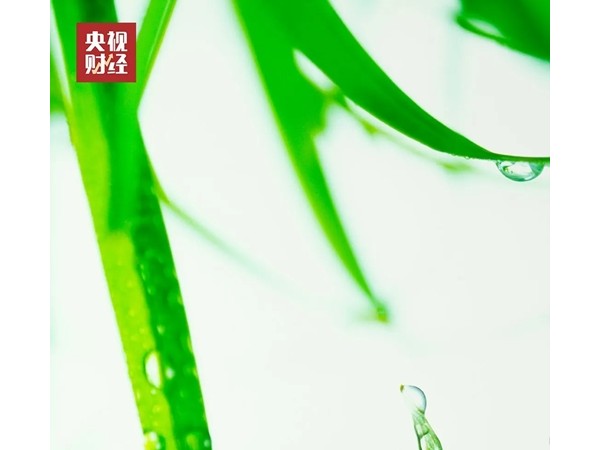我最近去了阿尔巴尼亚旅游,返回英国后,一位00后中国留学生问我:“阿尔巴尼亚?在非洲吧?”
我愣了一下,想了想,若有所悟:“你是不是把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混在一起了?”
他笑了,不好意思地承认:“是的,搞混了。”
说实话,也不能怪他。别说中国的00后了,就是中国的70后、80后,绝大多数也不熟悉这个人口不到300万、面积不到3万平方公里的东南欧弹丸小国。
但在上个世纪60年代,对当时已经与苏联东欧集团彻底决裂的中国来说,阿尔巴尼亚却是中国在欧洲的唯一朋友,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作“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宁死不屈》《海岸风雷》等阿尔巴尼亚电影,曾经在那时的中国风靡一时,中国也曾慷慨地援助这个“既反美帝、又反苏修、更反各国反动派”的自豪国家。
然而,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后,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自认为是“国际共产主义领袖”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却激烈地批判中国搞“修正主义”,导致两国关系降至冰点。中国也因此停止了对阿援助。
在中国打开国门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早已把眼光放到了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不了解、也不关心这个巴尔干小国随后发生的种种变化了。
欧洲的难民输出国
抵达阿尔巴尼亚的第二天,我参加了一个“小巴一日游”,从首都地拉那出发,前往该国的两个风景名胜之地——“千窗之城” 培拉特和最古老的城市都拉斯。
小巴搭载的乘客只有六个人,除了我们一家三个人之外,还有三个美国人。到了培拉特,停下车后,司机兼导游阿尔班知道我来自中国,现在住在英国,便用中文和我打招呼:“你好!”
但他的中文水平也就到此为止,他改用英语和我聊天:“我去过中国多次,是在1997年我们国家金融崩盘之后。我想做点儿贸易,弥补我在那次金融崩盘中损失的钱。但也没有成功。”
“所以,我现在只能干导游了。”阿尔班苦笑着说。他已经过了60岁,但仍然在工作。
金融崩盘?我刚想问他这段历史,却被他的提问抢了先:“你住在英国,在英国的阿尔巴尼亚人特别多,是吧?”
我点了点头。
阿尔班接着说:“他们好像都挣了很多钱,回到阿尔巴尼亚探亲时,都开着奔驰汽车,向亲戚朋友们炫耀着。”
我明白他的言外之意。虽然如今有的中国年轻人甚至不知道阿尔巴尼亚位于哪个大洲,但英国人却非常熟悉这个国家,因为一两年前,阿尔巴尼亚经常登上英国媒体的头条,原因却不太光彩:许多阿尔巴尼亚人乘坐橡皮筏,从法国启航,冒险穿越英吉利海峡,登陆英国,或申请难民,或彻底“黑”下去。
根据英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自从2022年5月以来,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小皮筏偷渡客急剧增多。从2022年5月至9月,短短五个月,阿尔巴尼亚人在所有偷渡英国的船民中的比例便增至42%,人数达到11102人。相比之下,2021年全年,乘坐小皮筏偷渡英国的阿尔巴尼亚人总共为815人。2022年夏季的某几个星期,超过一半偷渡英国的船民来自阿尔巴尼亚。
虽然2024年偷渡英国的阿尔巴尼亚人有所下降,但这都是在英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政府施加强大压力之后才达成的,最近,英国外相卡梅伦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就特别提到了两国在阻止阿尔巴尼亚船民方面的合作。
但偷渡英国的阿尔巴尼亚船民,仅仅是合法和非法移居国外的阿尔巴尼亚移民洪流中的一股小小的支流。
根据阿尔巴尼亚政府自己的说法,阿尔巴尼亚人移居海外已有很久的历史,但在1945年至1990年之间,即该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时期,移民现象几乎完全消失。自从1990年7月以来,阿尔巴尼亚重新出现移民潮。在过去20年,阿尔巴尼亚总人口的大约25%移居了海外。也就是说,在2004年至2024年期间,每四个阿尔巴尼亚人中,就有一人移民海外。
1989年至1991年,欧洲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转型为市场经济和选举政治,阿尔巴尼亚是最后一个转型的国家。至少就阿尔巴尼亚现代史而言,移民潮起伏与该国历史变迁密切相关。
阿尔巴尼亚欧洲和外国事务部引用统计数据指出,目前大约有140万阿尔巴尼亚公民在国外生活和工作,其中大部分(约70-75%)居住在希腊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希腊最多,意大利次之,其余则住在德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注意,这140万人指的是“阿尔巴尼亚公民”,不包括那些早已在移居国归化入籍的阿尔巴尼亚裔人,考虑到目前居住在该国的人口为280万左右,这意味着,大约三分之一的阿尔巴尼亚公民实际上是“在国外生活和工作”。
名为“巴尔干晴雨表”(Balkan Barometer)的民意调查机构曾经在2023年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83%的阿尔巴尼亚公民希望离开自己的祖国,移居国外。
在所有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向富裕国家移民的现象并不罕见,但没有一个国家有如此大比例的国民移居海外。还有一个重要区别:欧盟实行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许多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外流高潮都是在加入欧盟之后出现的,属于合法流动;而阿尔巴尼亚一直未能加入欧盟,该国向外流出的移民,有很大一部分是非法移民,如前述的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乘坐橡皮筏跨越英吉利海峡的船民。
在种种限制的情况下,仍有如此大比例的国民冒险移民海外,这就是亟需解释的一大现象了:在所有转型的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中,阿尔巴尼亚为什么混得这么惨?为什么这个既敢反美、又敢反苏、更敢反华的“山鹰之国”,如今却混成了欧洲的难民输出国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简言之:阿尔巴尼亚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坎坷的转型之路
在离开阿尔巴尼亚的前一天,我又参加了从首都地拉那出发、驶往斯库台和克鲁亚观光的“一日游”。这次我很幸运,司机兼导游西雷驾驶的那辆日本丰田牌汽车上,只有我们一家三个人。
斯库台是阿尔巴尼亚北部的历史名城,克鲁亚是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领导人民反抗土耳其侵略者的斗争中心,两个城市都有很悠久、很丰富的历史。三地相距较远,车行时间较长。尽管阿尔巴尼亚比较贫穷,但它依山傍海,风光奇美。我一边观赏着车窗外的景色,一边听着西雷滔滔不绝的导游解说。西雷是一个30岁出头的青年人,虽然年轻,却是一个“历史迷”,英语极好,又特别健谈,一路向我们介绍该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历史。
“我的中学同班同学都移民了,只有我一个人留了下来,”西雷说完了历史,开始讲他自己,“他们回家探亲时,开着奔驰车,讥笑我买了一个日本车。确实,我是一个异类。我服务的游客也问我,你们国家那么穷,为什么公路上跑着这么多的奔驰车?他们不知道,很多阿尔巴尼亚家庭都有孩子在国外打工,寄钱回家,没有孩子在国外的家庭,为了不丢面子,也花钱买二手、三手的奔驰车。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是很爱攀比的。但我不在乎面子,我只考虑实用……”
突然,车剧烈地颠簸了一下,打断了他的话。原来,他只顾着说话,没注意路上的一个坑。此时,车行驶在农村地区,道路坑坑洼洼的。
“我爸爸也是靠开车养家糊口的,”车过了坑,西雷接着说下去,“他开出租车。他给我说过一个故事。1997年,那时我还小,他开出租车,也遇到了这么一个坑,但比这个大得多,车颠簸得太厉害,他停下车检查,忽然发现前面有两群人互相冲突,都开了枪。他吓得调转了方向。后来才知道,我们国家的军火库被抢了,大量的武器流落民间,流落到互相对立的政治派别手中,甚至流落到犯罪黑帮手中。”
“啊?你们国家在1997年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惊讶地说。
“是的,确实发生过,”西雷缓缓地说,“可能是我做导游的原因,我比较喜欢研究历史。当时听了爸爸的讲述,我也很吃惊。后来我成年了,就上网查了很多资料,才知道1997年我们国家发生了可怕的金融崩盘,也就是融资骗局,老百姓多年的存款被洗劫一空,导致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军火库被抢,内战爆发,最后不得不让联合国派驻维持和平部队恢复秩序。那一年发生的事情对后来我们国家的发展影响很大。”
坦率地说,虽然我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但我也是此时才第一次听说这种事。也许当时是因为这个国家太小,此事“不值得”登上国际新闻的头条?也许是因为毗邻的南斯拉夫正在发生惊天动地的内战,抢走了各大国际媒体的注意力?
回到英国后,我也上网查了查,才知道,无论谁谈到阿尔巴尼亚为什么会成为欧洲的“失败国家”,都避不开1997年所发生的那次金融崩盘。
1992年,阿尔巴尼亚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一些公司和个人以贸易实业公司或慈善基金会的名义注册,利用人们渴望通过捷径迅速发财的心理,以高利率为诱饵,从事“金字塔式”的集资活动,他们付给储户的高额利息并非来自投资所得利润,而是用后来储户的存款垫付前者的利息。这些公司为争夺储户而竞相提高存款利率,有些公司的利息甚至高达70%至100%。
当时执政的民主党政府居然批准了这种高息吸储行为,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国有银行的“空白”,促进资金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甚至觉得这也是市场行为,既然搞自由市场,政府就不能干涉市场。由于政府的支持,这类假集资机构在全国普遍设立储蓄点,吸引了该国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参与集资活动,总存款额几乎占当时阿尔巴尼亚 GDP(国内生产总值) 的一半。
1997年初,一些金字塔集资公司宣告破产,许多百姓毕生的积蓄化为乌有。随后的发展,就像导游西雷所说,金融崩盘,经济混乱,民众抗议,局势失控,军火被抢,内战爆发,政府倒台,联合国介入。
然而,1997年距今毕竟已经27年了,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惨烈的战争,许多国家战后的复兴和繁荣都没有花那么长的时间。那么,为什么其他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相对成功,而阿尔巴尼亚的转型却失败了?究竟是什么原因拖累了阿尔巴尼亚后来的经济发展,让这辆行驶在经济转型之路上的“巨车”,仍然未能彻底爬出1997年掉进去的那个“深坑”?
“人人都想离开这个国家”
“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国家什么都生产。在今天,我们什么都进口。”在俯瞰杜拉斯海港的小山上,阿尔班对我和那三个美国游客说。
已经谢顶的阿尔班,仍然记得霍查统治时的生活。海港停泊的集装箱货轮,大概装载着他说的各类进口品。
“如今我们唯一的出口品,就是劳动力,有技能的劳动力、年轻的劳动力。” 阿尔班感慨地说,“如今海港的工作人员多数都是中老年人,我们这个行业也一样,多数导游都是像我这个岁数的人。在我们国家,许多行业的月薪只有400元,而到国外打工,收入是国内工资的10倍,你怎么能够在国内找到年轻雇员?”
据报道,在几乎所有冒险偷渡英国的阿尔巴尼亚船民的家乡——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人均每月收入只有270欧元。
由于欧盟奉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原则,许多加入欧盟的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入盟初期也出现了大量人才流失的问题,例如波兰,就有大量的年轻人涌入当时还是欧盟成员国的英国。但移民增多,引发了两个方向的趋势:一方面,移民输出国大量年轻人出走;另一方面,移民输入国反移民情绪上升。英国退欧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本土居民对东欧移民的排斥。但随着移民输出国经济状况的改善和外出劳工汇款的贡献,有些国家渐渐走上良性循环之路:经济跃上一个台阶,对外移民开始减少。
然而,阿尔巴尼亚却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泥沼——经济状况没有明显的改善,合法和非法的外向移民形成狂潮,占据了整个人口中非常大的比例。
专家们普遍认为,阿尔巴尼亚迟迟未能成功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加入欧盟的时间不断被推迟也使外国投资因此大幅增加的希望落空,这两个因素都加剧了人才外流现象。
此外,许多远走他乡的阿尔巴尼亚人谈到自己的移民原因,除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之外,还有一个考虑:逃离该国无处不在的腐败。
阿尔巴尼亚移民问题专家、地拉那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伊利尔·格德什表示,该国北部山区年轻人偷渡英国,背后的原因是贫穷和绝望,而促使首都地拉那许多大学生毕业后就移民的因素,则是厌恶本国的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
曾经担任阿尔巴尼亚国会议员的该国著名学者罗密欧·古拉库奇持有同样的看法:“我的祖国的治理方式、傲慢、不平等、腐败、法治失控、企业发展和外国投资都缺乏保障,这些因素都加剧了社会的萧条。”
爱尔兰记者梅兰妮·麦克唐纳认为,考虑到阿尔巴尼亚目前缺乏法治、政府腐败、人民对变化不抱希望等情况,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国家”。
今年1月30日透明国际公布的最新全球清廉指数显示,阿尔巴尼亚得分只有37分,排名第98位,低于许多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该指数根据公共部门腐败程度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名,评分范围为0(高度腐败)到100(非常廉洁)。
人到中年的阿尔塔·乔吉会讲三门外语,拥有三个学位,却在地拉那一家医生诊所做临时医生,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腐败在我们国家就像癌症。你如果想在公共部门找到工作,就必须承诺给管事的政客带来1500张选票。我不是在开玩笑,他们有专人负责统计你带来的选票。”
“人人都想离开这个国家。” 乔吉说。乔吉后来移民到了美国。
阿尔巴尼亚著名财经杂志《监测》(Monitor)主编奥内拉·利佩里说:“一段时间以来,阿尔巴尼亚的企业家们一直抱怨说找不到员工。现在他们则抱怨说找不到买家。”利佩里的言下之意就是:如今连企业家们也打算移民了。
大规模的人才外流,既是一个国家贫穷的结果,也是这个国家贫穷的原因。两者互为因果。
超过健康比例的大规模外向移民,本身就是对本国经济的一大“诅咒”:如果一个国家最优秀、最有才能的人都远走他国,如果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也都走光了,那么,你怎么还能想象这个国家会有未来?
如果假以时日……
“说句实话,我也想过移民,”导游西雷承认,“我都办好了去德国的工作签证。但我一个特别要好的中学同学在一家旅游公司做导游,要去意大利,临走之前问我,他空下来的职位,我想不想做。最初我不想做,但我爸爸劝我试试。他不想让我出国,因为我是独子。就这样,我留了下来。不过,我是一个异类。”他又重复了“异类”这个词。
“你那么喜欢历史,那你觉得,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是转型前好,还是转型后好?”我问他。
西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觉得,还是转型后好。我出生在1991年,不知道转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我喜欢历史,看了很多书,我爸爸也经常给我讲霍查统治时期的生活。那时,我们的生活远远比今天穷,而且专制、枯燥、封闭、与世隔绝。人们不是不想移民,而是没有任何渠道移民,偷渡国境在当时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
“那为什么转型30多年后,阿尔巴尼亚还是那么穷呢?”我问。
西雷迟疑地说:“那是因为转型并不成功。而且,像阿尔巴尼亚这样的贫穷小国,国门一旦打开,就没有任何竞争优势了。”
确实,这也是所有贫穷小国所共同面临的困境:打开国门,人都流走了,相对贫穷;关闭国门,人是留下了,但绝对贫穷;决定相对贫穷和绝对贫穷的因素,就是外出打工仔的汇款;听上去,很是可怜、残酷,但这就是现实,冷冰冰的现实。
一般而言,能够走出这种困境的穷国,通常都是那些拥有自然资源或人力资源的规模较大的国家。
我们结束了在克鲁亚的游览,开始返回首都地拉那。回程中,西雷突然问我:“你见多识广,你说,历史上有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既无自然资源、人口又少的贫穷小国逆袭,最终成为富国的先例?”
我想了想说:“有,新加坡就是一个例子。”
听到我的回复,西雷最初眼神亮了一下,但很快就又暗了下来:“新加坡的经验,我们很难学。”
我也一时找不到话说。
我们静静地行驶了一段路程。西雷又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斯洛文尼亚比新加坡更适合让我们学习。”
我没有去过斯洛文尼亚,也不了解这个国家。回到英国后,我上网查了查,维基百科关于这个国家的词条是这么写的:“斯洛文尼亚是一个发达国家,是最早符合加入欧盟资格的前南斯拉夫地区国家,人均GDP为欧盟27国平均水准的88%,在东欧经济转型国家当中人均GDP名列第一。2007年1月加入欧元区,斯洛文尼亚使用欧元作为法定货币。2010年开始,斯洛文尼亚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也就是说,斯洛文尼亚如今已是富国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虽然斯洛文尼亚有许多不同于阿尔巴尼亚的地方,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斯洛文尼亚曾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期,斯洛文尼亚也是南斯拉夫联邦经济最发达的成员。但比起新加坡,斯洛文尼亚与阿尔巴尼亚更为相像:两国都是欧洲国家;两国都很小,人口和面积相差无几;两国都位于曾经的“欧洲火药桶”——巴尔干半岛;两国都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基本上在同一个时期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
西雷的感觉是对的:斯洛文尼亚能成,如果假以时日,为什么阿尔巴尼亚就不能成?
也许,西雷最终决定留在阿尔巴尼亚,并不仅仅因为父亲的劝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