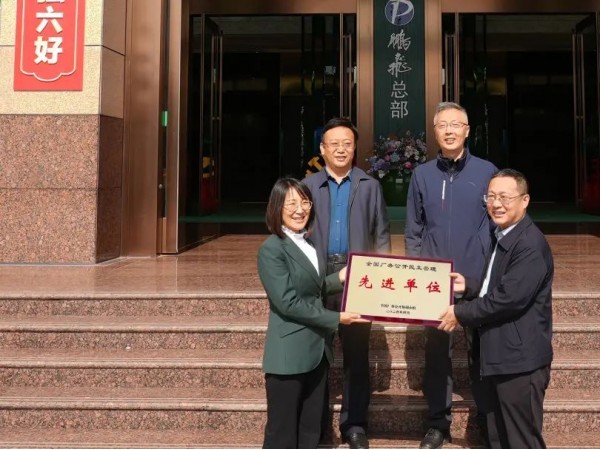过去一年里,“全球南方”成为一个冉冉升起的政治热词。面对美西方构建的不公平国际秩序,全球南方国家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强调重新构建新的国际秩序。
在观察者网联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推出的2023答案年终秀上,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提出了“南方中之北方”和“北方中之南方”,这也许是我们今天回应“基于规则的秩序”最好的答案。
范勇鹏:
大家好。非常高兴又一次在“答案”年终秀和大家见面,感谢观察者网的组织和邀请。我今天的题目是《全球南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我主要是研究政治制度,已经很多年没有专门研究国际关系了,所以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也是一个命题作文,请大家打分。
第一点我要谈的就是世界秩序和知识生产。这几年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越来越暴露出它粗糙和残酷的一面,其实这才是世界秩序的本相。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度以为这个世界秩序是公正的、和谐的、有规则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认知?有很多原因:
首先,国家成功保护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用去面对那个粗糙和残酷的世界。第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战略选择使我们得到了相对较多的收益,解决了一部分的挑战和问题,当然也会冒出新的挑战和问题。第三就是我要讲的知识生产,即二战后西方主导的整套知识生产模式,它给我们提供了一套东西,但不是为了让我们来真正理解世界,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容易接受这个世界。
说白了,就是在这个粗糙的表面上,其实有一个涂层,主要的堡垒就是人文社会科学,比如传媒、文艺产业,成功驯化掉各个社会里一部分愿意思考的、有闲的,甚至一部分比较聪明的人。所以我们在大学里会遇到那种炫技式的学科教育,前几天我还看到一句话,说现在很多学术论文是用高斯都看不懂的模型,得出一个村长看了都摇头的结论。
这样一种知识生产维持了很长时间,但是当它和常识严重背离时,我们自然会产生质疑。所以当原有的国际体系开始转型时,最先剥落的就是外表的涂层。从特朗普当选,从西方社交媒体的兴起,从俄乌冲突到巴以冲突,从萝莉岛名单再到纽约的犹太人教堂,我们发现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认为确定不移的那些知识和事实,现在都站不住了,都在崩解。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中国。我们中国的人文社科知识界,其实还没有完全跟得上世界转变的大潮。
今天我们认识到的世界秩序,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这样一种知识生产的透镜观察到的。所以过去我们曾经认为主权国家、国际法、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体制以及自由贸易等等一系列的国际机制,是一套比较有效的、公平的、运行顺畅的体制。但是现在它出问题了,我们发现这个曾经被标榜为普遍性的世界秩序既无效又不公正,甚至有非常残酷甚至邪恶的一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这个世界秩序还能不能维系?
从地理-制度的视角来思考,为什么今天的世界秩序是这样子的?我用了两个类型,一个是陆地,一个是海洋。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陆地是不均匀的,有高山、有河流,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介质,还是一个治理对象,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仅仅拿它作为一个工具,忘记了陆地上还有人民。而海洋的重要特点是相对更均匀,更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介质,而不是治理的对象。
所以从这两点出发,第一种秩序叫陆地型秩序,这也是过去三五千年亚欧大陆上最主要的文明发展形式,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我们广土巨族形成的过程,就是从陕西、四川、山西、河南、山东、河北这几个版块开始,互相竞争、迭代、演化,逐渐产生出一种我们称之为“天下”的世界秩序。
这样一种世界秩序是在陆地上发生的,首先必须要用制度和人文的创设来扶平这个不均匀的土地。所以我们古代有个词叫“体国经野”,出自《周礼》,泛指创建和治理国家,《尚书·禹贡》也是对这种治理的理想化描述。第二,它要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容纳进来,变成一个共同体,所以我们古代有个词叫“编户齐民”,就是把地和民都能够纳入到这个体系里来。第三,这么多人一起生活,不可能长期处于歧视、压迫、不平等之下,所以最后会产生出一种共同的愿景:天下为公。第四,我们的制度在伦理和功能上都强调治国理政。所以简单来讲,在陆地上形成的这样一种文明、一种秩序,它有很强的治理导向,是人在治理自己的共同体。
那么海洋性秩序是不是这样子呢?很明显,它跟我们有很大的区别。
柏拉图讲过一句话,他说希腊世界地中海周围国家就像一个池塘边上卧着的一圈青蛙,每个青蛙都在呱呱叫,只和自己相邻的青蛙比较容易连接,也就是小世界网络。
什么叫文明?什么叫世界秩序?文明就是内部联系超过了对外联系。所以像地中海这样的世界,就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文明圈,因为彼此之间的联络成本非常高,中间有浩瀚的大海,虽然是均质的,但是在那个时代还突破不了。
小世界网络理论还提到,如果在中间随机拉几条线,就会大大降低各个顶点之间的距离,再往后就会出现枢纽节点,就是超级连接。我们在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体验,比如在我们的朋友同学圈里,总会有那么几个社牛朋友,所有人他都认识,所有事情找他都好使,就是类似于一个枢纽节点。这种枢纽节点的出现,会让这个小世界网络迅速变成一个内部连接非常紧密的体系。
我们看欧洲地图,希腊或者罗马就非常具备成为这样一个枢纽节点的位置。中国为什么叫中国?因为我们强调天下之中。但是地中海没有天下之中,而是在海里,地中海中的意大利半岛就承担了这个功能。这样一种地理结构上产生的文明,自然会呈现出几个特点:
第一,等级化的帝国结构,它不是像河南、山西、四川这样形成板块的结合,而是以一个中心辐射开来形成一个伞状结构,所以它很容易形成一种中心和边缘的结构。第二,正是因为这种中心和边缘结构,所以同民族以及不同民族之间自然会形成不平等的结构。第三,资源和权力信息的流动也主要呈现出一种单向特征。所以总结起来,它大体上是一个点和线构成的体系。而且地中海文明在近代之前很少深入内陆,缺乏地区的整合和治理的需要。
罗马帝国是这样,英帝国、美帝国也都具有类似的特征。这是一张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海洋图,美国的位置就像地中海里的意大利,克里米亚半岛、中南半岛,某种程度上也具有这样的特征。所以这两种文明代表了两种普遍性,而随着西方在现代的崛起,西方文明也从一种地方性文明变成了表象上的普遍性文明。
但西方文明的普遍性表象掩盖了特殊性和地方性本质,实际上在大多数时间里,亚欧大陆上产生的陆地性文明更具有普遍性。2013年新加坡历史学家王赓武指出:西方的胜利是通过海洋秩序打败陆地秩序,英国把欧陆国家牢牢锁在陆地,美国把苏联限制在陆地,而实现的。他认为“中国素有大陆性实力,现在又有了发展海军的能力。……中国将成为拥有强大陆地支持的海军力量的另一个大国。”而在2013年,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
接下来我想讲一讲全球南方的崛起与世界新秩序。我想大家都会同意,今天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等级制下的世界秩序并不是我们需要的,全球南方就是这样一个体系的产物。其实旧知识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非常乏力的。比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去年11月份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全球南方在政治上是一个伪概念,在事实上并不成立——其实西方人特别擅长在自己回答不了时就否定这个概念,否定这个问题。约瑟夫·奈代表的就是旧知识体系对新的世界变化做出的一种掩耳盗铃式的拒斥,一种无能的拒斥。最近这两天特别火的阿根廷新任总统米莱,我感觉他有可能就是旧知识最后回光返照的代表人物。
我也接触了很多左翼人士,包括南方国家的很多学者与专业人士,他们对旧体系的批判非常深入,理论上也非常精致繁琐,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他们批判的很有力,但是对未来却没有提出很好的想法。为什么?因为面对未来需要的不是理论,而是实践。
而在过去这些年里,是谁在实践呢?我觉得主要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实践。比如一带,实际上是延续了我们历史上通过制度和人文来扶平陆地结构的非均匀性,再通过基础设施重建起陆地型治理秩序。当我们这个秩序到达哪里,那个地方的教派冲突、民族冲突、种族屠杀等等,就会被我们的方式化解掉。
在一路,即使从海洋秩序来讲,我刚才提及的地中海历史也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小小角落。在历史上中国也构建起了庞大的海洋贸易网络,从中国的南海一直到印度洋甚至红海地区。美国学者贡德·弗兰克说过一句话:所谓西方文明只是偶然加入到了亚洲的港角贸易——港口到港口之间的近海贸易——然后拿到了一张三等票,通过这张三等票最后上升到头等舱,最后变成了驾驶员,然后才建立起了现代世界体系。
我们通过对海洋秩序这种仅仅基于点和线构成的等级制结构的改造,把海和陆重新融合起来,形成一种海陆兼具的人类未来秩序,目标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怎么做呢?我们的方法论,总结起来就两句话:南方中之北方和北方中之南方。我们要团结全球南方国家,改变这个旧秩序。但是这个改变过程不是为破而破,而是要构建出新的发展样板,甚至我们要在南方国家里边带出一些“兄弟”,我们的公共产品能够覆盖它,甚至我们的军事力量能够保护它,在南方世界中构建出新的发达板块,也就是带引号的“北方”。
那么,什么是北方中之南方呢?今天的北方并不是铁板一块,北方国家集团里有接近南方国家的一些国家,发达国家内部也有类似于南方的阶层和人口。未来的全球秩序必须是包容性的,能够把这些人们团结起来,带动大家共同构一个新的全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