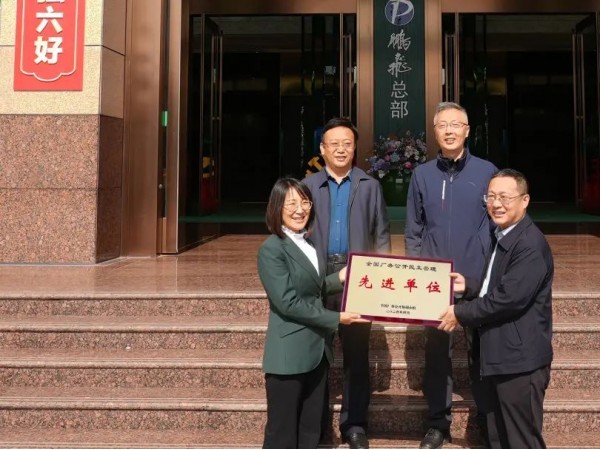口述:肖本良 文:周于江
前年四月份,我从县农业农村局长的位子上退休,过起了清静悠闲的日子,像大多数老年人一样,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无法治愈的失眠成了大问题。
睡不着,就肯定思想一些问题,到了这个年龄,对以后的事情倒是思谋不多,说句实话,在来日并不方长的日子里,就是吃好喝好玩好,该管的不管,该问的不问,该说的不说,生活中尽量去做减法,心情愉悦的过好每一天也就是了。
可对以前的事情总是念念不忘无法释怀,每晚躺下后,过往的事情总缠绕于胸,几乎每晚,都把从前的所作所为在脑子里过一遍。
其实真也没有什么值得回味的,自己是个平庸的人,也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只是好在父母赋予了一个不算太愚钝的大脑,在八十年代初好歹考上了个中专,在时代大潮的挟裹下,随波逐流,热桌子冷板凳地熬到一个正科级的芝麻官。
庆幸的是没有迷失自我,做的事情无愧于心,从不敢越雷池,谨小慎微的躲过了晚节陷阱,从容不迫的完成了从官到民的平安转身。
回望这几十年的仕途宦海,唯一让我感到遗憾失落,心里无法平衡的是,我退休后去年为村里做的一次公益,虽我竭尽了全力,可结局是出财出力不讨好,还得罪了村干部挨了村民的辱骂,这不能不说是我人生中的最大败笔。
去年的八月二十九日,我突然接到了退休多年的原副县长,与我同村同宗的肖本义大哥的一个电话,内容是有事找我商量,请到他家一趟。
一踏进肖本义大哥家的门,见到我们村的支书,本义的五服族侄在座,我与他握手寒暄之后,又问了几天前一场特大暴雨,村里的受灾情况。
没等村支书回答,本义一脸抑郁地插话说:本良啊,这场暴雨可苦了老家人了,村北的丹河桥冲垮了,村民去种河北面的大棚蔬菜,要转十几里过桥呢。”听罢,我心里也不安起来,我知道村里这座桥的重要性,它的冲毁会严重影响到村民的生产生活的。
我们是一个近千口人的大村,村北的小丹河把村里的土地的一分为二,河北土地平坦肥沃,水浇条件好,全部是经济效益高的蔬菜大棚,河南则是贫瘠的山岭薄田,村民们只种些粮食作物。桥没了,村民不但无法过桥劳作,恐怕他们的蔬菜也会烂在地里销售不出去。
想到这里我急忙说:“村里赶紧修桥是当务之急呀。”这时本义哥用手指了指村支书又说:“是啊,这不他就是为这事来的,修桥村里没钱,想让村里在县城的人集些资。”他又转过脸对村支书说:“你快跟你本良叔说说村里的打算。”
支书就把村里准备花几十万,再建一个简易的滚水桥,筹资方式是村民集一点,在外工作有能力的捐一点的计划全盘托出。我对村支书说:“咱村在外有能力的人多,这事应该没问题。”
做沉思状的本义对我的话不置可否,转脸对支书道:“今年遭了灾,村民肯定日子不好过,你回去后最好先不要集资。因口罩的事不能聚集,待我俩分别做做县城里人的工作,视筹资情况再定。我心领神会到这是本义哥另有打算还留有余地。
村支书走后,本义大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了下面一段话:“本良啊,出来这么多年,没给家乡干一点像样的事,我心里惭愧呀,到了生命的最后,我想给老家里的人留下些印记,也不枉此生啊。老家的这座桥从我记事起,冲毁了不下四五次,我想这次咱们在外的人努努力,为家乡建座抗御百年洪水一遇的钢梁大桥,不知是否能达成啊,建这样的桥起码要几百万哪。最好不要村里人集资了,这里边的道道你懂得。”
本义大哥长吁了一口气又说:“也不知人们是否寒了心,还愿不愿意付出啊。”对他最后这几句话我是心知肚明的。
2016年,为村村通工程,前任村支书也来县城筹资,大家踊跃捐献,结果除工程项目账目混乱,才两三年修的路,就坑坑洼洼,不成样子,大家当然明白钱进了什么人的腰包。
本义哥是清正廉明的好官,要不是因为身体原因,他很有可能再进一步。在他任前任后,在不违法不犯纪律的范围内不知帮助了多少人。
我们村一个早年的小包工头,因其老婆患了胃癌手术后,欠医药费太多被中止了治疗,这人哭着找到他后,本义马上赶到医院,由他作保,先治病救人后付费用。现在这人已是县城最大建筑公司的董事长。
还有一个开化工厂的,因与环保局的人关系弄僵,被强制停产了三个月损失巨大,也是由他出面协调,后来环保达标迅速开了工。
一个身有残疾的村里孤儿,被他弄来县城学了厨师,现在已是三家大酒店的老板,这些人都早已是身价过亿的人士,对本义哥都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包括我也是工作之后,本义哥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做官,怎样处理上下级关系,怎样避免贪腐的陷阱,一路呵护才有了我的今天。
有多年领导经验的本义大哥,对这次为家乡建桥的推进程序当然是有条不紊的,他先是让我用车载着他,拖着一条病腿,气喘吁吁(他有老慢支)地跑主管部门,桥梁设计勘察部门,造价评估机构,最后定型为一个造价三百万元,永久钢梁大桥。
然后开始进入关键的筹资运作。本身我俩考虑,因口罩原因经济不景气,加上村里修路筹款时的不快,弄这么大笔资金会有很大困难的,没想到本义哥一发话,出奇的顺利。
他首先拿出了他的全部五十万存款,当我让他留一些以备不时之需时,他轻轻摆摆手道:“留它干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每月有工资,生病治疗免费,孩子都能自食其力,这钱用在这里是最恰当的。”
我受他感染,也力所能及地献出了二十万,有三个老板也慷慨捐献每人三十万,十万的也有好几位,五万、二万、一万、五千的若干,五六天之内就完成了三百万建桥款的筹措。这不能不归功于本义哥的人格魅力,不能不归功于他榜样的力量。
缜密又周全的本义哥,在优中选优了一个路桥公司,和一家质优的监理公司全程监理工程外,还在捐款者中选出一名搞过工程,一名懂财务的人员,还聘请了镇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和我们村的书记(遭拒绝)加上我组成五人工程质量财务监管小组,以我为组长协调一切。
在这一切的运作期间,村书记还给本义哥打过电话说,他正准备发动群众集资,让我们筹到的资金转到他的账号上。我与本义哥相视会意的一笑,算是做了回答。
当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准备开工时,把一切情况通知了书记,他不但恼怒地拒绝了加入监管小组,还莫名其妙地挂断了电话,其中端倪深不可测。作为体制内的我与本义哥自是再明白不过。
修桥开工后遇到了无数的麻烦,先是大型工程设备开进时,将村里的几棵绿化树刮倒,村文书出来拦住车辆进行敲诈,每ke棵树索赔偿一万,在苦口婆心劝说无效情况下报警处理。
工程需一块空地,搭建工人住的帐蓬,大型工程设备的存放,及所需水泥、钢筋、石料的储存,本是占用河边一块荒芜的沙滩,可村支书的的堂兄,却硬说这是他的承包地,坚决不许存放物资,此时村支书电话不通,人也找不到,我只有找了镇上的一把手才得以解决。
原来,他是村里的建筑头,本设想村里集资修桥,把工程包给他,也能从中分一杯羹,现在他看到这样的结果自然就怀恨在心,有意出来捣乱。
还有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还专门过来盗水泥、钢筋等筑桥材料,有人要报警被我制止,我实在不愿看到这些本村的老人,被警察执法的不适场面。
更让我憋屈的是,后来还传来村里人说,我们这是一帮贪官钱贪得花不了怕遭报应,才来做善事的,有的还说贪了钱怕出事,专门来洗钱的。对于这些村里人的恶行恶言,我始终没有告诉已病倒在医院的本义哥,怕他
生气加重病情。只是自己忿忿不平地责问自己,这不是扒着眼照镜子自找难看,自取其辱吗?自己劳心劳力破财却得来这样的结果,实在让我难以接受,当了几十年的干部,也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想想真让人寒心啊。
好在经过了一段难熬的凄风苦雨,总算高质量地把桥修了起来,早就焦头烂额的我,连镇上搞的通车庆典也未参加,回家县城家中睡了一天一夜才算恢复了元气。
来到医院看到本义大哥的肺气肿老毛病已好的差不多,实在憋不住的我,便把发生的一切,全盘抖落了出来。其实,大哥可能早就知道了一切,他微笑着对我说:“这些应早就预料到了吧,我知道一个在官场历练这些年的大局长,是能够挺过来的。”
当我又叨叨着,咱哥俩都这么大年纪,这到底是图了什么?本义大哥说:“什么也不图,就图最后给家乡做件实事,做点善事图回报的那是投机那是沽名钓誉。我们要的是能回家或路过,看到村里的老老少少,畅通无阻地通过我们努力建起的这座桥,去地里劳作,去赶集上店就够了。”
“兄弟呀,像我们俩这岁数的人,拿着高额的退休金,享受着各种优惠待遇,而与我们同龄的农民,却只有百多块的养老钱,还得在土里苦苦地刨食,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们对我们这些当官的有些许的怨言了。”
听罢大哥这一番话,我的心里才通畅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