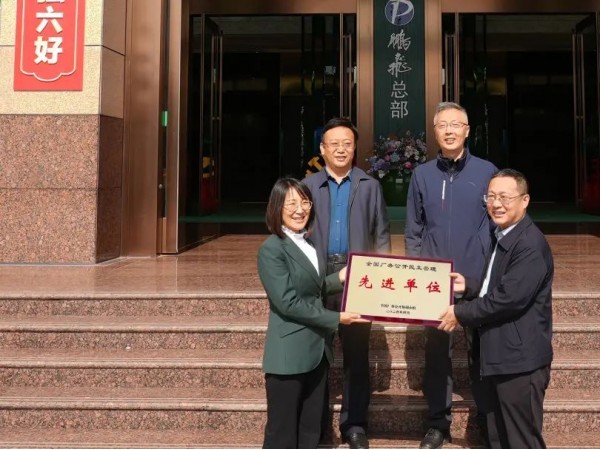当今日本,“一亿总中流”(“中流”意为“中产”——编者)已成为一种令人怀念的说法了。“一亿总中流”曾经有过,至少人们在心底里相信其存在过,如今它已不复存在,也没有人再相信。无论是从生活富足程度还是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看,“一亿总中流”都可以紧密地将各种各样的日本人联系在一起。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亿总中流”已经变成了一种日本社会中的常识。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同样就这一点达成了共识。和美国一样,学者们几乎不再使用表示人们之间存在差距的“阶级”一词。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随之出现了形容这种现象的流行语“格差社会”。其实,从“格差社会”一词回首过往,尽管当时很多人没有发现贫富差距的扩大,但实则存在已久。
最终将人们从“一亿总中流”的幻想中拉回现实的,正是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对不同人群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并不是无差别的。
日本人为何认为自己属于“中流”
日本人相信的确存在过“一亿总中流”的时代。当然,这个时代也存在相当大的社会差距。但是大多数人如果被问到所属社会阶层,都会回答自己属于“中层”。当时的民众对于“日本人的九成是中流”这种说法深信不疑。
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提问方式会诱导人们回答自己属于“中层”。毕竟人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究竟处于“上层”“中层”还是“下层”,没有明确认识。如果被问到属于哪一个阶层,无法明确作答的人比较多。但是,如果一定要从中选择一个,一般人会使用排除法,去掉“上层”和“下层”,选择“中层”。
其次,在号称存在“一亿总中流”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持续十几年之后,实际社会差距变小了。大部分人的收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增加,生活水平达到了过去的“中流”水平。因此,即使说日本社会有“一亿总中流”,也毫无疑问。
再次,人们其实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水平在整个社会中处于何种位置。因为生活变化很大,所以和平时不见面、学历和职业都不同的人相比,无法判断自己的生活水平是高还是低。富人不知道自己比别人富裕,穷人不知道自己比别人贫穷。因此,很多人即使被人说“你处于‘中层’”,也不会有任何疑问。
于是,人们大多把成为“中流”作为人生理想。与古希腊哲学家、鲁滨逊·克鲁索的父亲以及日本近代的思想家一样,人们认为“中”就是好的状态,大部分人处于“中间”位置的社会就是好的社会。因此,“一亿总中流”成为大多数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也被大家欣然接受和认同。
但是在那之后,经济差距持续扩大,进入21世纪后,贫富差距扩大、贫困阶层人数增多这样的事实已无法被继续掩盖。于是,人们开始正确认识自己究竟处于社会中的何种位置。富裕的人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富裕,而贫穷的人也知道自己处于贫困阶层。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人们不再相信“总中流”论。既然人们对贫富差距的认识和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差距扩大的现实面前,再让人们去相信“自己属于中流”几乎不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中流”是理想的状况,能够相信“自己属于中流”的社会只能是理想的社会。但是,如果不改变贫富差距扩大的现状,也就是说不缩小差距、消除贫困,就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
“中流”再生与新“总中流”社会
大多数人能实际感受到自己属于“中流”的社会被称为新“总中流”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社会,究竟怎样做才好?
扩大旧中产阶级的规模以及新中产阶级的范围是可能的。另外,还可以缩小新旧中产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的差距。这样的话,与今天相比会有更多的人成为“中流”,或者切实感受到自身属于“中流”。
具体分两个方面考虑。首先是扩大“中流”的范围。在现代日本,旧中产阶级的减少较为突出,其比例仅为11.8%,共约751万人,而且包含了相当多的个体劳动者。内阁府2019年的调查显示,虽然就业形态显示的是个体经营者,但事实上既没有实际店铺,也没有雇用员工的人,在建筑业达到了40.4万人,批发零售业有21万人,共计达到了200.3万人。这其中也包括学术研究、专业技术服务业、信息通信业等专业性较高的从业者。大部分从事销售、服务业与体力劳动,非正式职工较多。从这点来看,实际上旧中产阶级已经在大幅度减少,估计仅有10%,和1992年相比其实都不到一半。
由于个体经营者的减少,社会失去的东西也开始增多。地方商业街的店铺相继停业,购物开始变得不方便。便捷又价格便宜的小电器店、施工人员等也都逐渐消失了。还有实惠可口、具有季节特点的手工料理店也在消失。与此同时,农田被遗弃,自然景观被破坏的现象可谓层出不穷。事实上,多样化个体经营者的存在对于丰富我们的生活有着重要意义。个体经营部门,具有超越经济效率以及缓和大资本带来巨大压力的社会意义。加大对个体营业者的援助,以及帮助工人阶级自主地向旧中产阶级流动,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因此,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减缓旧中产阶级减少的方式来扩大“中流”的范围。
对于新中产阶级,我们首先希望缩短其劳动时间。长久以来,日本人的拼命加班已成为常态,缩短劳动时间的进程非常缓慢。尽管从统计数据上看劳动时间是缩短了,但实际上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劳动时间是由非正式职工的增加所填补的,真正劳动时间的多少很难正确把握。如果能真的缩短劳动时间,也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新中产阶级的队伍工作。当然,这也是有限度的。
新中产阶级即使在现在,也不是按照自己自由决定的工作方式去工作的,能力和经验也没有完全发挥。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说他们完全调动了工作热情。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更为不自由,处于一种无法从“被边缘的劳动”脱离出来的境况。也正因如此,工人阶级才想升职为管理人员,同时希望子女通过上大学可以晋升为新中产阶级。其实,还可以有别的改善途径,如熊泽诚指出的那样,尝试“改善工人整体的工作条件”,同时加强对工人阶级工作方式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制止劳动简单化,推进能力开发。
其次是尽可能保持“中流”的生活水平。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变为中产阶级。但是,可以尽可能让所有人保持“中流”的生活水平。方法有很多,例如,消除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的工资差距,实现平等待遇原则。同样,男性和女性之间、大学毕业生和非大学毕业生之间也有必要实现平等待遇,还可以通过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来实现收入的增加。如果工资差距缩小,与现状相比收入再分配的必要性就会变小。但是,考虑到股东和部分经营者获得巨额收入的现状,还是有必要进行收入再分配。提高所得税的累进制,通过引入资产税和加大继承税的税率来提高富裕阶层的实际税率等都是有效的做法。
此外,社会保障的作用也很大。新中产阶级的相当一部分随着退休而从“中流”的生活水准中滑落下来。旧中产阶级同样在退休后,大半都无法维持“中流”生活水准。退休后工人阶级的生活更是困难。生活困难的个人和家庭,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补助,但是仍然有很多未被最低生活保障体系覆盖的人群。最低生活保障补助的使用率(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中,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补助的人的比例)仅有20%左右,处于较低水平。当然原因有很多,有行政效率的低下,也有来自周围人对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补助人的看法等。但最大的原因,还是领取该补助的条件过于苛刻,需要满足不能有一个月以上存款的条件。
如今“中流”的使命
那么,为了使“中流”能够再生以及新“总中流”社会得以实现,现在身为“中流”的人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需要明确的是,“中流”的内部绝对不是铁板一块,如今“中流”的内部已明显呈分裂状态。例如,“中流右翼”“中流自由主义派”二者的想法也完全不同。
“中流右翼”并不承认差距扩大的事实,认为贫困是自己的错,这种自我责任论的倾向很强,所以也不会赞同实现新“总中流”社会的目标。他们是阶级社会中的居民,满足于自己在阶级社会中处于相对上层的地位。因此,如果只是呼吁,可以说是徒劳的。
而“中流自由主义派”明确认识到了差距扩大的事实,也认为差距扩大是问题,支持收入再分配政策。他们并不认同排外主义,对少数派表示理解;对于放宽经济限制持批判态度,支持零核电的人也很多。他们是古德纳所说的“批判言论文化”的旗手,是实现新“总中流”社会的中心力量。但是,虽说他们是“中流”中的最大势力,也只不过勉强占了“中流”整体将近一半,其实也很弱。如果不把位于中间位置的“中流保守派”吸纳进来,就很难实现目标。
如果“中流保守派”与“中流自由主义派”联合起来,会是怎样的情况呢?“中流保守派”对自我责任论持否定态度,在不否定政府介入经济这一点上,与“中流自由主义派”是共通的。但是,他们在对收入再分配政策持消极态度这一点上,与“中流自由主义派”的差异很大。他们认为虽然自己不支持自我责任论,但也没有必要特意通过收入再分配来缩小差距,通过增加税金的方式可能并不受人欢迎。
如果想让“中流自由主义派”和“中流保守派”为了实现新“总中流”社会达成共识,恐怕也需要“中流自由主义派”方面的让步。关于收入再分配也可以在双方达成协议的基础上逐步推进。
“中流自由主义派”和“中流保守派”之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区别,但并不是像“中流右翼”和“中流自由主义派”那样,有着极端对立的关系。至少二者对于实现新“总中流”社会这一目标不存在分歧。另外,二者对于政党的支持,也并不是完全对立。以“中流自由主义派”为中心,找到与“中流保守派”的共同点,在这里组建由其他阶级中持有“自由主义派”和“稳健保守派”观点的人构成的政治势力,也绝非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