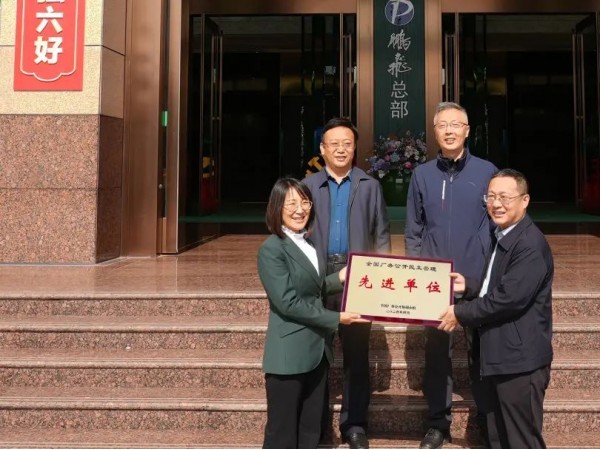安徒生的童话《红魔鞋》,说的是一个夏天里打着赤脚的穷女孩,在接受坚信礼前买了一双艳红的鞋子。当牧师庄严地宣讲上帝的荣耀与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时,她心里想的却全是新买的鞋子。鞋子吸引着众多的目光,并且得到了人们的赞赏:多么漂亮的舞鞋啊,跳起舞来一定很美!经不起别人的赞叹,她跳起舞来,舞姿的优美飘逸让她深感意外。一开始,她还可以脱下鞋子,获得一时的歇息,但那天晚上,她穿上鞋子去参加一个舞会,就完全失去了控制。红色的舞鞋带着她不停地舞蹈,从城内舞到城外,一直舞到黑森林里去。她害怕起来,想脱掉鞋子,却发现鞋已经长到皮肉里去了。红舞鞋就像一只精灵领着她跳向田野、草原和山冈,在雨天、在太阳底下、在黑夜里不停地旋转腾跃。最后,她不得不请求刽子手挥斧将自己的双脚剁掉,而这双鞋子竟带着剁掉的小脚跳向山林深处。
安徒生的这个故事,虽说是一个童话,天方夜谭的事情,却道出了人世间自由的悲剧。卢梭称,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他看到了枷锁的普遍存在,却看不清枷锁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在裴多菲的诗歌里,自由有比生命和爱情更高的价值,但是,我们常常看到,这种价值至高无上的权利轻易断送于各种无意义的事物中。人们总想拥有、支配更多的事物,但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行为服从于物的逻辑,为异己的力量所挟持,甚至把物的意志当成了自己的初衷来执行,以为这就是自由真谛。
唐代诗人贾岛有《剑客》一诗传世,诗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倘若真有剑客用十年的时间磨出一柄锋利无比的剑,最终落个“霜刃未曾试”的结果,会是多大的遗憾啊!剑乃凶器也,其斩钉截铁、见血封喉的锋芒闪现着一种难以掩抑的杀气。在暗室里静静磨砺的人清楚,剑隐藏着嗜血的渴望,流泻着令人战栗的寒光。它是作为夺命追魂的武器被人们锻造出来的,它不能辱没自己的使命,废掉自己的全部武功,它必须扬眉出鞘,履行作为一种凶器的职责,完成自己被锻造时赋予的使命,实现人们对于剑的想象,证明自己不是一片平庸的铁片。它呼唤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时刻,给自己提供横空出世、施展身手的机会。倘若没有,它也会激励、鞭策、怂恿握着它的人去制造。同在一条狭窄的路面上行走,人与人之间难免要发生一些摩擦,这种摩擦可以和风细雨地加以化解,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也可以以牙还牙,不断升级成为一场格斗。在摩擦发生的时候,当事人手中是否持有一把贾岛牌宝剑,结果会大不一样。倘若对立双方两手空空,也许可能拱手相让,井水不犯河水;倘若其中一方怀有一把研磨了十年、刃如霜雪、跃跃欲试的长剑,很难保证不会酿成一场你死我活的惨案。这时候,作案者不是持剑的人,而是人所持的剑,人很难控制它对血腥的饥渴和冲动,人成了被剑左右的傀儡,只是一个帮凶而已。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人们通常羡慕那些身怀绝技的高人,觉得拥有他们神出鬼没的武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武术从来都不是自娱自乐的把戏,它的各种招式都指向想象中的敌人,企图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当一个人把各种致命的绝活儿学到家时,他本人也不知不觉变成了贾岛诗中描述的那把寒光毕露的剑,不甘在幽暗的皮鞘里寂寞地终其一生。他不能将所学的武艺置于一无所用的地步,因为那等于废掉了这些高超的本领,等于自己数十年习武付出的心血全都付诸东流。于是,他的内心有了对不平之事的期待,而期待中的事情最终是要发生的。就这样,他不由自主地进入一个冤冤相报的江湖,杀人并且为人所追杀。整个过程可能看起来都出自他本人的选择,天衣无缝,谁能够看清其中的被迫和无奈?
无独刀剑,各种事物都隐含着特定的功能目标和意志追求,特别是那些被人制造出来的东西,在出身之时就被赋予某种意向。由于初始的目标意向,事物本身处于尚未完成状态,存在着对称性破缺,或者说圆满性破缺,因此,它具有一种自我完成的倾向和属性。当人拥有某种事物并消受它带来的恩惠时,隐蔽在其中的倾向性就附着于人的心灵,给予某种持续的心理暗示。这种暗示在不知不觉中强化起来,并最终偷换人的意志,让人乖乖听命于它的调度和派遣,还以为是来自自己内心的呼唤,以为是一种天职或神秘的天意。就拿资本来说,资本是一种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能够带来利润的成本。不断实现自身价值的增值,使之趋于最大化,是资本本身固有的倾向和追求。资本的这种初始意向使所有拥有它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服从于它的逻辑,不屈不挠地去实现它的渴望,完成它的属性。一个拥有亿万资本的人,如果能够使自己账户里数字的位数增加,他会深感欣慰,觉得自己对得起手中的货币,也实现了自我的价值,有了慰藉感和成就感;反之,倘若账户里资本的数目不断减少,向零的方向运动,他会感到恐慌,痛恨自己,觉得自己有罪,甚至不可饶恕。自2008年开始的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已经导致许多顶级富豪跳楼卧轨,他们为自己不能完成资本赋予的使命而引咎辞命。可见,资本与贾岛的宝剑一样,具有夺命追魂的魔力。资本对剩余价值不可抑制的追逐,与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和经济运行的周期波动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谁都无法保证自己手中的资本任何时候都处在增值状态当中,真是苦了那些资本家,他们的灵魂很难摆脱资本的梦魇。恩格斯说过,少女可以歌唱自己失去的爱情,资本家却不能歌唱自己失去的金钱。
近年,汽车消费成为时尚。看到周围的人纷纷成为有车族,我的邻居,一位大学教师,也买了一辆亮丽的白色轿车。其实,他的生活基本都在校园里完成,需要出车的机会极少。而买一款崭新的车子,搁在那里不用,风吹雨淋日晒,是一种浪费和痛惜,是暴殄天物,况且不经常使用,车辆也会出问题。每天的夜晚与清晨,他都在阳台上默默地注视这辆流线型的坐骑。目光中,洁白的车身保持着向前冲驰的姿态,像一匹白马在厩栏里想象着旷野上的奔腾跨跃。他感到了白马内心有一种深深的压抑,还有作为骑手莫名的愧疚。有时候,他不得不专门抽出时间,驾车到城里漫无目的地转悠。甚至到学校羽毛球馆打球,不过两百米距离,他也要把车开上,将车倒过来倒过去。每年算下来,汽车养护、汽油、停车等费用,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远远超出了租车的花费。而且,由于运动量的减少,他的身上长出了许多赘肉,需要减肥。实际上,他所购买的不是使用权,而是一种拥有权,但到底是他拥有了汽车,还是汽车拥有了他本人,已经很难说得清楚。
刀剑、资本、车辆这些没有血肉灵性的事物尚且如此,那些有血肉灵性的个体隐含的魔性,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春秋时,卫国第十四代君主卫懿公特别喜欢鹤,整天与鹤为伴,以鹤的所好为自己的情愿,鹤所乘坐的车子比大臣的还要豪华。为了养鹤他耗费大量资财,疏于朝政、不问民情,引起臣民的不满。公元前659年,北狄部落侵入国境,卫懿公命军队前去抵抗。将士十分气愤:既然鹤的地位和待遇比我们都好,就让它们去打仗吧!卫懿公没办法,只好亲自带兵出城迎敌,最终战败而死。
卫懿公当年因为迷于玩鹤,把自己和一个国家的命运给玩完了。人们把他的行为称作“玩物丧志”。玩物丧志其实是人在玩物的时候,不小心被物的意志俘虏,反过来为物所玩,断送了自己的意志自由。人们通常以为,把越多的事物揽到自己怀里,或是划归自己名下,是一种显赫的成就。他们陶醉于拥有众多贵重事物的辉煌觉受,却不知,每一种事物都有自身隐秘的倾向,把众多事物收拢到自己怀里,同时也是把众多异己的力量引到自己身上,这些异己的力量会反过来控制人的心灵,使自己更加身不由己。时下,富人、官员包养二奶、小蜜成为时尚,似乎不如此便对不起自己的发迹。他们都想要步袁世凯的后尘。袁世凯拥有三十几房太太,太太之间各有各的性情、心思、欲望,都想排斥别人,从他这里得到更多的宠爱和好处,切割他从外头搬回来的那块大蛋糕。为此,这帮女人时常平白无故生出许多是非曲直来,把后院闹得鸡飞狗跳,让他在料理国家大事之余疲于应付,惹出许多荒唐的笑话来。最后,他不得不用政治手段来治理家庭。
自由通常被定义为人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随心所欲地做出抉择。但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向,而不是另有所往?其中另有深意存焉。在很多时候,人并不清楚自己意志背后的因缘集起。人的内心通常不能在无意向的状态中持续,止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的安详自在,为了避免陷入一种茫然无措和怅然若失的状态、沉溺于散乱昏沉之中,他需要抓住一些东西,一些稻草和藤萝,并通过对稻草和藤萝的抓握来提领心气,获得生活的指望和劲头。倘若抓握不到,心里没着没落,就有一种深渊似的遗弃感,就会生出巨大的恐慌——这是人最原始、最根本的精神强迫症。因为内心强迫的压力,人不能怡然自得地跟自己相处,总想从自己面对的紧张中逃离出去。是故,他们很容易接受暗示和诱惑,被物的意志所召唤和激将,将外在的蛊惑和怂恿当成自己的自由意志。
从自我面对中逃离出来的人们所热烈讨论的,不是要不要抓住什么的问题,而是抓住什么样的事物才是最好的问题。他们要在事物间的差别中来寻找和判别自己生活的意义,度量自己人生的成就。对此,庄子专门写了篇洋洋洒洒的《齐物论》,告诉人们,他们所要追逐和躲避的事物之间的差别,只是一种观念构造而已,这种观念只有在某种褊狭、局促的对待关系中才可能成立,换一种对待或参照系就成为荒谬。因此,抓住什么其实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有人抓住事物的时候被事物抓住了,有人则没有。庄子给人们迷恋追逐的对象袪魅,是想让人能够以平常心对待,从最原始的精神强迫症中解脱出来,与物同作逍遥游,又不为物的意志所缚,并与之沉沦。勘破各种事情的阴谋,保持与事物之间不即不离、亦即亦离的关系,化物而不为其所物化,是庄子的智慧。
物的意志对人的规驯和控制,就像是鬼魅的附体,就像是人中了什么邪气。在巫术中,人们用各种残酷的方法来驱邪。其实,邪魔的源头不在事物,而在于人的内心是否萦怀于事物,陷入由此引发的幻想境界不能自拔。对于人丧失自在的原因,释迦牟尼进行了深邃的追问,形成了十二因缘学说,最终追溯到人的意向:“无明缘行”。小乘罗汉灰心灭志,绝诸缘起,进入寂灭的有余涅槃,以求解脱。大乘菩萨则于缘起之中了悟空性,证取“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色空不二、生死即涅槃的境地。《维摩诘所说经》讲述了古印度毗舍离地方一个叫维摩诘的富翁,他家有万贯资财,过着世俗间富贵荣华的生活,但能够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着境,无为而无不为,于世间出世间,成为大菩萨的典型代表。佛的许多大弟子和菩萨都没有他那么高的修为。
说起来,物的意志如怪力乱神,防不胜防,其实这种神力源自于人的赋予,源自于人内心定力的薄弱。安徒生童话中的那双红舞鞋之所以有如此可怕的魔力,是因为那个穷女孩对它产生了深深的痴迷和无尽的遐想。人的心意若能够从事物之上悄然脱落,豁达开来,不为任何现象所系缚,事物也就无任何意志和邪魅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