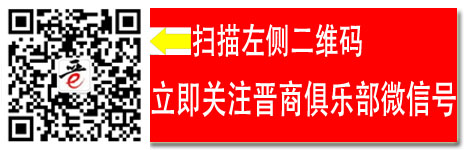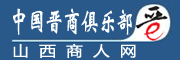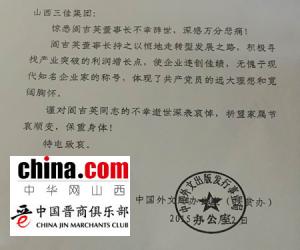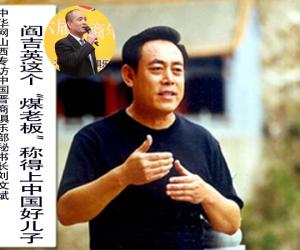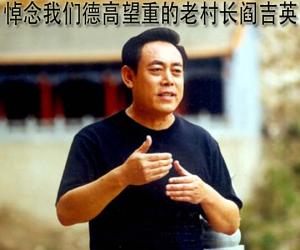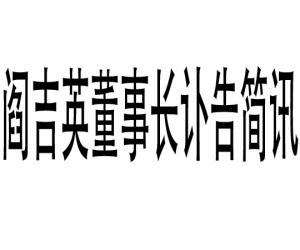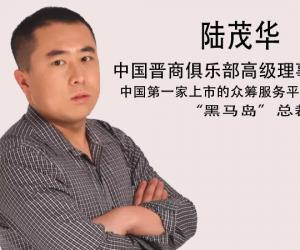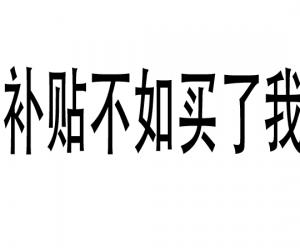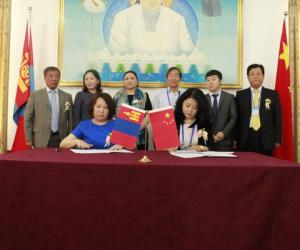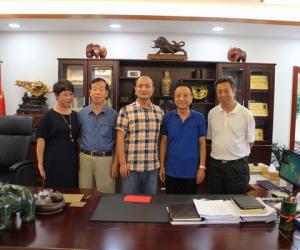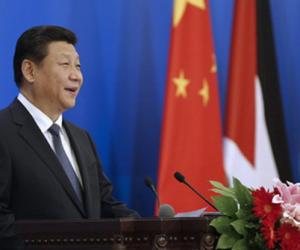碛口听涛
碛,是河中的浅滩。黄河在晋陕峡谷中弯了九十九道弯,在山西临县有一段近500米的暗礁浅滩,叫大同碛,这便是临县碛口镇。
碛口是太原、京、津联系陕、甘、宁、蒙的码头,是东西经济、文化之枢纽,素有“九曲黄河第一镇”之美誉。这便孕育了商机,也就是现在说的物流。据说鼎盛时期,碛口码头每天来往的船只150艘之多,各类服务店肆300多家,人称“水旱码头小都会”,晚上满街都是拨拉算盘的声音。
走在碛口的明清街上,新铺的石板有点硌脚,尽管有游人,静还是出奇的。街道两边的铺子已经凝固了,像标本一样展示过去的商业繁华。砖是明清时期的主要高档建筑材料,用砖实砌做墙一般是大财东;次一点的是表墙,即外砖内土坯;再次的四角砖柱,土坯做墙;最次的就是土窑、茅屋了。在临县这个相对贫瘠的地方,明清街上的人家都是用砖实砌的房子,可见当时的富有。
明清街上石砌的路,是供木轮大车辗压的。咕隆隆,是沉闷的载重大马车的声音;咣当当,是空马车的筛磕声。轮下是压不塌、辗不碎的石板条,算是那时最高档的路了,相当于现在的花岗岩、大理石了。如今我们的脚踏上去,荡不起一点尘土,只有女人的高跟鞋能碰出一点响声,清脆的单调,单调得让人去幻想时髦的女郎。
碛口的胡同是很大气的,叫什么,我忘了名了,大约有九尺宽,要比太原郊区农村的老胡同宽得多,第一眼我就看上它了。胡同两边人家的墙是石砌的,就地取材吧,大概比明清街上铺面建筑要低一个档次。砖是奢侈品,石是土特产。但石砌的墙一样精细,可以看出石是洗过面的,石缝是精心对齐的,这样盖得房子结实、美观、大气,但要耗费许多钱财,是家庭富裕人家才有的建筑。胡同这么宽,大马车不能走,驴车是宽绰有余的,大概当时是为了骡马驮货、卸货方便才留的吧。
碛口明清街上的铺子门面小,也矮。矮大概是面对黄河,面对西北风保暖的需要吧;门面小大概是临河岸边土地紧张的缘故吧,从整体的形象看,碛口是晋商建筑的微缩版。
碛口,已成为一种历史,久远得让本地人都记不清楚;碛口,成为一种建筑标本,让农村长大的孩子足以怀旧。
碛口的静,像一个小山村,寂寞得只剩下黄河;报晓公鸡扯不破碛口的晨,游人荡不起碛口的喧嚣,似乎汽车的喇叭也叫不醒碛口,只有黄河哗啦啦、哗啦啦……
漫步在河滩,黄河冲刷石头的哗啦啦格外清晰,哗啦啦、哗啦啦……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汾河畔的邵城村,稗草、芦草淹没的汾河滩。
童年的汾河是无忧无虑的河,童年的汾河是摸鱼捉虾的河,童年的汾河是孩子们娱乐嬉戏的河。
捧一掬黄河水,浑浊的河水在掌心里慢慢变清,敷在脸上,感到水是柔滑的,有点凉。河水欢畅的,匆匆从脚下的石头间穿过;心是洁净的,深深印着水的柔滑和清凉。好一个笑,从丹田升起在七窍奔放……哈、哈、哈!响彻了我的五脏六腑;感动了给我拍照的亲人朋友。
黄河的涛声不大、不惊、不壮、不凶,滚滚的河心浪不大,也没有鸣;只有河边的水急急得冲撞大大小小的巨石、大石、怪石、小石,发出哗啦啦的响声,衬托这碛口古镇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