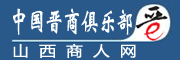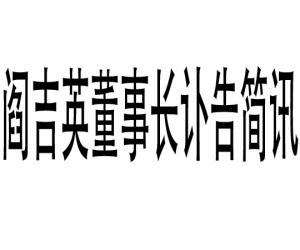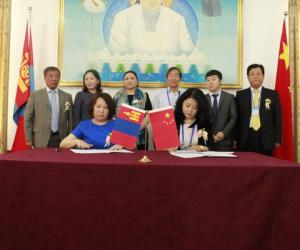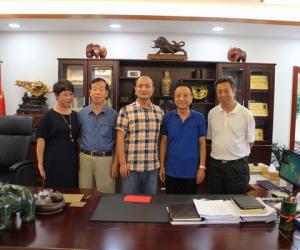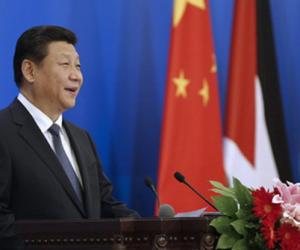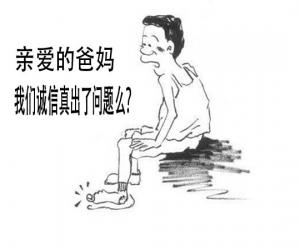晋商大院的别一种文学想象——评毛守仁长篇
山西省作家毛守仁的《北腔》,写的是晋商文化中的女性生存状态。
这部以晋商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
说,没有对晋商的商业活动进行正面展示,作家真正关注的重心,是身处社会边缘的女性,是对晋商命运起伏中极为复杂多变的人性存在的剖析与透视,尤其是对那
些堪称凄绝悲凉的鲜活女性生命的生动再现与由衷赞叹,借助于晋商这一载体将若干女性曲折的生命历程与丰富的精神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
从《北腔》的艺术表现层面来看,最值得注意的成功处主要表现在这样四个方面。
首先是《北腔》的基本行文结构,采用了一种将晋商与晋剧并置交叉描写以推动情节演进的结构方式。我理解,毛守仁之所以将小说命名为“北腔”,其实有着双
重的意味。从写实意义上说,这“腔”当指与晋商的发展差不多保持了同步状态的地方剧种——晋剧;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腔”便隐指着一种以晋商与晋剧为突
出外在表征的带有浓烈地域文化特征的晋商文化形态。一部表现晋商的长篇小说,差不多有一半的篇幅描写晋剧,而且,关于晋剧的描写较之于晋商似乎还更显浓墨
重彩也更具艺术感染力,关键的问题在于,小说中的晋剧描写实际上承担着一种极为重要的结构功能。小说文本中有这样的话,“连皇宫那样的道貌岸然处,也无非
是一放大的院子,人心不差米粒。天下事无非是戏,他们也跑不到戏外。”一句“天下事无非是戏”道破了毛守仁以汪洋恣肆的笔墨尽情描写晋剧的根本动机所在。
其次,从其艺术的基本根源来看,毛守仁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一些优秀的小说传统,另一方面也对西方的现代小说经验进行了有益的借鉴。首先,我们从《北腔》中
能够读出一些《红楼梦》的韵味来。让我们形成这样一种判断的首要原因当然是《北腔》中对于若干美丽且别具精神内涵的女性形象的鲜活刻画,此外的另一个原因
则是艺术表现层面上毛守仁对于“藏”字诀的成功运用。所谓“藏”字诀当然是我个人杜撰的一个名词,它的意思是说作者在小说的描写过程中对于自己所欲凸现的
艺术主旨往往采取一种极含蓄地带有极强烈暗示意味的表现方式,言有尽而意无穷,颇有一点中国古代山水画中写意留白的意味。作家在描写时绝不写足写满而只是
点到为止,从而预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供读者去积极填充。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优秀小说传统进行创造性继承的同时,毛守仁在《北腔》中同样有对于西方现代
小说表现手法的成功借鉴,这一方面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作家通过对西方“意识流”手法的创造性转化而对于人物的潜意识活动进行了堪称准确到位的艺术揭示。
第三,《北腔》在叙事方面的一个突出特征则体现在对于一种第三人称主观限制叙事模式的成功运用,然而它又与一般意义上的第三人称不同,毛守仁又对第三人称进行了明确的限制。具体来说,《北腔》中的每一个叙事段落都是严格地按照故事中某一人物的
视点来进行叙事的,这样,虽然并未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但这些不同的叙事段落却共同表现出了一种十分突出的主观化色彩。也就是说,《北腔》在叙事上极
富艺术智慧地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叙事特点进行了极其巧妙的整合。应该承认,这种叙事整合取得了相当明显的叙事效果。一方面,第三人称的运用使得作家可
以以一种冷静客观的姿态描摹社会上的世情百态,从而赋予了小说一种突出的客观化特征;另一方面,第一人称的叙述视点则为作家对于人物形象复杂微妙的精神心理世界的探究与表现提供了极便利的条件,从而使小说又呈示出了一种极明显的主观性特征。建立在客观性基础之上的主客观融合恐怕正可看作现代小说的一个突出表征所在,《北腔》则也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依循第一人称的人物视点方式进行叙事的时候,由于小说中存在着众多的人物,所以也就相应地形成了叙述视点频繁转移的这样一种叙事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毛守仁其实正是在这样一种人物叙述视点频繁快速转移的过程中逐步推进、深化小说的故事情节演进的。
第四,从根本上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毛守仁对于小说创作中语言的重要性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他在创作过程中自觉地实践着对于一种准确典雅而又及物的小
说语言风格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说,毛守仁这样一种过于严格的语言追求甚至还多少带有了一点唯美主义的倾向。比如小说中描写祁掌柜唱戏时的一段叙事话
语:“这个腔新奇、俏丽,拖腔上高出半个字,似跑调却没跑出去,没跑调又在边缘滑,就像刀尖儿划着肉皮儿走,险则险,却又诱人。”这段叙事话语对于祁掌柜
拿捏得恰到好处的唱戏感觉进行了极准确的描写,实际上,也正是作家在小说语言运用方面所具有的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艺术功力,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北腔》艺
术成功的最终取得。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毛守仁《北腔》的艺术主旨问题。虽然毛守仁对于晋商、晋剧,对于张之洞、否否居士的史料均下过相
当大的功夫,但在我看来,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北腔》更多地还是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建立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汹涌而起的商品经济大潮基础之上的容纳了毛守
仁关于晋商、关于女性的别一种文学想象的长篇历史小说。毛守仁曾经强调:“晋商的正本大戏由如椽大笔们去摹写,那是正史,是大主旨,我只写自己能感受到
的。这是美,是美的伤痛。”应该承认,实际的情形也的确如此,就小说的基本艺术主旨而言,作家所欲表达的确实“是美,是美的伤痛”,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