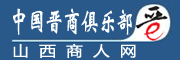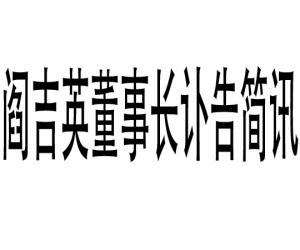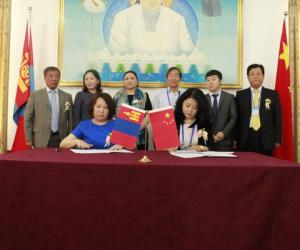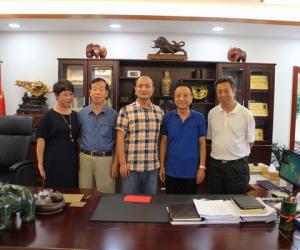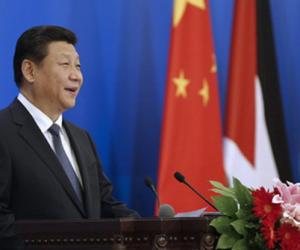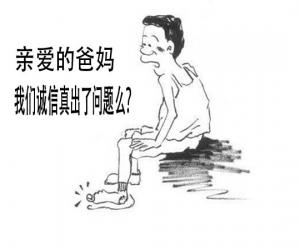中古商贩与社会网络
自有历史以来,社会共同体一直就伴随着人类。远古的部落、现代的国家、政党、企业都是共同体的一种形式。商贩群体,也是一个社会共同体,五百年来,流变不居。其形成和流变,可能蕴含着我们不知道的有关共同体的故事。罗朗斯·丰丹的《欧洲商贩史》一书,恰好就对商贩这个特殊群体做了全面的和细致的梳理。
法国历史学,一直以来就有个突出的特点,不是寻找传奇,也不构建意识形态,而是擅长做群体和事件分析。这一点,在年鉴学派,尤为明显。罗朗斯·丰丹对这种史学手段,显然非常熟悉。因为掌握大量资料与档案、族谱,看她使用,都是信手拈来。
丰丹将整个商贩群体作为一个共同体进行了叙述,并认为,其主要特点,就是流动。既然是流动的,那还是不是一个共同体,这就有疑问了。如果不是吉卜赛这种以流动为生活方式的民族,很难将流动群体作为共同体来考察。典型如中国古代的流民,在中国史的研究中一直很难界定,除了农民起义时能被注意以外,长期被忽视,而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流民一直是长期存在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行商坐贾的说法,但终究商人是要“行”的,所以商人无论如何是流动的。正如近年来电视剧一再强调的晋商“走西口”等等,都说明了商人在传统社会中,流动性是非常大的。但在商人流动性比较大的同时,我们也看出了另外一种趋向,也就是商人家族化,进而组织化。组织化的商人集团,就有些共同体的味道了。好比我们现在很了解的温州商人群体,都不是小商小贩的单干,而是有集体规则与行动的共同体。
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商人,我们再来看看丰丹讲的欧洲商人。
商贩,在欧洲历史上,有很大的特殊性。这一点,与古代西欧的行商制度密切相关。商人是有行会组织和正式的城市身份,属于一个被古代西欧政治组织所承认的群体,所谓的第三等级(Middle Class)。通过行会组织,商人有效地形成了自我共同体。
按照行会法规,商人的活动,从开店时间到从事行业,都有严格的限定。大型的商贸活动都有严格的限制,中古时代跨区域的集市非常之少,像香槟集市这样的大型经贸会更是凤毛麟角。
丰丹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这个共同体的组织方式就是“家族”。长期以来中西方历史比较,在东西方社会组织形式上一直有争议。传统认为古代中国以家族血亲为组织方式,而西方则是宗教和社团组织,故而东西方文明本质不同。但是事实上,历史研究不断告诉我们西方并没有那么“不近人情”。丰丹的商贩研究就是典型,商贩通过婚姻、继承等各种关系不断地弥散到各区域,各个社会次生体系,而彼此认同。
故而《欧洲商贩史》不仅对于我们了解欧洲商贩这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有意义,对于中西文明的所谓差异问题也能有所帮助。
不过丰丹的这本书意义并不仅在于此。商人群体是如何走出中古,跨入现代公司制度的?这一直是历史学研究的重点。传统史学都以为是工业兴起的结果,但是丰丹却给出了另一种可能。丰丹认为,商贩群体很早就在竞争中形成了网络化社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搭建了社会网络,逐步掌握了跨区域贸易。而现代的商业社会,正源于这种陌生人构筑的网络社会。
书读完,我想起另一个问题,中国近代,商人群体的败落,是为什么,是简简单单的竞争不行?这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就不是一部《欧洲商贩史》能解决了。
(《欧洲商贩史》,(法)罗朗斯·丰丹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