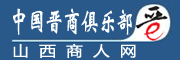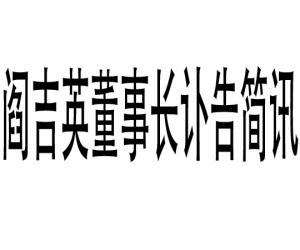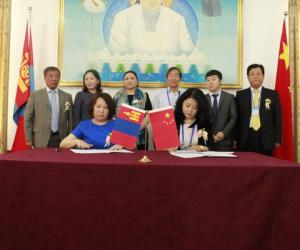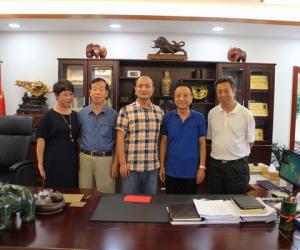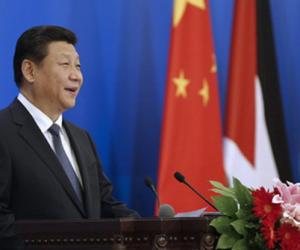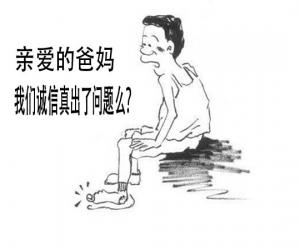金融时报专访秦晓:国有企业、政府角色、及中国模式
“没有人说我是国有企业的坚定支持者,我自己也不认同这样一个概念。我只是国有企业的一员,我要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说这番话的是秦晓,中国国企标杆之一,招商局集团现任董事长。在他近15年的国企领袖生涯中,招商局是他迄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亚洲金融风暴后他临危受命,从另一家国企中信调任负债累累的招商局,用五年时间扭转颓势,让这家百年企业重焕生机。如今招商局正经历秦晓任下的第三次“再造”,目标是 2011年时集团资产和利润较2006年翻番。
常驻香港总部的秦晓行程密集,我们在他短暂访京途中逮住了一次视频采访他的机会。
身着深灰色西服的秦晓面容黝黑清癯,思路敏捷清晰,语速悠缓却不容打断。有着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他被公认为企业领袖中的思想者。在谈了金融危机对招商局的冲击,以及招商局再造计划的远景后,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国有企业和经济改革上。
我想听听他对西方最近颇受争议的“国有化”思潮的看法。在问题的开头,我有些想当然地称呼他为“国有企业的坚定支持者”。
秦晓没有打断我,平静地听我说完问题,稍稍一顿,说出了本文开头的那段话。
这着实令我我暗暗诧异。
成立于晚清的招商局一直是中国企业界的一艘巨舰,广泛涉足运输、码头、金融、地产等领域。但到97亚洲金融危机时,集团“横向多元化、纵向多级化” 的结构痼疾暴露无疑,不良资产激增、盈利能力下降、利息负担加重、现金流断裂。秦晓上任后,果断剥离非核心业务,斩断过长的管理链,加强总部主控,带领集团先后用一半的时间完成了两个五年再造计划。启动于2007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到2011年,集团总资产比2006年翻番达到2000亿元,净资产翻番达到700亿元,净利润翻番达到120亿元。前两个目标到2008年底已经接近实现,而尽管净利润增长受此番金融危机所累,秦晓还是对按时完成计划表示乐观。
他说,这次金融危机,到了国企“比内功”的时候,招商局在前几年的“静悄悄的革命”为抵御这次危机准备了弹药。
这么一个对经营有追求有建树的国企当家人,却这般直接地否认自己支持国企这种经济形式,令我惊讶。而秦晓的回答很快让我明白,他对国企的思索和担忧,早已超越了一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甚至超越了国企的经济职能,而是直指国企及其背后的政府,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他说:“在我看来,有两个问题是我们在改革中需要去反思和研究的。第一个就是政府主导经济。”
他说,我们市场化追随的是韩国和日本的“发展主义政府”模式,这个模式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主导太强,变成了大政府小市场,强政府弱市场。“我想我们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这里来。”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有没有必要去控制这么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国有企业是政府直接控制的经济资源。”
他说,政府的职能本应当是提供公共产品,以及行使宏观调控和调整经济周波等职能,而非控制资源,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国有企业应当被逐渐社会化。
他说他反对一种观点,即涉及到国计民生和国家战略的产业需要国有企业来主控。“这话意思就是说,其它国家就没有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没有国家战略产业?那你要回答我,第一,为什么其它国家不要国有企业来做这个事情;第二,你能证明国有企业更有效、更安全吗?在没有一些政策支持,没有一些垄断的情况下,你能证明吗?”
我忍不住问:那国有企业究竟还要不要存在?
“长远来看不需要存在,”秦晓回答得很干脆。“我认为国有企业是遗产,是计划经济的遗产,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现在的任务,从微观层面看应当把它搞好。从宏观层面看,应当把它逐步地分散到社会和民众手里去。”
既然已经从微观谈到了宏观,那么我想听听秦晓对改革三十年后路径的看法。我问,这次金融危机之后,连西方都出现了一种声音,就是中俄式的,集权政体下政府主导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也许不失为共产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我们的发展模式究竟可持续吗?
“我想一种模式的诞生一定有它的合理性,”秦晓沉吟半晌说。“但是它有一个基本的规律。这个基本规律就是,不能简单用经济增长的速度,来做一个价值判断。”
他认为,更高层次的价值判断,是社会是否认同包括自由、个人权利、和民主在内的一些“核心价值观”。
“如果抛开这些价值,只看经济发展速度的话,我以为是不成立的。”
这些核心价值观正是秦晓口中“现代性”一词的含义。他曾经多次提及、甚至撰文阐述这个概念。他认为,在中国,我们一直用“现代化”来代替“现代性”,而这正是我们发展的误区所在。
“现代化在中国就是民富国强,更多的是一个物质和经济指标,我们提出翻两番啊,人均GDP多少啊,都是一些经济和物质的指标,”秦晓说。他认为,这种经济增长奇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社会转型,
“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这个转型一定要有现代性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和制度来作支撑,”他说。
采访接近尾声,秦晓说,在追求“现代性”上,他不是一个本土派,而是一个“普世派”。也就是说,他认为,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追求,不只适用于西方,而具有普世意义。说到这里,我几乎已经忘记自己是在和一个企业家交谈了。
也许正是这种超越数字指标,触及价值层面的思考,帮助秦晓带领招商局用五年时间完成了规划中需耗时十年的两次“再造”;正是这种思考,令他可以跳出 “在其位谋其政”的思维,直面国企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尴尬处境;也正是这种思考,可以令那位当年插队内蒙草原的牧民、那位五十岁获得剑桥博士的学者,和那位管理着数千亿资产的企业家,在秦晓身上完美地集结。